- 蒋百里

蒋百里
人物生平
 蒋百里
蒋百里
清光绪八年(1882年),蒋百里出生于浙北硖石镇的大家族。蒋百里原名蒋方震,百里是他的字。[1]
祖父蒋光煦(号沐公)是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建“别下斋”藏书楼一座,贮书10万册,刻印《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等多种书籍流传于世。
父亲蒋学烺(号壶隐),因生下来缺左臂,沐公不喜欢他,送他到寺庙出家做小沙弥。长大还俗学医,悬壶济世,娶浙江海盐秀才、名医杨笛舟的独生女杨镇和为妻。杨氏贤妻良母,又通文墨,成为蒋百里的启蒙老师。
1893年,蒋百里11岁,回原籍蒋氏家塾附读。[2]
1899年,蒋百里参加桐乡县“观风题”考试,获得“超等第一名”。
1900年春,蒋百里18岁,应同邑桥镇孙氏之请,聘为塾师。不久在方雨亭县令的介绍下,蒋百里到林启创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就读深造,同学中有钱学森之父钱均夫、著名医学家厉绥之、民国开国名将施承志等。
1900年,庚子事变,志士唐才常组“自立会”,谋在汉口、湖南等地同时举义,后力战三天失败,唐才常被杀。蒋百里闻唐才常死,题诗追悼:
“君为苍生流血去,我从君后唱歌来。”
1901年,方雨亭县令、林启知府、陈仲恕监院3人共同出资,送蒋百里东渡日本留学。
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3000人左右,大多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同年,蒋百里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
1903年2月,与厉绥之等人创办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该杂志32开本,月刊,每期约8万字,行销国内。
蒋百里为《浙江潮》所写的发刊词,其思想之尖锐深邃不亚于《湘江评论》和《新青年》。创办于1915年的《新青年》,距《浙江潮》相差了十二年。
他又以飞生、余一等笔名,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论文连载,宣扬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颇类梁启超文笔;而他倾向革命,又不同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颇受读者注意。也是在此期间,蒋百里结识了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并执弟子礼。
鲁迅先生积极支持《浙江潮》,每期都寄回国内让亲友阅读,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达之魂》等,即发表于《浙江潮》。身系上海狱中的章太炎先生的诗文也在该刊登载,《狱中赠邹容》一诗万人争诵。
1905年,光绪卅一年,蒋百里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第三期毕业班毕业,轻松夺魁,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把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剑带走。
筹建新军
1906年,蒋百里应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聘为东北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筹建新军。赵曾专折奏保蒋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督练公所是一省督练新军的最高枢纽,督办由将军或督抚兼任,其总参议相当于总参谋长。不到30岁的蒋百里能够一跃而居高位,就算在当时也堪称异数。[2]
1906年,蒋百里被公派德国研习军事,成为兴登堡将军(后为德国总统)下面的连长。后为德意志国防军第七军营长。
1910年,蒋百里返回北京,受邀住在“宗社党”首领良弼家中。良弼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以知兵而为清末旗人翘楚。良弼看中了蒋百里,任命蒋百里为京都禁卫军管带。
1911年初,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向朝廷奏请调蒋百里回督练公所仍任原职。不过这次调任,却在程序上出现了问题:蒋百里那时的官衔只是管带,属于中下级军官,而总参议则是上中级军官,差了好几级,官场上说不过去。赵尔巽特意想了个变通的法子:在奏折上避去管带官衔,而改称“留德学生蒋方震”,“以二品顶戴任用”。
蒋百里在京都禁军管带任上,很受官兵拥戴。他辞卸当日,全营官兵围在他住所的门前,不让走,还是良弼用梯子从后楼把他偷偷接下来。当天,蒋百里就离开北京,二入奉天。
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民国成立,又调任陆军部高等顾问,以及袁世凯的总统府一等军事参议。
忧愤时局
1912年年底,袁世凯起用蒋百里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百里赴任之际,就承诺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训练成最优秀的军官,如不效,则当“自戕以谢天下”。并赠每人一册梁启超所著《中国之武士道》,以奖掖军人当勇武善战、忠于国家。蒋百里要办一流军校的理念,与北洋政府把军校当摆设的设想南辕北辙。半年之间,经费屡屡克扣,段祺瑞所掌管的军部一再告诫蒋百里莫要改革。
1913年6月18日凌晨5点,天刚灰亮,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就召集全校两千余名师生紧急训话。他身着黄呢军服,腰挂长柄佩刀,足蹬锃亮马靴,站在尚武堂石阶上一脸沉痛:“初到该校,我曾宣誓,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如此看来,我未能尽责……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接着,蒋百里掏出手枪,瞄准自己胸口猛开一枪。
蒋百里此次自杀的缘由众说纷纭,有说是愤于军校学风浮躁,有说是向陆军部请求拨款未果,也有说是对中国当时军界、政界之绝望。
自杀前夜,蒋百里致书寡母,称:“为国尽忠,虽死无关重要,然于陆军及民国前途有益。遗币二百,薄田数亩,聊供赡养。”字字肝胆。
蒋百里不是空谈而盲目的爱国者,在保定军校就以日本为假想敌训练新军。 培养了陈铭枢、唐生智、刘文岛、龚浩、万耀煌等大批将帅。
奇人必有奇运,蒋百里受到医院护士、日本女子佐藤屋登的悉心照料,竟奇迹般生还。后者成为第二任妻子,改名蒋左梅。
助蔡讨袁
1916年袁世凯称帝,蒋百里入川辅佐老同学蔡锷讨袁。袁世凯死后,陪蔡锷去日本就医,旋即为之料理丧事。
1917年回国,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首次撰写军事论著《孙子新释》、《军事常识》等,出版后成为军校教辅。
联省自治
1918年至1919年,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归国后主持“读书俱乐部”、“共学社”等团体。
当时,国内提倡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梁启超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蒋百里积极参与,成了梁启超最得力的助手,号称“智囊”。他不仅出主意,更著书立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将。
1920年9月,梁启超与蔡元培、汪大燮等人发起成立讲学社,聘请“国外名哲”来华讲学。当时讲学社的总干事便是“文武全才”的蒋百里。英国哲学大师罗素、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蒋百里代表讲学社具体负责接待工作。
1920年,他当选浙江省议会议员,参与浙江、湖南省宪起草工作,支持“联省自治”。又主编《改造》杂志,其影响力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在此期间,蒋百里写了不少关于联省自治与社会主义的文章。毛泽东当时也致力倡导“湖南省自治”,正是受其影响。
1921年,蒋百里将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为之作序,下笔不能自休,竟写了5万多字,跟原书的字数都差不多了,梁氏只好另作短序。后来梁将这篇长序改写、充实,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作序。可算民国学术界一大佳话。
《西方文艺复兴史》至今为中央美院教材,谁能想象此书出自陆军二级上将之手?!
1921年,由郑振铎、茅盾、蒋百里等12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1922年,梁漱溟被冯玉祥请去给部队将领讲话,梁漱溟惊讶发现,冯玉祥给将领每人发的小册子上,辑录的古今名将治军格言中,除了“岳飞曰”、“曾国藩曰”、“胡林翼曰”,“蒋方震曰”亦赫然并列,他早听说冯玉祥对蒋百里相当崇敬,这回终于眼见为实。
1923年,松坡图书馆在北京成立,梁启超任馆长,蒋百里主持编辑部。
1923年,蒋百里与胡适一起创办新月社,并同徐志摩结为至交。几年后蒋百里被蒋介石关进监狱,感情充沛、容易激动的徐志摩还背起铺盖,喊着要进去陪他坐牢。
论持久战
1923年,蒋百里从北京返乡葬母,后由津浦路北上,车过徐州时,他指着窗外对同行的学生龚浩说:在不久将来,中国和日本必有一战,一旦战事爆发,津浦、平汉两线将被日本占领,中国国防线大体应北起太原,经洛阳、襄阳、衡阳这三阳线,是为东部平原与西部山地的连接地带,日后可作抗击外敌入侵。龚浩听了不以为然,以为老师杞人忧天。十四年后,抗战爆发,半壁江山沦陷,已任第一战区参谋长兼河南省建设厅长的龚浩感念万千,于蒋百里逝世一周年时,在他驻防地南阳诸葛武侯祠建“澹宁读书台”纪念恩师,“澹宁”是蒋百里晚号,匾额为龚浩手书,另立的“蒋百里先生纪念碑”刻录了当年车上的这席谈话。
1925年,蒋百里再度出山,任吴佩孚的总参谋长,因吴佩孚不“讨奉”而辞职,去上海投孙传芳。
1929年,他支持原湘军将领唐生智起兵“倒蒋”。
1930年,入狱。稍后,与蒋介石达成和解。
1933年,奉蒋介石之命赴日考察,认为中日必有一战,拟定多种国防计划,呼吁国民政府备战。
1935年,被聘为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
1936年,赴欧美各国考察军事,归国后倡议发展空军。中国最早关于空军构建的思想,来自陆军出身的蒋百里。
1937年初,蒋百里最重要军事论著集《国防论》出版,轰动一时,扉页题词是:“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蒋百里将军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但他后半生和日本结缘不少。他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编著的《国防论》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抗日战争的战场上,蒋百里将军在保定军官学校、在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
1937年9月,他以蒋中正特使身份出访意、德等国,10月面见墨索里尼,11月又赴德国柏林。 [3] 回国后发表《日本人》及《抗战基本观念》,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1938年10月,他出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原由蒋中正兼任)。
文节千古
1938年11月4日,在迁校途中,他病逝于广西宜山,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
黄炎培先生的挽联云: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
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邵力子先生的挽联云:
合万语为一言,信中国必有办法;
打败仗也还可,对日本切勿言和。
张宗祥挽蒋百里先生诗:
宵夜病急难求药,地僻医迟未处方。
如此人才如此死,旅魂凄绝鹤山傍。
章士钊挽蒋百里先生诗:
文节先生宜水东,千年又致蒋山佣。
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
名近士元身得老,论同景略遇终穷。
知君最是梁夫子,苦忆端州笑语融。
著述文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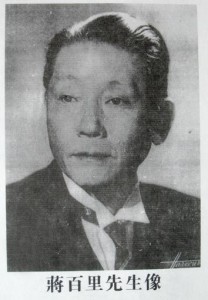 蒋百里蒋百里与蔡锷同庚,同为秀才,在日本留学期间一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遂结成生死之交。蔡锷是维新派领军人物,梁启超的弟子,那时梁启超在日本避难,由蔡锷介绍,蒋百里结识梁启超并拜他为师。梁启超对蒋百里的文学才能分外赞赏。
蒋百里蒋百里与蔡锷同庚,同为秀才,在日本留学期间一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遂结成生死之交。蔡锷是维新派领军人物,梁启超的弟子,那时梁启超在日本避难,由蔡锷介绍,蒋百里结识梁启超并拜他为师。梁启超对蒋百里的文学才能分外赞赏。
蒋百里一向视梁启超为恩师,执礼甚恭,但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上,却从不含糊,敢于同恩师公开论战。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宣扬“立宪”,尤重“新民”,指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接着他又写出了《新民说》、《新民广义》等文章,加以系统地阐述发挥,改良主义论调泛滥一时,迷惑了不少人。蒋百里立即用笔名“飞生”,撰写《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刊于《浙江潮》,尖锐指出:“《新民说》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而《立宪说》则直所谓隔靴搔痒者也。”此文连载两期。刚刊出上半篇,即引起梁启超的高度重视,马上回应,写了《答飞生》一文,刊于《新民丛报》,进行辩解。这场论战,实际上是后来章太炎与梁启超那场大论战的前奏。同好问蒋百里:“梁任公是你的恩师,你怎么同他公开论战?不怕损害师生情谊吗?”蒋百里直言相告:“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
《浙江潮》创刊词
蒋百里亲撰了创刊词:“我浙江有物焉,其势力大,其气魄大,其声誉大,且带有一段极悲愤极奇异之历史,令人歌,令人泣,令人纪念。”“呜呼!亡国其痛矣……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激刺于吾国民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我愿我青年之努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
1920年9月,蒋百里主编的《改造》杂志发刊,销路日增,成为当时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有数几家全国性刊物之一。蒋百里每期至少有一篇文章发表。其时,“省自治说”颇为流行,以对抗北洋政府的中央集权。蒋百里陆续写了《同一湖谈自治》、《联省自治制辨感》等篇。公众对社会主义颇感兴趣,《改造》每期都有文论及,蒋百里也写了《我的社会主义讨论》、《社会主义怎样宣传?》等文章,更加引起梁启超、陈独秀等的关注。
《欧洲文艺复兴史》
蒋百里醉心研究文学。1920年,他从海外归来,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于文艺复兴时期精神,体会很深。他在“导言”中指出:“文艺复兴,实为人类精神界之春雷。一震之下,万卉齐开。……综合其繁变纷纭之结果,则有二事可以扼其纲;一曰人之发见;二曰世界之发见。”梁启超评论此书为“极有价值之作,述而有创作精神”。蒋百里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是我国人士所撰有关文艺复兴的第一本著作。1921年问世后,14个月内出了三版。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民主”、“科学”两大旗帜深入人心。蒋百里在文中提出的“人之发见”、“世界之发见”两点,正是“民主”、“科学”的生动注脚,符合于时代精神。《欧洲文艺复兴史》约5万言,由梁启超作序。梁启超下笔不能自制,一篇序言竟也写了5万字,与原书字数相等。他又觉“天下固无此序体”,只好另作短序,而将此长序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为该书作了序言。这一文坛趣事虽不能说是绝后,却属空前未有。
蒋百里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共学社丛书》,从1920年9月到1935年7月,15年间,共出丛书16套、86种,是旧中国规模最大的学术文化丛书之一。当时进步作家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翻译了许多俄罗斯文学名著,都在蒋百里的帮助下,收入《俄罗斯文学丛书》,由“共学社”出版。
《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
蒋百里在文史方面亦有建树,写过《宋之外交》、《东方文化史与哲学史》、《主权阶级与辅助阶级》等,颇有独到见地。他在抗战初期写了许多文章,其中最出色的当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这篇剖析日本形势的杰作,极大地激励了四万万同胞的抗日斗志。
《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是蒋百里的传世名作之一。蒋百里还是著名的“日本通”,在《日本人》一书中,他深入剖析日本的国民性格,又从自然、地理、风土、人种特征等各方面入手,并对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代表人物进行分析和比较,从而得出结论:日本民族会走到极端,欲征服亚洲进而称霸世界,所谓诛求无厌,但最终“缺少像长江、黄河这样宽阔的胸怀,乃总是很难如愿以偿”。此书一出,即成为一本社会人类学的范本。
《国防论》
1937年初,出版军事论著集《国防论》。他在其他著作及言论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 :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第三,以空间换时间,行持久战,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 。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事实上,蒋百里虽然在1938年早逝,中日的战争发展,恰恰按照他的预料进行,反映了他对两国实力与战略态势的准确把握。他在逝世前不久发表的文章中,更掷地有声地提出了今后中国对日战略的指导方针——“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 !”不过,这些观点并没有出现在《国防论》中,后人以讹传讹多矣。
《国防论》问世于全面抗战前夕。书中认为,“中国国家的根本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中国国民的军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利用国民自卫心来保卫国家,没有不成功的”,“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敝;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用处”。(陶菊隐:《蒋百里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1、162页。)蒋百里的这些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对指导抗战是有益的 [4]。
1938年,蒋百里病逝。许多名人写挽联挽诗哀悼。章士钊《挽百里》诗云:“文节先生宜水东,千年又致蒋山佣。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名近士元身得老,论同景略遇终穷。知君最是梁夫子,苦忆端州笑语融。”
军事思想
“寓兵于农”的军事理念
1918年9月,蒋百里参加“欧洲考察团”,归国后发表《德国败战之诸因》一文,详细分析了当时德国的形势、政略、兵略之失败,得出德国军国主义的失败乃“军阀之祸”所致的结论,从而改变了自己以往认为军队可以决定一切的思想观点,发现比军队更加深刻而有力的战争决定因素乃是老百姓。
蒋百里提出了“寓兵于农”这一全民抗战的崭新军事理念。该文与后来德国鲁登道夫将军反省德国欧战失败教训的著作《全民族战争论》,互为表里,并驾齐驱,在国际军事论坛上受到高度重视。
居安思危的战争预言
1922年,发表《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一文,首次公开指出日本侵略的危险,说:“至于从中国现状言,吾侪所最感危险者,即邻近富于侵略性的国家……”
1928年5月3日,日军大举进攻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印证了蒋百里的战争预言。
开创性的军事经济思想
1935年,发表《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提出:“我于民族之兴衰,自世界有史以来迄今日,发现一根本原则:曰:‘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文中分别以蒙古人的马、欧洲人的船既是“吃饭家伙”又是“打仗家伙”为例,从而揭示了他们两度征服世界的奥秘,并以西人的国家动员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为例,对上述论点做了强有力的阐释。
蒋百里把人民生活(经济)与武装战斗(国防)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大大开拓了人们对于如何取得战争最后胜利的对策思路。
1945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说:“我们要打击日本侵略者……然而我们是处在个体经济的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怎样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就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一种方法。”“用极大的精力帮助农村人民展开生产运动,几年之内,农村就会有丰富的粮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坚持战斗,不但可以对付荒年,而且可以贮藏大批粮食和日用品,以为将来之用。”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中,再次提出:“全军应趁目前的时机,在不妨碍作战和训练的条件之下,一律学会完成部分的生产自给的任务。” [5]
从上述文字可见,毛泽东与蒋百里谈的是同一个问题,基点都是生活条件之于战斗条件的重要意义及其密切关系。
立体化的军事对垒思想
1937年初夏,蒋百里的《国防论》问世。其中着重提出了三点:杜黑主义、总动员、速战与持久。
此时已值抗战前夜,他所提出的这三点,正是摆在当时中国面前必须充分认识与亟待解决的重大军事课题。面对日军侵华战争即将爆发、而当时中国空军能投入作战的飞机尚不足百架,极有可能处于被动挨打,丧失胜机的危险,蒋介石正是采纳蒋百里的意见,才从速添置飞机,扩大航空学校。
1937年8月15日,中日双方爆发大规模空战,中国空军顶住了60多架日机的袭击,当天击落日机17架。
1937年8月16日,又将8架日机敲落在地,一举冲散了中国天空多日的阴霾,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使中国军民斗志大振。
蒋百里推崇的“杜黑主义”对最初的抗日战争是一个立竿见影的实战建议,他提出的“总动员”和“速决与持久”的战略战术思想,为后来抗日战争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战术指导。
超前的军事人口战略思想
1937年,蒋百里作《张译鲁屯道夫全民族战争论序》,提出:“新军事的主流,是所谓‘全体性战争’”,“未来的战争不是‘军队打仗’而是‘国民拼命’”。这是蒋百里在对以往传统军事人口学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而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军事人口战略思想。不仅从战略上揭示了民众参战对战争取胜的决定性意义,也从军事人口学意义上触及了民众是军事人力资源的本质要义。
这一思想既合乎战争规律,又合乎中国国情。因为它不再是对世界“新军事主流”的纯理论研究,而是集结了对日本国的深刻了解,并结合了中国军阀混战,拥兵割据,穷兵黩武,新军力量不堪一击,但同时中国又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的实际情况。
在蒋百里提出上述论点之后的1937年7月,毛泽东在他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也同样提出了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问题:“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6]
1938年1月26日,蒋百里在柏林又写出了一篇针对抗战形势,论述速决与持久关系的重要军事论文——《速决与持久》。文章开头就提出:“以此现代战术战略的趋势,也自然向速决方向走去。但从整个国家的立场说来,即从所谓‘全民战争’的范围说来……就注重在‘持久’两字……”
这是蒋百里先生在军事人口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战术问题。
1938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一文,分析说:“由于日本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日本是采取战略进攻方针的,我们则居于战略防御地位。日本企图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们应自觉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
富有战斗精神的抗战言论
抗日战争初期,蒋百里先生曾被誉为“抗战文坛健将”。针对当时敌强我弱、不少人士中流行“恐日病”的情况,蒋氏在《国防论》的扉页上写道:“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办法何在?即“国民皆兵”、“国民拼命”。
在抗日战争中,蒋百里“中国是有办法的”这句名言,大大鼓舞了全国军民齐心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韧性战斗精神。
1937年9月,蒋百里赴意大利考察,10月面见墨索里尼,11月又赴德国柏林。在此期间,撰写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从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各方面深刻剖析了日本国内情,结语是:“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
此文系蒋百里先生潜心研究日本30多年的心血结晶,文中结语通俗易懂,直截了当,观点鲜明,一语道出了全国亿万人民抗战到底的心声,一时成为国人铭言、朝野一致的金科玉律。[3]
家庭关系
蒋百里的婚姻很是有名,因为他是一个以研究对日战略著名的中国将领,却娶了一个日本妻子。其过程早有披露,盖将军为保定军校事心灰意冷而自杀,日本护士佐藤屋登照顾他时两人产生感情而成眷侣,过程则一波三折,不及详叙。
两人成亲后,佐藤屋登改名蒋佐梅,盖将军酷爱梅花。两人曾在海宁植梅数百株,意将来归老此地,皆毁于抗日战争之中。
冯玉祥本是蒋百里将军好友,在军中办教育班,内容多是“孙子曰”、“岳飞曰”、“华盛顿曰”,其中竟然还有“蒋方震曰”,对将军的推崇可见。因此闻知将军去世不免反应过激,出身日本的佐梅夫人就成了他的怀疑对象,于是写文章说将军是被佐梅夫人用毒针杀害,因为“你爱你的祖国,我爱我的祖国”。其实,这句话是两人成婚前佐梅夫人表达自己对百里将军研究抗日理论的理解而说的,原话是“你爱你的祖国,亦如我爱我的祖国一样”。
这件事给佐梅夫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但是佐梅夫人很快用自己的行为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任与爱护。她此后用华语教育将军的五个女儿,带着她们一起到街头募捐处,拔下头上的首饰捐助抗战事业,并亲赴前线为中国的伤兵治疗服务。佐梅夫人晚年曾讲,她这样做,因为她认为当时中国的战斗是正义的。 1978年,夫人病逝,墓碑上篆刻的名字为“蒋佐梅”——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妻子的名字。
将军和佐梅夫人生有五女,除大女儿蒋昭早逝外,也都颇有传奇色彩。
二女儿蒋雍,原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抗战开始后按照父母的劝导回国参加救护队,为伤员服务,后定居美国。
三女儿蒋英,是著名钢琴家和歌唱家,毕业于柏林国立音乐学院,音域宽广优美,是德律风根公司的十年唱片签约歌手。1955年随丈夫钱学森回到祖国,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
四女儿蒋华,定居比利时,曾筹办欧洲中山学校,为华侨教育做出重大贡献,在钱学森回国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穿针引线作用。
五女儿蒋和,幼年就曾随父亲环游欧洲,解放后定居北京。“文革”期间,因为她的身份受到严格审查。蒋和傲然不屈,在写交待材料的纸张上写道——“陈伯达是杂种”,吓得审问人员张口结舌,不敢将材料上交。
一代名将,风流竟不灭凡七十年也。
友人族亲
蒋百里是兵学家,又是国学家,其祖父是海宁藏书名家,一生风流倜傥,身边名士云集。他好交朋友,罗素、郑振铎等都受其帮助;蒋经国、唐生智虽为部下却感情深厚,蒋百里的朋友,也都是大有性格人物。
与杭州厉家
蒋百里家与杭州厉氏家族、杭州钱氏家族,三家都是浙江的书香名门,且为亲族世交。
蒋百里与晚清金石大家厉良玉的长子、中国近代西医学教育先驱厉绥之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之父、教育家钱均夫,三人既是亲戚,也为挚交。三人青少年时便是杭州求是书院的同学,毕业后又同赴日本留学。1903年,蒋百里与厉绥之在日本东京一同创办了著名的《浙江潮》杂志。回国后,厉绥之成了名医,蒋百里和钱均夫家若有人患病,均请厉绥之帮忙诊治。蒋百里女婿钱学森小时候得过两次很厉害的病,差一点夭折——一次是脑膜炎,一次是伤寒,都是在厉绥之的医治下转危为安。1946年钱学森回家探亲,拜过高堂之后,第一个来看的就是厉绥之——他当时是下跪的,说:“伯大人,没有你当初的照顾,就没有我钱学森的今天。”蒋百里之女蒋英与钱学森被传为佳话的结合就是由厉绥之撮合的。
蒋百里与厉绥之二弟、抗日爱国名将厉尔康相交甚笃。两人不仅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毕业后还一同在清廷禁卫军中供职,随后又一起参加革命。厉尔康所著《国防与物资》一书,蒋百里曾大为赞叹,并为书作序推荐。
蒋百里与厉绥之三弟、近现代文教界代表人物厉麟似也是刎颈之交。厉麟似曾听取蒋百里的建议,辞去了国民政府的职务,全力帮助蒋百里翻译德国军事著作。蒋百里著名的《国防论》,厉麟似即是该书隐形的第二作者。《国防论》中有不少内容都是这位低调的军事翻译家襄助蒋百里完成的。
与徐志摩
徐志摩与蒋百里为亲族,曾共同组织新月社。在徐志摩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蒋百里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帮其渡过难关。1930年蒋百里受牵连入狱,徐志摩竟然扛上行李到南京陪蒋百里坐牢,一时轰动,新月社的名流纷纷效仿南下,一时“随百里先生坐牢”成了时髦的事情。
与梁启超
梁启超与蒋百里尽管有师生名分,政治观点上却相左,经常激烈争论。有人对此不解,蒋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两人的争论丝毫不影响感情,梁启超也是出名的豁达人。蒋百里曾作《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启超作序,梁看了非常赞赏,下笔就没了定数,写完一看,居然比原作还长——天下没有这样的序,梁只好另作一序,原来那篇长序呢?干脆充实为另一本书发表,这序呢,就请蒋百里来写,遂成佳话。
与蔡锷
蔡锷和蒋百里是同年秀才,又是同学,莫逆之交。蒋从日本士官学校以第一名毕业回国后,袁世凯对他极为器重,彻夜谈兵孜孜不倦,随后根据他的建议组建“模范团”,作为中国新式陆军的样板部队,逐渐推广全国。因袁称帝倒台,这个设想没有实现。不过模范团的后身第九旅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兵海参崴,以纪律严明为中国争得一份光荣。
蒋家与厉家的缘外之缘。蒋家与钱家是亲家,钱家与厉家素厚,而蒋家又与厉家甚有渊源。厉鹗后人厉良玉长子厉绥之是蒋百里的亲家公钱均夫的莫逆之交,同时又是蒋百里的同窗好友。无巧不成书,厉绥之二弟厉尔康又因蒋百里赴日留学后选择了军事方向与其同在清廷禁卫军中供职。两人因家有渊源而相交甚笃。1927年,厉尔康著《国防与物资》一书,蒋百里为其作序。同时,厉绥之与厉尔康的四弟厉麟似也与蒋百里交情甚笃。厉麟似曾受蒋百里之邀辞去国立中央大学德文教授的职务特赴上海为其翻译德国军事著作。
当袁世凯酝酿称帝的时候,蒋百里不顾个人恩情,和蔡锷、张宗祥等11名将领秘结同盟,先后南下组织反袁护国。这中间,蔡锷因受到监视,乃采取蒋的妙计深居简出、吃花酒做出一副醉生梦死之态,乃至家人反目而走减轻了袁的疑虑,然后突然逃走,到云南组织讨袁战争,这就是电影《知音》中小凤仙掩护蔡锷出逃的真相。同盟中人曾担心袁派人追杀蔡,蒋却胸有成竹,道“老袁用错了人”,原来他已知晓袁世凯派出追杀的是陈仪,也是同盟中的一员。
不久,蒋亦南下加入讨袁司令部,参加北伐。袁惊惧而死后,蔡锷因喉病逝世于日本福冈,蒋百里时在其侧,代拟遗电,并护送灵柩回湖南安葬。时人论曰,蒋之反袁,取大义而舍私恩,万里扶棺,是豪杰显真性情。
女儿: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钱学森夫人----蒋英[7]
女婿:“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7]
侄儿: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7]

-
林肯航海家/飞行家百周年限量版上市 吉利豪越L配置曝光
2025-09-15 15:09:02 查看详情 -
云度云兔正式上市 百公里油耗1.4升
2025-09-15 15:09:02 查看详情 -
成都标致207购车优惠1.2万元 上海百分百购置税优惠
2025-09-15 15:09:02 查看详情 -
上海大众宝来现金优惠达2万元 上海百分百购置税优惠
2025-09-15 15:09:02 查看详情 -
Mobileye再次成功上市 百公里综合油耗4.33L
2025-09-15 15:09:02 查看详情 -
重庆卡罗拉双擎E+现金优惠4万 上海百分百购置税优惠
2025-09-15 15:09:02 查看详情 -
贵阳标致408优惠达2.8万元 上海百分百购置税优惠
2025-09-15 15:09:02 查看详情 -
雪铁龙C6ORIGINS百年臻享型怎么样 报价优惠
2025-09-15 15:09:02 查看详情 -
雪铁龙C6ORIGINS百年臻享型怎么样 最新怎么样
2025-09-15 15:09:02 查看详情 -
雪铁龙C6ORIGINS百年臻享型怎么样 时尚大气
2025-09-15 15:09:02 查看详情


 求购
求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