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食散

寒食散
基本概述
 寒食散 所谓“五石散”,是一种中药散剂。这种散剂据说是张仲景发明的,张仲景发明这个药方,是给伤寒病人吃的,因为这个散剂性子燥热,对伤寒病人有一些补益。称它“五石散”,是因为它 用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五味石药合成的一种中药散剂,而之所以又被称为“寒食散”,乃是因为服用此药后,必须以食冷食来散热而得名。
寒食散 所谓“五石散”,是一种中药散剂。这种散剂据说是张仲景发明的,张仲景发明这个药方,是给伤寒病人吃的,因为这个散剂性子燥热,对伤寒病人有一些补益。称它“五石散”,是因为它 用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五味石药合成的一种中药散剂,而之所以又被称为“寒食散”,乃是因为服用此药后,必须以食冷食来散热而得名。
其他别名
唐代称“乳石散”。
历史沿革
 寒食散 魏晋风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文人士大夫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和追崇的典范。在很多人看来,魏晋风度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鲁迅在其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不但谈到了魏晋风度和何晏等人物,同时亦多处提到了由何晏大力倡导服用的药物“五石散”。实际上谈论魏晋风度时,必定会说到这个“五石散”,因为两者几乎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服食“五石散”的风气自被何晏倡导并开始流行后,由魏晋至唐,名士们趋之若鹜,历整整五六百年而未有间断,且颇有发展,仅在《隋书·经籍志》中就著录了二十家“五石散”的解散方。
寒食散 魏晋风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文人士大夫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和追崇的典范。在很多人看来,魏晋风度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鲁迅在其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不但谈到了魏晋风度和何晏等人物,同时亦多处提到了由何晏大力倡导服用的药物“五石散”。实际上谈论魏晋风度时,必定会说到这个“五石散”,因为两者几乎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服食“五石散”的风气自被何晏倡导并开始流行后,由魏晋至唐,名士们趋之若鹜,历整整五六百年而未有间断,且颇有发展,仅在《隋书·经籍志》中就著录了二十家“五石散”的解散方。
这个与魏晋风度一样,在中国历史上极其著名的“五石散”,又叫“寒食散”,一般认为是由东汉的张仲景(150——219)发明的。因为最早注明“宜冷食”将息的“侯氏黑散”和最早直呼“寒食”的“紫石寒食散”,都是首见于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中的《伤寒杂病论》一篇,所以隋代的巢元方在他的《诸病源候论》里引晋名医皇甫谧语道:“寒食、草石二方出自仲景”。张仲景合此药的其主要目的,是用它来治疗伤寒(这个伤寒指的是感冒伤风一类的病,也就是古人说的风邪入侵,而不是指现代的伤寒症)。
主要成分
所谓 “五石散”,是一种中药散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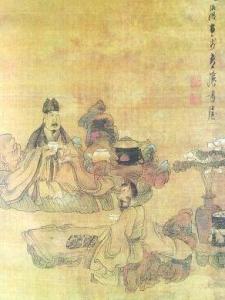 寒食散 它的主要成分是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此外还有一些辅料。
寒食散 它的主要成分是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此外还有一些辅料。
这种散剂据说是张仲景发明的,张仲景发明这个药方,是给伤寒病人吃的,因为这个散剂性子燥热,
对伤寒病人有一些补益 石钟乳:
功效:温肺气,壮元阳,下乳汁。主治:治虚劳喘咳,阳痿,腰脚冷痹,乳汁不通等。
白石英:
功效:温肺肾,安心神,利小便。主治:治肺寒咳喘,阳痿,惊悸善忘,小便不利等。
石硫磺:
功效:壮阳,杀虫。主治:内服治阳痿,虚寒泻痢,大便冷秘。
赤石脂:
功效:涩肠,收敛止血,收湿敛疮,生肌。主治:治遗精,久泻,便血,脱肛,崩漏,带下,溃疡不敛等。
紫石英:
功效:镇心,安神,降逆气,暖子宫。主治:治虚劳惊悸,咳逆上气,妇女血海虚寒,不孕。
不良后果
 寒食散服此药致羰而死者,有何晏、裴秀、晋衰帝司马丕、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等,学者皇甫谧则因服散而成残疾。其风自魏晋至唐,历五六百年而未中断。
寒食散服此药致羰而死者,有何晏、裴秀、晋衰帝司马丕、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等,学者皇甫谧则因服散而成残疾。其风自魏晋至唐,历五六百年而未中断。
曹歙、皇甫谧、靳邵、范曲、释道弘等,对寒食散深有研究,对药理学产生影响。唐初孙思邈《千金方》中录散方甚多,但深斥其祸。其后孟诜、薛曜又推挹乳石之功备至,故唐人用乳石、硫磺之类,也颇常见。降及明代,则演变为红铅。巢元方《诸病源侯论》引晋皇甫谧曰:“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必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余亦豫焉。”
相关事件
 寒食散五石散与魏晋风流人士:不明就里者往往认为魏晋名士的穿着很飘逸,称其为魏晋风度。殊不知,晋人着轻裘、缓带、宽衣,是迫不得已———因为他们服食了五石散。服五石散是魏晋上流社会的流行风俗,不过当时的名士服用此药是有极大的代价的,一不小心,它就会要人命的。然而,五石散究竟是种什么神秘药物,竟使魏晋至唐中叶的名士们趋之若鹜,历时整整五百余年而未有间断?
寒食散五石散与魏晋风流人士:不明就里者往往认为魏晋名士的穿着很飘逸,称其为魏晋风度。殊不知,晋人着轻裘、缓带、宽衣,是迫不得已———因为他们服食了五石散。服五石散是魏晋上流社会的流行风俗,不过当时的名士服用此药是有极大的代价的,一不小心,它就会要人命的。然而,五石散究竟是种什么神秘药物,竟使魏晋至唐中叶的名士们趋之若鹜,历时整整五百余年而未有间断?
五石散,亦称寒食散。其五味主药为白石英、紫石英、石钟乳、赤石脂、石硫黄而言。五石散是一种剧毒药,服用后伴随毒性发作,产生巨大的内热,因此需要一整套极其细微而繁琐的程序,将药中的毒性和热力散发掉,即所谓散发。如果散发得当,体内疾病会随毒热一起发出。如果散发不当,则五毒攻心,后果不堪设想。即使不死,也将终身残废。而散发的重要一点是,必须在服药后多吃冷饭,故称寒食散。
除了吃冷饭之外,还要注意多外出步行运动;称为散动或行散。还要注意多喝热酒、好酒,每天饮数次,使身体薰薰有酒势,即处于微醉状态。如果饮冷酒或劣质酒就可能会送命。西晋的裴秀就是因服药后饮用冷酒而致命。另外,服药后还要用冷水浴来将药的毒性和热力散发掉,并不能穿过多过暖的衣服。
其它信息
 寒食散其实寒食散的药方,汉代就有了。五石散的广泛流行是从魏何晏改造药方服用见效,加以推广后开始的。那么,何晏为何要服用并推广此药。
寒食散其实寒食散的药方,汉代就有了。五石散的广泛流行是从魏何晏改造药方服用见效,加以推广后开始的。那么,何晏为何要服用并推广此药。
何晏是三国时魏国人,本是汉末何时之孙,后来他的母亲改嫁曹操,他也就被曹操收养了。据何晏自己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并觉神明开朗。”就是说,服此药不但可以祛病,更重要的是可以使精神爽朗、气色红润———这在盛行清淡,美貌是品评人物才性高低的必要条件之一的当时,是十分重要的。何晏作为清淡的领袖人物和吏部尚书这一选官的重要位置上,不可能不高度重视自己的容貌和风度。据载,生活中的何晏美姿仪、脸很白,直令人疑其涂脂抹粉。所以,何晏服五石散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追求美貌。
以何晏的名士圈子的声望,他的一言一行都会成为人们效仿的对象。西晋以下,服散之风更盛,晋哀帝、王羲之、张孝秀、房伯玉、皇甫谧等名流,都嗜服五石散。据史学家余锡嘉先生考证,从魏正始到唐天宝之间的500多年中,服石者可能有数百万,因此丧生的也可能有数十万。
服散无异于慢性自杀,与现代社会中的吸毒现象性质类似,但服散对人体的危害程度却要远远超过吸毒。服用五石散的时间越长,中毒的程度就越深,直至死亡。长期服用的结果,有的舌缩入喉,有的痈疽陷背,有的脊肉烂溃,有的痛苦异常得要自杀,有的因为应饮热酒却误饮冷酒而送了命。
至于以行貌绝美著名的何晏,在被司马懿所杀之前,善论阴阳的管略说何宴: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谓之鬼幽。可见,服用五石散没有也决不可能使他长期精力旺盛,反而伤了他的元气。
治服药方
 寒食散服草木之药则速发,须调饮食;金石者则迟起而难息。其始得效者,皆是草木盛也,金石乃延引日月。草木少时便息,石势犹自未盛。其有病者不解消息,便谓顿休,续后更服,或得病固药微,倍复增石,或便杂服众石,非一也。石之为性,其精华之气,则合五行,乃益五脏,其浊秽便同灰土。但病家血气虚少,不能宣通更陈瘀,便成坚积。若其精华气不发,则冷如冰。而病者服之望石入腹即热,既见未热,服之弥多。既见石不即效,便谓不得其力,至后发动之日,都不自疑是石,不肯作石消息,便作异治者,多致其害。道弘道人制《解散对治方》,说草石相对之和,有的能发动为证,世人逐易,不逆思寻古今方说,至于动散,临急便就服之,即不救疾,便成委祸。大散由来早难将之药,夫以大散难将,而未经服者,乃前有慎耳。既心期得益,苟就服之,已服之人,便应研习救解之宜,异日动之,便得自救也。夫身有五石之药,而门内无解救之人,轻信对治新方,逐易服之,从非弃是,不当枉命误药邪。检《神农本草经》,说草石性味,无对治之和,无指的发动之说,按其对治之和,亦根据本草之说耳。且大散方说主患,注药物,不说其所主治,亦不说对和指的发动之性也。览皇甫士安撰《解散说》及将服消息节度,亦无对和的发之说也。复有禀丘家,将温法以救变败之色,亦无对和的动之说。若以药性相对为神者,栝蒌恶干姜,此是对之大害者。道弘说对治而不辨此,道弘之方焉可从乎?今不从也。当从皇甫节度,自更改栝蒌,便为良矣。患热则不服其药,惟患冷者服之耳,自可以除栝蒌。若虚劳脚弱者,以石斛十分代栝蒌;若风冷上气咳者,当以紫苑十分代栝蒌。二法极良。若杂患常疾者,止除栝蒌而已,慎勿加余物。
寒食散服草木之药则速发,须调饮食;金石者则迟起而难息。其始得效者,皆是草木盛也,金石乃延引日月。草木少时便息,石势犹自未盛。其有病者不解消息,便谓顿休,续后更服,或得病固药微,倍复增石,或便杂服众石,非一也。石之为性,其精华之气,则合五行,乃益五脏,其浊秽便同灰土。但病家血气虚少,不能宣通更陈瘀,便成坚积。若其精华气不发,则冷如冰。而病者服之望石入腹即热,既见未热,服之弥多。既见石不即效,便谓不得其力,至后发动之日,都不自疑是石,不肯作石消息,便作异治者,多致其害。道弘道人制《解散对治方》,说草石相对之和,有的能发动为证,世人逐易,不逆思寻古今方说,至于动散,临急便就服之,即不救疾,便成委祸。大散由来早难将之药,夫以大散难将,而未经服者,乃前有慎耳。既心期得益,苟就服之,已服之人,便应研习救解之宜,异日动之,便得自救也。夫身有五石之药,而门内无解救之人,轻信对治新方,逐易服之,从非弃是,不当枉命误药邪。检《神农本草经》,说草石性味,无对治之和,无指的发动之说,按其对治之和,亦根据本草之说耳。且大散方说主患,注药物,不说其所主治,亦不说对和指的发动之性也。览皇甫士安撰《解散说》及将服消息节度,亦无对和的发之说也。复有禀丘家,将温法以救变败之色,亦无对和的动之说。若以药性相对为神者,栝蒌恶干姜,此是对之大害者。道弘说对治而不辨此,道弘之方焉可从乎?今不从也。当从皇甫节度,自更改栝蒌,便为良矣。患热则不服其药,惟患冷者服之耳,自可以除栝蒌。若虚劳脚弱者,以石斛十分代栝蒌;若风冷上气咳者,当以紫苑十分代栝蒌。二法极良。若杂患常疾者,止除栝蒌而已,慎勿加余物。

-
依韵和李舍人旅中寒食感事
2025-09-29 09:42:40 查看详情


 求购
求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