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希逸

崔希逸
简介
 崔希逸(?-738年),唐朝军事人物。开元九年(721年)任万年县尉,监察御史宇文融奏为劝农判官,迁监察御史。曾任吏部郎中。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自郑州刺史改任江淮河南转运副使,岁运百八十万石。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秋,以右散骑常侍知河西节度事。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袭吐蕃,破之于青海西,玄宗命右拾遗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塞宣慰,作《使至塞上》一诗,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三月,吐蕃寇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击破之。二十六年丙申,改河南尹,“自念失信于吐蕃,内怀愧恨,未几而卒”。事迹见《唐刺史考》卷四九,《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八十亦有传。
崔希逸(?-738年),唐朝军事人物。开元九年(721年)任万年县尉,监察御史宇文融奏为劝农判官,迁监察御史。曾任吏部郎中。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自郑州刺史改任江淮河南转运副使,岁运百八十万石。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秋,以右散骑常侍知河西节度事。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袭吐蕃,破之于青海西,玄宗命右拾遗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塞宣慰,作《使至塞上》一诗,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三月,吐蕃寇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击破之。二十六年丙申,改河南尹,“自念失信于吐蕃,内怀愧恨,未几而卒”。事迹见《唐刺史考》卷四九,《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八十亦有传。
履历
 (开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条上大悦。寻以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江淮、河南转运都使。以郑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萧炅为副。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这时的崔希逸已经官至郑州刺史(从三品),由御史台职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乣视刑狱,肃整朝仪”的监察御史,变成了一个地方大员。郑州,州治即在今天的河南省省会郑州市,在唐代是连通两京与河北道、河南道以及江南地区的重要交通要冲。开元时全州有户六万四千六百一十九,乡一百二十四。郑州当时也是漕运所经过的重要州郡之一,正因如此,玄宗在采纳了裴耀卿的建议之后任命了崔希逸为河南转运副使。崔希逸也不辱使命,三年间“运七百万石,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裴耀卿入相后,崔希逸接任了河南转运使,卓有成绩,“岁运百八十万石。其后以太仓积粟有余,岁减漕数十万石”。在此之后,崔希逸的生平再次出现了一段空白,直到开元二十四年开始的与吐蕃的战争。开元二十四年秋,崔希逸以中书省重要官员(右散骑常侍)的身份接任牛仙客为河西节度使,开始了他最为煊赫也最为怅恨的戎马生涯。
(开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条上大悦。寻以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江淮、河南转运都使。以郑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萧炅为副。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这时的崔希逸已经官至郑州刺史(从三品),由御史台职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乣视刑狱,肃整朝仪”的监察御史,变成了一个地方大员。郑州,州治即在今天的河南省省会郑州市,在唐代是连通两京与河北道、河南道以及江南地区的重要交通要冲。开元时全州有户六万四千六百一十九,乡一百二十四。郑州当时也是漕运所经过的重要州郡之一,正因如此,玄宗在采纳了裴耀卿的建议之后任命了崔希逸为河南转运副使。崔希逸也不辱使命,三年间“运七百万石,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裴耀卿入相后,崔希逸接任了河南转运使,卓有成绩,“岁运百八十万石。其后以太仓积粟有余,岁减漕数十万石”。在此之后,崔希逸的生平再次出现了一段空白,直到开元二十四年开始的与吐蕃的战争。开元二十四年秋,崔希逸以中书省重要官员(右散骑常侍)的身份接任牛仙客为河西节度使,开始了他最为煊赫也最为怅恨的戎马生涯。
后记
 其一,崔氏在隋唐时期是很有影响的名门望族,有唐一代,崔姓之人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记载:“崔氏定著十房:一曰郑州,二曰鄢陵,三曰南祖,四曰清河大房,五曰清河小房,六曰清河青州房,七曰博陵安平房,八曰博陵大房,九曰博陵第二房,十曰博陵第三房。宰相二十三人。”但是,查阅所有现在能见到的各种史书、家谱以及姓氏录,都未发现对崔希逸家世的任何记载。按照常理来说,有官至如此高品(凉州都督为从二品官)的族人,谱牒应该是记著其人的。但是根据现有资料来看,任何史料都没有相关记载,崔希逸的家世仍然是一个有待考证的疑问。其二,河西节度使使所凉州,位于河西走廊上的咽喉部位,是唐代中原地区与西域各国联系和交往的必经之路,也是切断唐王朝两大边患——吐蕃和突厥联系的最重要的闸门。“节度使”的职官名号也肇始于河西。唐代中央政府对河西节度使(惯例皆兼任凉州都督)的选任是非常慎重的,出任此职的一般都是一代名将。检《唐方镇年表》,有史可载的河西节度使共二十六人,其中两《唐书》有传者十六人,除遥领其职的李林甫外,其余皆为骁勇善战之人。
其一,崔氏在隋唐时期是很有影响的名门望族,有唐一代,崔姓之人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记载:“崔氏定著十房:一曰郑州,二曰鄢陵,三曰南祖,四曰清河大房,五曰清河小房,六曰清河青州房,七曰博陵安平房,八曰博陵大房,九曰博陵第二房,十曰博陵第三房。宰相二十三人。”但是,查阅所有现在能见到的各种史书、家谱以及姓氏录,都未发现对崔希逸家世的任何记载。按照常理来说,有官至如此高品(凉州都督为从二品官)的族人,谱牒应该是记著其人的。但是根据现有资料来看,任何史料都没有相关记载,崔希逸的家世仍然是一个有待考证的疑问。其二,河西节度使使所凉州,位于河西走廊上的咽喉部位,是唐代中原地区与西域各国联系和交往的必经之路,也是切断唐王朝两大边患——吐蕃和突厥联系的最重要的闸门。“节度使”的职官名号也肇始于河西。唐代中央政府对河西节度使(惯例皆兼任凉州都督)的选任是非常慎重的,出任此职的一般都是一代名将。检《唐方镇年表》,有史可载的河西节度使共二十六人,其中两《唐书》有传者十六人,除遥领其职的李林甫外,其余皆为骁勇善战之人。
历史记载
《新唐书》载:(崔希逸)既而与惠琮俱见犬祟,疑而死,诲亦及它诛。
《旧唐书》载:行至京师,(崔希逸)与赵惠琮俱见白狗为祟,相次而死。孙诲亦以罪被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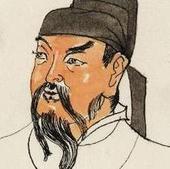
《资治通鉴》载:希逸自念失信于吐蕃,内怀愧恨,未几而卒。
新旧《唐书》的记载比较离奇,但符合古时人们的那种宿命心理。不管见没见到白狗作祟,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崔希逸是由于对失信于人的愧疚郁郁而终的,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古代人的观念是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周边的少数民族被视为蛮夷戎狄,与汉人相比,是低一等的。对待这些少数民族自然就可以不择手段,历史上的这种事例也是屡见不鲜的。崔希逸这种“迂腐”的想法自然是不能被别人所理解的,在史官的眼里,他的死也是不值得去同情的。这可能就是正史中都没有为其立传的一个重要原因吧。这一点也可以从正史对这场战役的记载中得到佐证。除了上面提到的两《唐书》吐蕃传的记载较为详尽外,其他几处对这次战役只是寥寥几笔提过,绝口未提这次战役发生的原因何在。甚至在记载中对这次掩袭的成功带有明显的炫耀口气:
三月乙卯,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自凉州南率众入吐蕃界二千余里。己亥,希逸至青海西郎佐素文子觜,与贼相遇,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
这里面就明显的带有中原汉族自我中心主义的观念。在这种观念占主流地位的情况下,崔希逸的那点信义也就不足为提了。
从正史中这些零散的崔希逸的生平事迹来看,他是一个才能卓越、文武兼备的人。从其他史料中对他其他一些事迹的记载来看,在人品上,他也是值得为人称道的。《大唐新语》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牛仙客为凉州都督,节财省费,军储所积万计。崔希逸代之,具以闻。诏刑部尚书张利贞覆之,有实。玄宗大悦,将拜为尚书。
这种能够褒前任之美而非据为己功的人,确实是不可多得的贤才。《太平广记》中,也收录有一条关于崔希逸的故事:
开元末,金坛县丞王甲,以充纲领户税在京。于左藏库输纳,忽有使者至库所云:“王令召丞。”甲仓卒随去。出城行十余里,到一府署。入门,闻故左骑常侍崔希逸语声。王与希逸故三十年,因问门者,具知所以,求为通刺。门者如白,希逸问此人何在,遽令呼入。相见惊喜,谓甲曰:“知此是地府否?”甲始知身死,悲感久之。复问曾见崔翰否,翰是希逸子。王云:“入城以来,为开库司,未暇至宅。”希逸笑曰:“真轻薄士,以死生易怀。”因问其由来。王云:“适在库中,随使至此,未了其故。”有顷,外传王坐。崔令传语白王云:“金坛王丞,是己亲友,计未合死。事了,愿早遣,时热,恐其舍坏。”王引入,谓甲曰:“君前任县丞受赃相引。”见丞着枷,坐庭树下。问云:“初不同情,何故见诬?”丞言受罪辛苦,权救仓卒。王云:“若不相关,即宜放去。”出门,诣希逸别。希逸云:“卿已得还,甚善。传语崔翰,为官第一莫为人做枉,后自当之。取钱必折今生寿。每至月朝十五日,宜送清水一瓶,置寺中佛殿上,当获大福。”甲问此功德云何。逸云:“冥间事,卿勿预知,但有福即可。”言毕送出。至其所,遂活。
在这个故事里,崔希逸成为了地府中的一个判官,类似于钟馗的形象。在这里恰恰反映出了人们对真实历史中崔希逸其人的认识和评价。出仕于名士,终世于信义,隐没于历史长河中的崔希逸,尽管在正史中没有取得一席之地,却赢得了后人的理解和尊敬。

-
逍客优惠6000元 写逸生活
2025-09-29 20:44:34 查看详情 -
成都哈弗H9最高优惠5000元 写逸生活
2025-09-29 20:44:34 查看详情 -
奥迪a8l霍希版落地价(奥迪a8l霍希版多少钱)
2025-09-29 20:44:34 查看详情 -
长安新款逸动PLUS正式上市 T运动版
2025-09-29 20:44:34 查看详情


 求购
求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