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卫马克思

保卫马克思
图书信息
书名:保卫马克思?
作者:路易·阿尔都塞(Althusser.L.)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0年10月1日
ISBN:9787100070294
开本: 16开
定价: 23.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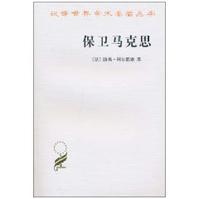
内容简介
《保卫马克思》名是一声呼喊,几乎是一个口号般的呼喊,今天它仍然在回响着,或者说它又一次回响起来,其声音还如同三十年前一样响亮。不过,这种回响有另外的原因,并且是处于完全不同的境况中的。阿尔都塞这部著作现在面对着新老的读者,而老读者们再次阅读阿尔都塞的著作之前,自身却已经有深刻的改变了,其接受作品的方式也有巨大的改变了。
图书目录
1996年重版前言
序言:今天
说明
一、费尔巴哈的“哲学宣言
二、论青年马克思(理论问题)
三、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
四、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
五、卡尔·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政治经济学与哲学)
六、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
七、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
关于“真正人道主义”的补记
致读者
生平传略
书评
关于唯物辨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林永青2007-04-05[2]
没有对思维的艰苦挑战,不建议阅读......
“凡是把理论导致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具体总体作为思维总体、作为思维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绝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凌驾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阿尔都塞也谈到列宁和毛泽东,他认为,“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里给我们留下的一些段落是辨证法的素描,(虽然没有从理论上来阐述);而毛泽东在1937年所著的《矛盾论》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发挥。”
毛泽东从矛盾的“普遍性”出发来论述矛盾,但他的根据也正是一条“普遍”原则: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毛泽东通过以下的普遍形式思考了矛盾的这条原则:矛盾始终是特殊的,特殊性普遍地属于矛盾的本质性。“人们或许会嘲笑毛泽东赋予普遍性的这个‘前提’,似乎普遍性需要一种附加的普遍性才能够产生出特殊性,人们甚至将这个‘前提’当作黑格尔的‘否定性’的前提。可是,真正懂得什么是唯物主义的人都知道,这个‘前提’不是普遍性的前提,而是对作为前提的普遍性提出的前提,其目的和结果恰恰是要禁止这一普遍性抽象化或产生‘哲学的’(意识形态的)欲念,并强迫它回到自己的地位上来,即回到具有科学特殊性的普遍性地位上来。假如普遍性应当具有这种特殊性,我们就不能说哪一种普遍性能够不是这种特殊性的普遍性。”......
如果你读到这里,还没有精神分裂,恭喜你......
[题外话]阿尔都塞虽然是法国人,但他基本上继承了17~19世纪德国思想家极具思辨的文风和述事方式。就我本人而言,我可愿意接受更为晚近的、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或分析哲学等学派,对思想的描述方式——说的诗化一点,它们比较“逻辑”。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界的赵鑫珊等人极力推崇德国的思辨文风的美学趣味,认为:“我要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康德”。然而,如果说康德、黑格尔过于“纯粹”,功利的或者懒惰的人们很少去理会他们。而马克思却是自他诞生之后的几个世纪中,谁也回避不了的思想家。我们还是要在德国人马克思的著作里用功。(也可能是译文用功与否的问题?马克思的作品还是相对可以解读的。)
编辑推荐
《保卫马克思》: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文摘
我将指出另外两个关注别的东西的“自我批评”。它们产生于不同的时刻,有着不同的目的。一个是人们可以看到存在于从“亚眠答辩”(1975,重版于1976年版的《立场》中,社会出版社)到写于1980年悲剧事件前后的一些特别具有暗示性(比如“偶然唯物主义”设想之必然性的暗示,这种唯物主义出现在1984年同费尔南德·纳瓦罗的“谈话录”中,它更多地受到伊壁鸠鲁而非现代辩证论者的启发)和特别言简意赅的作品中的。这个词语在他以前的作品中至多出现了一次,但是在1975年提交给博士学位评审委员会的“亚眠答辩”中,在涉及到矛盾和其自身的“不均衡性”时,阿尔都塞令人迷惑地宣称,如果没有同样也是根本性的亚决定(sousddtermination),多元决定就不能起作用:不是和同样结构中构成性的东西轮流在同样的因果决定中去起作用。①在此,我们甚至应该阅读这样一个被评论和补述所掩盖着的自我批评吗?我倒愿意做这样的建议。对我来说,由于它比别的更为建构性,所以更有意义。不过,同样确定的是,它所给出的标志——在解释了偶然的必然性之“结构”之后,仍然还要表达这种偶然的偶然,表达共存于同一事件中心的各种可能性和趋势之“亚决定物”的多样性——更多的是一个哲学纲领而非一个论题或一个假设。
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路易·阿尔都塞(Althusser.L.) 译者:顾良
序言
《保卫马克思》这一书名是一声呼喊,几乎是一个口号般的呼喊,今天它仍然在回响着,或者说它又一次回响起来,其声音还如同三十年前一样响亮。不过,这种回响有另外的原因,并且是处于完全不同的境况中的。阿尔都塞这部著作现在面对着新老的读者,而老读者们再次阅读阿尔都塞的著作之前,自身却已经有深刻的改变了,其接受作品的方式也有巨大的改变了。
当这部作品于1965年第一次出版时,它既是依某种方式、依这种方式的逻辑和准则解读马克思的一个宣言,也是保卫马克思主义,更确切地说保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与“党”以及运动不可分离的理论和哲学,并且被明确地要求着)的宣言。今天,也许除了那些试图在其中恢复往事,甚至是在想象中再次经历往事的怀旧的人之外,问题将是这样一个呼喊,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在马克思主义之后阅读、研究、讨论、运用,以及改变马克思,因为马克思主义不可逆地完成了。不过,这不是在对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之所是的忽视或蔑视中,在对把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的思想及我们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复杂性的忽视或蔑视中进行。

-
欧拉新款R1将于成都车展上市 全新宝马2系Coupe最新谍照
2025-09-22 09:52:04 查看详情 -
马自达3经典款钜惠13000元 车展钜惠
2025-09-22 09:52:04 查看详情 -
有望在5月底上市 全新宝马X5
2025-09-22 09:52:04 查看详情 -
广汽本田全新皓影正式上市 宝马1系M运动曜熠版上市
2025-09-22 09:52:04 查看详情 -
雪佛兰开拓者正式上市 全新宝马7系/i7正式上市
2025-09-22 09:52:04 查看详情 -
珠海英菲尼迪Q50L优惠达5.4万 成都新宝马3系优惠5万元
2025-09-22 09:52:04 查看详情 -
成都新宝马3系优惠5万元 再送装潢礼包
2025-09-22 09:52:04 查看详情 -
运良版牧马人战马上市 4月15日正式上市
2025-09-22 09:52:04 查看详情 -
德阳马自达6最高优惠3.7万元 最低多少钱
2025-09-22 09:52:04 查看详情 -
上海购金刚最高优惠1.3万 成都海马普力马现金优惠4千元
2025-09-22 09:52:04 查看详情


 求购
求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