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河小说

长河小说
简介
30年代至50年代在英国文坛较为流行的另一种小说样式便是安东尼·鲍威尔(Anthony Powell, 1905- )等作家创作的"长河小说"。它与传统的长篇历史小说或高尔斯华绥的世系小说具有很大的区别。它虽然由多部小说组成,但往往描写一个故事而不是多个故事;它提示的不是一个家庭或地区的变化,而是一个中心人物的经历与情感生活。
这就是界定的标准,像聊斋也是故事集,但是描写的截然不同的故事,这就不是了。
大多数现代小说与维多利亚时代以前的传统小说相比则更加简短,即便是由多卷组成的"长河小说",其每一部作品的篇幅也大都比较适中。 所以篇幅并不是绝对的标准。
来源
在《英国小说艺术的发展与演变》(上外,李维屏)中有这样一句: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中有两类作品较为引人注目:一是社会讽刺小说,二是由多卷组成的系列小说或"长河小说"(river novel)。
代表作品
长河小说以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最为著名 (它也是一部音乐小说)
在托尔斯泰《复活》 《战争与和平》就已经有长河小说的特色了 左拉《卢贡-马卡尔家族》基本上可以算是长河小说
中国现代文学中 李劼人(1891~1962)的长篇《死水微澜》,和他后来的《暴风雨前》、《大波》是比较重要的长河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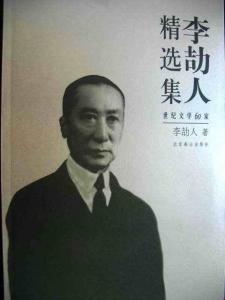 李劼人
李劼人
罗曼·罗兰作品简介
 当今年届七八十岁的老人,很多在意气奋发的青年岁月,都曾深深地陶醉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以音乐家为主题的长篇多卷本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它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他们的灵魂;而傅雷先生神奇的译笔,又为它增添了多重魅力。长达百万字的多卷本小说,在风行快餐式阅读的时代,早已被视为“文学恐龙”;但在上世纪初叶,它在法国文坛很风行,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马丁·杜伽尔的《蒂波一家》都是这类多卷本作品,它们如大江大河奔涌激荡,所以被称为“长河小说”。
当今年届七八十岁的老人,很多在意气奋发的青年岁月,都曾深深地陶醉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以音乐家为主题的长篇多卷本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它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他们的灵魂;而傅雷先生神奇的译笔,又为它增添了多重魅力。长达百万字的多卷本小说,在风行快餐式阅读的时代,早已被视为“文学恐龙”;但在上世纪初叶,它在法国文坛很风行,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马丁·杜伽尔的《蒂波一家》都是这类多卷本作品,它们如大江大河奔涌激荡,所以被称为“长河小说”。
欣悦的灵魂
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相比,罗曼·罗兰在晚年(1921-1933)创作的另一部长河小说《欣悦的灵魂》(罗大冈先生的中译本名为《母与子》),读者无疑要少得多。原文标题中的形容词Enchantée,既有中魔法、受魅惑之意,又可引伸为极度高兴、喜悦。全书法文合订本有1500页之巨,译成汉语约120万字。简直是一大块厚实的砖石,掉下来保证可砸死几只老鼠。尽管不时有沉闷之感,但还是被书中奔涌的情感之流裹挟住了。
和《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样,《欣悦的灵魂》也是一部音乐小说,尽管主人公并不是音乐家。它洋洋洒洒地描绘了女主人公安乃德·李维埃数十年曲折的人生路程。在罗曼·罗兰的笔下,生活不仅仅是外在的行动,更重要的是内心生活,他甚至以为“真正的生活是内心生活。”“这条漫长宽阔的内心之河”永不休止地奔涌着,她不断地陷入梦幻的诱惑;等美梦幻灭后,又直面新的魅惑,直至生命的终点。有趣的是,法文中安乃德的姓氏Rivière的原意就是河,在此,奔涌的河流与她的生命不可分离地合为一体。
如果用习见的小说规则来衡量,许多地方会显得罗嗦累赘拖沓,词不达意;但如果用音乐的目光来审视,一切都变得合情合理。作者原本就不是要写一部常规意义上的叙事作品,他企图由文字来表达奔腾不息的音乐之流,以交响曲的方式来展示多个主题。他在全书“导言”中写道:“无论它是什么样的,我这部作品是音乐。正如《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样,我把这部作品献给和谐,和谐是一切梦幻之女王,也是我毕生的梦。”
曾有不少人指责罗曼·罗兰的风格粗暴地破坏了法国语言明晰、准确的规范。的确,如果用福楼拜、莫泊桑精纯的文本相比照,罗兰激情四溢、狂放恣肆的文笔在雄壮高亢之余,有泥沙俱下之憾。但字里行间不时满溢而出的蓬勃的生命力,让人想起16世纪拉伯雷的《巨人传》。与17世纪后形成的典范的法语不同,拉伯雷百科全书式的风格具有一种雅俗兼容无所不包的气度,最粗鄙的笑话与最严肃的思考在狂欢的风格中比肩而立。罗兰的文体虽然达不到拉伯雷的丰富驳杂的境地,但其气势一脉相承。
而《欣悦的灵魂》中对主人公永不枯竭的生命力的讴歌,也让人联想起歌德的《浮士德》。在某种意义上,安乃德是浮士德在20世纪的变身,但她又确确实实是罗兰胸中孕育的果实,全书那种开朗、乐观、明亮的色调,不愧是地地道道的法国情调。尽管她也受到恶魔的蛊惑,但没有一个堪与靡非斯特相媲美的魔鬼形象登场。日耳曼式阴郁惶恐的色调在法兰西绚烂的阳光下找不到容身之地。
评价
时过景迁,罗曼·罗兰对生命力激昂慷慨的讴歌在今日富足和平的欧洲已成明日黄花,喧嚣了数个世纪的骚动似乎沉落到了慵懒的酣睡之中。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在市场经济和民主的笼子里安顿得慰贴无比,历史在此终结了,有的只是轻柔的浅吟低唱。也许只有在发生突变的未来,当人们需要再一次面对严酷的生存挑战时,他们衰朽的精神中会再一次响起罗曼·罗兰高亢激越的声响。

-
内斯比特幻想小说系列
2025-09-28 04:22:59 查看详情


 求购
求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