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
内容简介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分经、史、子、集四部分[4],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全书共4部44类66属。
- 经部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
- 史部收录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
-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
- 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5]
编纂背景
文化源流
传统学术自身的延续及发展,也在迫切要求当时的目录著作承担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责任,以经学为主的中国学术,历经了近二千年的发展历程,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直到清代汉学,期间渊源流变、兴衰利弊,都需要作出恰当评价。《四库全书》既然要囊括乾隆以前的历代典籍,那么,对传统学术的总结也就责无旁贷,因为传统目录学正是将典籍按照一定的体系加以排纂编次,进而通过文献典籍本身以及分类、编目、序录等方式来反映学术发展历史的。因此,编排历代典籍,总结评判传统学术,就成了《四库全书》编纂者的一项重要工作,《四库全书总目》也就由此应运而生。
时代风气
四库修书之前,出版业高度发达,典籍充分积累,藏书兴盛,文献整理工作全面展开,汉学成为主流学风。在时代学风下,学者们需要阅读大量藏书,以及许多完整的原著,以征引材料,考证学术源流。而对于自明末以来进入中国的西学,如何对待,到自觉检讨并总结以引导臣民认识西学,确立西学政策的时候了。在这种形势下,需要更大规模的行动,来做一次彻底全面的学术文化总结,也必得政府亲自出面主持方能完成这个任务。而拥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和雄才大略的乾隆帝,希冀超迈前人,并且他自己也完全有能力识断、调理文化。
皇帝自身
乾隆中期,经过一百多年的励精图治,清朝呈现出盛世景象。思想学术文化亟待总结的要求,政治经济的保障,以及乾隆个人的喜好,学术界的呼声,使中国传统的盛世修书在这个时候又展示出巨大魅力,催生出继顺康雍之后再次修纂大型书籍的态势。盛世的宏阔是需要鸿篇巨制来充实的,而清政府也需要完成时代留给自己的使命。
四库修书就表面而言,起于三方面。一是周永年自明末曹学佺再倡儒藏说,提倡集合儒书,与释藏、道藏鼎足而立。二是乾隆下诏直省督抚学政征求遗书,汇送京师。三是朱筠、王应采奏请校办《永乐大典》,辑佚书籍。但实际上是学术文化发展到总结时期,以及学术与政治的合力的需要。当然,乾隆想超越父、祖修书之功,尤其是超越祖父《古今图书集成》的私意也是不可忽视的。
历史沿革
编纂历史
- 提出辑佚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
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
- 整理图书
《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六个来源:内府本,即政府藏书,包括武英殿等内廷各处藏书;赞撰本,即清初至乾隆时奉旨编纂的书,包括帝王的著作;各省采进本,即各省督抚征集来的图书;私人进献本,即各省藏书家自动或奉旨进呈的书;通行本,即采自社会上流行的书;《永乐大典》本,即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6]
- 抄写底本
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
 四库全书(7)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
四库全书(7)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
- 校订过程
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为了存放《四库全书》效仿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的建筑建造了南北七阁。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鼐、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传世界。
流传情况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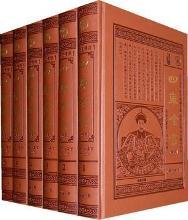 影印版(4)《四库全书》(1773年)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从那时开始,作为国家正统、民族根基的象征,已成为中国乃至东方读书人安身立命梦寐以求的圭臬和后代王朝维系统治宏扬大业的“传国之宝”。《四库全书》共收书3460多种、79000多卷、36000多册,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部”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10类;“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 15类;“子部” 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14类;“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05类。总共44类。为了保存这批精典文献,由皇帝“御批监制”,从全国征集3800多文人学士,集中在京城,历时十年,用工整的正楷抄书七部,连同底本,共八部。建阁深藏,世人难得一见。虽然由数千人抄写,但字体风格端庄规范,笔笔不苟,如出一人。所以,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赏价值。后几经战乱,损毁过半,更使这套世界出版史上的巨制,成为举世罕见的无价之宝。
影印版(4)《四库全书》(1773年)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从那时开始,作为国家正统、民族根基的象征,已成为中国乃至东方读书人安身立命梦寐以求的圭臬和后代王朝维系统治宏扬大业的“传国之宝”。《四库全书》共收书3460多种、79000多卷、36000多册,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部”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10类;“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 15类;“子部” 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14类;“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05类。总共44类。为了保存这批精典文献,由皇帝“御批监制”,从全国征集3800多文人学士,集中在京城,历时十年,用工整的正楷抄书七部,连同底本,共八部。建阁深藏,世人难得一见。虽然由数千人抄写,但字体风格端庄规范,笔笔不苟,如出一人。所以,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赏价值。后几经战乱,损毁过半,更使这套世界出版史上的巨制,成为举世罕见的无价之宝。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四库全书》正式开始编修,以纪晓岚、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陆费墀为总校官,下设纂修官、分校官及监造官等400余人。名人学士,如戴震(汉学大师),邵晋涵(史学大师)及姚鼐、朱筠等亦参与进来。同时,征募了抄写人员近4000人,鸿才硕学荟萃一堂,艺林翰海,盛况空前,历时10载。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编纂初成;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始全部完成。耗资巨大,是“康乾盛世”在文化史上的具体体现。
 纪晓岚(2)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四库全书》馆设立不久,总裁们考虑到这部书囊括古今,数量必将繁多,便提出分色装潢经、史、子、集书衣的建议。书成后它们各依春、夏、秋、冬四季,分四色装潢,即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集部灰黑色,以便检阅。因《四库全书总目》卷帙繁多,翻阅不易,乾隆帝谕令编一部只记载书名、卷数、年代、作者姓名,便于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的目录性图书。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总纂官纪昀、陆锡熊等人遵照乾隆帝的谕令,将抄入《四库全书》的书籍,依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逐一登载。有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问题,则略记数语。此书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告竣,共20卷。它实际上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中国古典文化典籍的分类,始于西汉刘向的《别录》。到了西晋荀勖,创立了四部分类法,即经、史、子、集四大部门。隋唐以后的皇家图书馆及秘书省、翰林院等重要典藏图书之所,都是按照经、史、子、集分四库贮藏图书的,名为“四库书”。清乾隆开“四库全书馆”,使成编时,名为《四库全书》。因为有了《四库全书》的编纂,清乾隆以前的很多重要典籍才得以较完整地存世。《四库全书》誊缮七部,分藏于紫禁城内的文渊阁、盛京(今沈阳)宫内的文溯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此为北四阁,又称为内廷四阁,仅供皇室阅览。另三部藏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即浙江三阁,又称南三阁,南三阁允许文人入阁阅览。中国近代,由于战乱不断,七部《四库全书》中完整保存下来的仅存三部。文汇阁、文宗阁藏本毁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文源阁藏本被英法联军焚毁;文澜阁所藏亦多散失,后经补抄基本得全,然已非原书。1948年,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往台湾,将故宫博物院的一些珍贵藏品运往台湾时,将《四库全书》中最为珍贵的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带到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现存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内。
纪晓岚(2)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四库全书》馆设立不久,总裁们考虑到这部书囊括古今,数量必将繁多,便提出分色装潢经、史、子、集书衣的建议。书成后它们各依春、夏、秋、冬四季,分四色装潢,即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集部灰黑色,以便检阅。因《四库全书总目》卷帙繁多,翻阅不易,乾隆帝谕令编一部只记载书名、卷数、年代、作者姓名,便于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的目录性图书。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总纂官纪昀、陆锡熊等人遵照乾隆帝的谕令,将抄入《四库全书》的书籍,依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逐一登载。有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问题,则略记数语。此书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告竣,共20卷。它实际上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中国古典文化典籍的分类,始于西汉刘向的《别录》。到了西晋荀勖,创立了四部分类法,即经、史、子、集四大部门。隋唐以后的皇家图书馆及秘书省、翰林院等重要典藏图书之所,都是按照经、史、子、集分四库贮藏图书的,名为“四库书”。清乾隆开“四库全书馆”,使成编时,名为《四库全书》。因为有了《四库全书》的编纂,清乾隆以前的很多重要典籍才得以较完整地存世。《四库全书》誊缮七部,分藏于紫禁城内的文渊阁、盛京(今沈阳)宫内的文溯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此为北四阁,又称为内廷四阁,仅供皇室阅览。另三部藏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即浙江三阁,又称南三阁,南三阁允许文人入阁阅览。中国近代,由于战乱不断,七部《四库全书》中完整保存下来的仅存三部。文汇阁、文宗阁藏本毁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文源阁藏本被英法联军焚毁;文澜阁所藏亦多散失,后经补抄基本得全,然已非原书。1948年,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往台湾,将故宫博物院的一些珍贵藏品运往台湾时,将《四库全书》中最为珍贵的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带到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现存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内。
修书毁史
清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大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为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馀种、8万馀块。除了焚毁书籍,大清还系统的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经全部被销毁了。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大清还系统的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
《四库全书》的编修可以说是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大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再如宋代《契丹官仪》记载辽国见闻:“胡人之官,领番中职事者皆胡服,谓之契丹官。枢密、宰臣则曰北枢密、北宰相。领燕中职事者,虽胡人亦汉服,谓之汉官。执政者则曰南宰相、南枢密。”四库本则篡改为:“契丹之官,领番中职事者皆异服,谓之契丹官。枢密、宰臣则曰北枢密、北宰相。领燕中职事者,虽国人亦汉服,谓之汉官。执政者则曰南宰相、南枢密。”改掉“胡服”、“胡人”等。
流失过程
《四库全书》其实是一部“四不全”的次品乃至废品。何谓“四不全”?因为在编修过程中,数目惊人的书籍遭到了焚毁、删削、篡改、错讹的厄运,而这一切都是蓄意为之。
一、焚毁
《四库全书》收录全文的图书一共有3461种,成书79000卷,近7.7亿字。编修中明令禁焚的书籍就有3000多种(估计禁毁6766部,93556卷),禁毁数超出收入的总数,这还不算上因当时诏令上缴违禁书籍在民间造成的恐怖氛围,百姓偷偷焚毁的书籍,合计起来被毁掉的书籍恐怕不止万部,这实在是空前绝后一场文化大浩劫。
二、删削
只举几例,据黄裳先生考证: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诏令:书籍内如有只须删改的字句,就不必因此而废掉全书;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禁网已注意到地方志;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注意力伸到野史诗、演戏曲本、小说等俗文学领域;乾隆五十年(1785年),改《明末纪事本末》中“吴三桂击走李自成”为“清军击走李自成”。
三、错讹
戊戌变法时支持新法的陕西进士李岳瑞,在其笔记《悔逸斋笔乘》中提到乾隆御制、四库馆臣校订的武英殿版《二十四史》。“曩读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惟《史》、《汉》、《国志》校勘无愧精审,《晋书》以次,则讹字不可枚举。”是四库馆臣的疏忽吗?不是。这是四库馆臣、内府官员、太监共同表演的取悦皇帝的“哑剧”——故意留下些容易看出的错误,等待喜欢校书的乾隆看到后标出,再对馆臣的“不学”降旨申斥,从而“龙心大悦”,觉得自己的学问也在“皆海内一流,一时博雅之彦”的四库馆臣之上。“然上虽喜校书,不过偶尔批阅,初非逐字雠校,且久而益厌。每样本进呈,并不开视,辄以朱笔大书校过无误,照本发印。司事者虽明知其讹误,亦不敢擅行改刊矣。”
从上述可以看出,毁、删、改,包括留下的大量错讹,都是蓄意而为。深究缘由,就不得不剖析乾隆编修《四库全书》的真实意图了。在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中,他鲜明地指出了清朝统治者编纂《四库全书》的真实用意:“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编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或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正如L.C.古德里奇所论证的,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7]
近代以来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抄,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文澜阁本在民国时期又有二次补抄。
民国三年(1914年)在杭州图书馆第一任馆长钱恂的支持下,由徐锡麟二弟徐仲荪及其学生堵福诜自费补抄,历时7年,史称“乙卯补抄”。民国十二年(1923年),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张宗祥得知徐仲荪、堵福诜的义举后,十分感动,但他知道“修补”量相当浩大,单靠几个人很难完成,必须由政府牵头。在他的重视下,补抄人员增加到百余人,费用全部由浙江籍人募集,徐仲荪任总校,堵福诜任监理,历时两年,史称“癸亥补抄”。解放初,由于徐仲荪和堵福诜修补《四库全书》有功,他们俩的画像曾被悬挂在杭州文澜阁,以志纪念。
1966年10月,当时正处于中苏关系紧张时,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林彪下令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从沈阳运至兰州,藏於戈壁沙漠中。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方面也修建藏书楼,加强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其最终归属仍处争议中。
2008年后《四库全书》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如今《四库全书》只存3套半,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现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本于1950年由中国政府下令调拨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而文澜阁本则藏于浙江省图书馆。[8]
2014年4月15日,一套原大原色原样复制的《四库全书》(文津阁本)运抵江苏扬州天宁寺万佛楼,18日开始对外展出。这套全书耗用手工宣纸6000刀、楠木函盒6144个、书架128个,它的复制从数码拍摄、数据修正、试制、正式生产到完工,前后历时十余年。
编纂人员
主要官员
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9]道号观弈道人。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直隶献县(今中国河北献县)人。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任《四库全书》总纂修官。代表作品《阅微草堂笔记》。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学问渊博,识断精审,思想邃密,是乾隆朝最著名的思想家,汉学代表人物。因博闻广识而破例允许他以举人身份供职于四库馆,担任《四库全书》的辑校工作。《四库全书》的主要纂修官。
陆锡熊(1734-1792),字健男,耳山,上海人。《四库全书》总纂官,卓有成效,受恩赏尤多。乾隆52年,清廷发现《四库全书》中有诋毁朝廷字句的书籍,乾隆帝大怒,令陆锡熊和纪昀负责重新修正,并由他两人分摊费用。时值隆冬,陆锡熊患病,终因心力交瘁,死于重校文溯阁《四库全书》的任上。可见朝野对《四库全书》之重视与严谨。
永瑢(1743-1790),乾隆帝第六子,号九思主人。乾隆末年被封为质亲王。喜作诗文书画,著有《九思斋诗钞》。《四库全书》馆正式成立后,乾隆帝为了表示对该项文化工程的重视,同时也为了加强对编纂工作的监控,命永瑢与永璇、永瑆,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刘统勋、于敏中为最高执行官即总裁,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宜。 《四库全书》智慧宝语荟要录。[10]
其他人员
| 分类 | 名单 |
|---|---|
| 任职人员:历任正总裁官(16人) | 永瑢永璇永瑆 刘统勋 刘纶 舒赫德 阿桂 于敏中 英廉 程景伊 嵇璜 福隆安 和珅蔡新 裘曰修 王际华 |
| 历任副总裁官(10人) | 梁国治 曹秀先 刘墉王杰 彭元瑞 金简 董诰 曹文埴 钱汝诚 沈初 |
| 总阅官(15人) | 德保 周煌 庄存与 汪廷玙 谢墉 达椿 胡高望 汪永锡 金士松 尹壮图李绶窦光鼎 倪承宽 李汪度 朱珪 |
| 总纂官(3人) | 纪昀(纪晓岚)陆锡熊 孙士毅 |
| 总校官(1人) | 陆费墀 |
| 翰林院提调官(22人) | 梦吉 祝德麟 刘锡嘏 王仲愚 百龄 张焘 宋铣 萧际韶 德昌 黄嬴元曹城瑞保 陈崇本 五泰 运昌 章宝传 冯应榴 孙永清 史梦琦 刘谨之蒋谢庭 戴衢亨 |
| 武英殿提调官(9人) | 陆费墀 彭绍观 査莹 刘种之 韦谦恒 彭元珫 吴裕德 关槐 周兴岱 |
书籍种类
| 分类 | 名单 |
|---|---|
| 任职人员:历任正总裁官(16人) | 永瑢永璇永瑆 刘统勋 刘纶 舒赫德 阿桂 于敏中 英廉 程景伊 嵇璜 福隆安 和珅蔡新 裘曰修 王际华 |
| 历任副总裁官(10人) | 梁国治 曹秀先 刘墉王杰 彭元瑞 金简 董诰 曹文埴 钱汝诚 沈初 |
| 总阅官(15人) | 德保 周煌 庄存与 汪廷玙 谢墉 达椿 胡高望 汪永锡 金士松 尹壮图李绶窦光鼎 倪承宽 李汪度 朱珪 |
| 总纂官(3人) | 纪昀(纪晓岚)陆锡熊 孙士毅 |
| 总校官(1人) | 陆费墀 |
| 翰林院提调官(22人) | 梦吉 祝德麟 刘锡嘏 王仲愚 百龄 张焘 宋铣 萧际韶 德昌 黄嬴元曹城瑞保 陈崇本 五泰 运昌 章宝传 冯应榴 孙永清 史梦琦 刘谨之蒋谢庭 戴衢亨 |
| 武英殿提调官(9人) | 陆费墀 彭绍观 査莹 刘种之 韦谦恒 彭元珫 吴裕德 关槐 周兴岱 |
收藏版本
由于《四库全书》由乾隆敕编,为了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需要,名为“稽古右文”,实则“寓禁于征”,大量搜罗、查禁、删改、销毁书籍。根据流传至今的几种禁毁书目和有关档案记载,全毁于2400多种,抽毁书400多种,铲毁、烧毁书版七、八万块。同时大兴“文字狱”,《四库全书》开馆后10年内竟发生了48起“文字狱”。而古书亡矣!”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文字狱如此。
- 善本:是指那些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或在其中某一方面有特殊价值的书本。一般来说,刊刻年代较早或经过精心校勘而错误较少的版本可称为善本。
- 孤本:某书的某一刻本或手稿。拓本在世间只有一份流传的为孤本。
- 秘本:私人收藏者秘藏于家室,置之高阁,不准许外人见阅的版本为秘本。
- 禁毁本:前代或当世之因遭禁被毁,侥幸私存下来的版本为禁毁本。在古代,保存这种禁毁本十分危险,一旦被当局发现,必遭大祸,因而其流传极其艰难。弥足珍贵。
- 绣像本:书中间有插图的版本为绣像本。这类绣像本书因其生动的表现形式而倍受欢迎,但因绘刻工艺复杂,价格昂贵而成品较少,因而现存的十分珍贵。
- 石印本:精选坚硬宽大而表面平滑的石头经打磨、雕刻制成石版,再用药墨将文字写在特制药纸上,将药纸上的字迹移置到石版上,然后滚刷油墨印成的书为石印本。
- 手抄本:根据底本抄写而成的书本。其中有一种影抄本,是把透明纸覆在底本上面,按其原有字体、行款照样摹写的书本。
- 残本:在流传过程中因种种原因(如运输、转卖、转抄、争执等)而残缺不全的书本为残本。
- 补本:对前代前人的著作有所增补,加以已意而写成的书。
- 续书:对前代前人的著作内容做继续的描写,以延续原著的意思为主旨。
- 保留本:因为某种私人目的而专门保留起来的书,一般是传家世代收藏保留,视为至宝。
- 经部: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
- 史部:正史类、编年类、记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
文宗阁版
文澜阁版
文宗阁位于镇江金山寺。文汇阁一名御书楼,位于扬州天宁寺西园大观堂。乾隆四十二年(1777)两淮盐政寅著领到颁贮扬州天宁寺行宫和镇江金山行宫的两部《古今图书集成》,奏请在行宫内仿天一阁规模建造藏书楼。乾隆四十四年(1779)镇江藏书阁建成,乾隆赐名文宗阁。次年扬州藏书阁建成,赐名文汇阁。两阁各入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阁中尚多空余书阁,后各收贮《四库全书》。道光二年(1842)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文宗阁本《四库全书》遭英军破坏。太平天国势力发展到江浙时,镇江、扬州被太平军攻克,文宗阁、文汇阁及其所贮《四库全书》一同化为灰烬。
文津阁版
杭州圣因寺行宫原有《古今图书集成》藏书堂一处,乾隆四十七年(1782)在堂后改建文澜阁,次年年底完工。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第二次攻下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大量散佚。杭州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收集残余,得到8140册,仅及原书四分之一。1864年太平军退走,丁氏兄弟又不惜重金从民间收购。光绪六年(1880)在旧阁原址上重建文澜阁。丁氏兄弟将书送还,并陆续抄补。民国后,归浙江省图书馆庋藏。1914年、1923年,两次组织人力就丁氏兄弟钞补未全者予以补钞。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始渐复其原。抗战时曾运至青木关,胜利后运回浙江,现藏浙江省图书馆。
文源阁版
在热河行宫(今河北省承德市)的避暑山庄。乾隆三十九年(1774),开始修建文津阁,次年修建完毕。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1784),《四库全书》入藏。1913年,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由国民政府运归北京,藏于文华殿古物陈列所。1915年,拨交新成立的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成为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每册卷首有“文津阁宝”,末页有“避暑山庄”、“太上皇帝之宝”小篆朱文方玺各一。史部的《八旗通志》成于嘉庆初年,后再补入,故里面仅有“嘉庆御览之宝”一方。全书与通行印本《四库全书目录》微有不同,盖以抄写较晚,有修订改易之处。[11]
文溯阁版
在圆明园内。园中“水木明瑟”之北稍西为文源阁,上下各六楹,阁西为“柳浪闻莺”。文源阁的匾额及阁内汲古观澜匾额都是乾隆皇帝御书。文源阁前为玲珑峰,上面刊有乾隆御制《文源阁诗》阁东的亭内有石碑,上刊御制《文源阁记》。文源阁本《四库全书》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抄毕入藏。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侵,大肆焚掠圆明园,文源阁本《四库全书》化为灰烬。今天,文源阁遗址已不可寻。刻《文源阁记》石碑尚存世间。
文渊阁版
在辽宁沈阳故宫内。乾隆四十七年(1782),第二部《四库全书》抄写完毕,送藏文溯阁。民国时期,文溯阁《四库全书》辗转流徙,几经危殆。1914年运京,存于保和殿。1925年,奉天教育人士拟办图书馆,呈请北京国民政府当局索回此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也落入日本人手中。日方曾假借所谓“国立图书馆”的名义代为封存。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才又回到人民手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战备需要,中央下令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从沈阳调出,运至甘肃存放至今。
文津阁版四库全书
位于紫禁城内的主敬殿后(主敬殿为文华殿后殿),建成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1782),第一部《四库全书》缮写告成,入藏阁内。民国时期,由故宫博物院接管。1933年春天,日寇侵略热河,北平地区形势十分危急。故宫博物院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连同所藏其他历代文物装箱南迁,运至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又辗转数千里运抵蜀中。抗战胜利之后复运抵南京。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时,运往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 阁名 | 所在地 | 建阁时间 | 成书时间 | 藏本存毁情况 |
| 文渊阁 | 北京故宫文华殿后 | 乾隆四十一年(1776) | 乾隆四十六年(1782) | 现存台北市外双溪故宫博物院 |
| 文溯阁 | 沈阳故宫 | 乾隆四十七年(1782) | 乾隆四十七年(1783) | 1966年由沈阳图书馆移存甘肃省图书馆 |
| 文源阁 | 北京近郊圆明园 | 乾隆四十年(1775) | 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 | 咸丰十年(1860)被英法联军烧毁 |
| 文津阁 | 承德避暑山庄 | 乾隆三十九年(1774) | 乾隆四十九年(1785) | 现存国家图书馆 |
| 文宗阁 | 镇江金山寺行宫 | 乾隆四十四年(1779) | 乾隆五十二年(1787) |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克镇江,阁书全毁 |
| 文汇阁 | 扬州天宁寺行宫 | 乾隆四十五年(1780) | 乾隆五十二年(1787) | 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攻克扬州,阁书全毁 |
| 文澜阁 | 杭州圣因寺行宫 | 乾隆四十七年(1782) | 乾隆五十二年四月 | 残存。现藏浙江省图书馆。 |
封装方式
| 阁名 | 所在地 | 建阁时间 | 成书时间 | 藏本存毁情况 |
| 文渊阁 | 北京故宫文华殿后 | 乾隆四十一年(1776) | 乾隆四十六年(1782) | 现存台北市外双溪故宫博物院 |
| 文溯阁 | 沈阳故宫 | 乾隆四十七年(1782) | 乾隆四十七年(1783) | 1966年由沈阳图书馆移存甘肃省图书馆 |
| 文源阁 | 北京近郊圆明园 | 乾隆四十年(1775) | 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 | 咸丰十年(1860)被英法联军烧毁 |
| 文津阁 | 承德避暑山庄 | 乾隆三十九年(1774) | 乾隆四十九年(1785) | 现存国家图书馆 |
| 文宗阁 | 镇江金山寺行宫 | 乾隆四十四年(1779) | 乾隆五十二年(1787) |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克镇江,阁书全毁 |
| 文汇阁 | 扬州天宁寺行宫 | 乾隆四十五年(1780) | 乾隆五十二年(1787) | 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攻克扬州,阁书全毁 |
| 文澜阁 | 杭州圣因寺行宫 | 乾隆四十七年(1782) | 乾隆五十二年四月 | 残存。现藏浙江省图书馆。 |
书籍对比
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是七部《四库全书》中的第四部,成书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原存于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入藏国家图书馆后,一直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与敦煌遗书、《赵城金藏》和《永乐大典》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善本四大专藏。
文津阁《四库全书》共36304册,分装6144个书函,陈列摆放在128个书架上。它是七部《四库全书》中保存最为完整,并且至今仍是原架、原涵、原书一体、乾隆御笔“题旧五代史八韵”刻在子部第32、33架的侧板上。书函中央板、丝带、铜环一依当年。翻开书册,即见“文津阁宝”朱印、“纪昀复勘”黄笺、雪白的开化纸和端正的馆阁体楷书,令人叹为观止。
文津阁《四库全书》具有独特的历史文献价值
第一, 从七部《四库全书》的成书时间来看,文津阁是北方四阁中最后完成的一部,距第一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成书已有三年之久,对已发现的讹误、遗漏当有所补正。
第二, 文津阁本是档案明确记载曾经乾隆亲校,并由纪昀亲自三校的抄本,几乎每册均有校核记录,其编校质量优于包括文渊阁本在内的其他诸本。
第三, 就仅存的三部半《四库全书》看,文津阁本保存最为完整,其他三阁本均分别据文津阁本加以补抄。经学者核对录异,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与文津阁本在篇卷、文字、《永乐大典》辑佚本、序跋、附录、提要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异。文津阁《四库全书》所保存下来的一些文献资料已是海内孤篇。
作品影响
文津阁《四库全书》共有楸木书盒6144个,内装书籍36304册。将书籍用木夹板上下夹住后,用丝带缠绕后放在书盒中。开启盒盖后,拉动丝带就可以方便地取出书籍。书盒盖刻上该部书籍的书名和所属部类顺序,清晰明了,便于查阅。
统治意义
《四库全书》收书和毁书数量:
先说收书:《四库全书》有不同版本,收书数量略有不同,第一份告成时收书3461种,79309卷,后来的文津阁本收书3503种、79337卷。
再说毁书:编《四库全书》毁、禁书数量不同专家给出不同数字,大致毁、禁、改书也达到3000余种。
乾隆把天下书收集来,一半毁了、一半收入《四库全书》。而且不仅毁书,还借此大行文字狱。以至于“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矣。
事实上,当时清廷征集到的书总共12237种,除了被收录和被毁禁外,那些编纂者认为价值不大的书,仅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这些存为书目的书是不允许留存和传播的,虽然没有明毁明禁,却不允许收藏,之所以只存个书目,不过是为了以示这些书知道就好,没有必要看罢了,实际上真的没有必要么?
 四库全书明末清初的科技科学著作都被付之一炬,明代《军器图说》罗列了各种火器,图文并举,叙说军器之制造,使用与威力等,却被焚毁。《崇祯历书》《天工开物》等决定着中国科技的一系列著作统统被毁,以至于后世之中华,不识不知科技为何物,积贫积弱。《军器图说》的那一句“夷虏所最畏于中国者,火器也”成了对满清修《四库全书》最大的嘲讽。
四库全书明末清初的科技科学著作都被付之一炬,明代《军器图说》罗列了各种火器,图文并举,叙说军器之制造,使用与威力等,却被焚毁。《崇祯历书》《天工开物》等决定着中国科技的一系列著作统统被毁,以至于后世之中华,不识不知科技为何物,积贫积弱。《军器图说》的那一句“夷虏所最畏于中国者,火器也”成了对满清修《四库全书》最大的嘲讽。
与《永乐大典》相比,相差何止毫厘?虽然《永乐大典》并没有向民间推行,但是它里面有的东西,民间都有,纵使不读,也不会存在你想知道的而没办法知道。但是《四库全书》就不一样了,推行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想让人知道他想让你知道的,你自己想知道的一些,他不想让你知道,你就永远也不会知道。全书都没有,那么这个东西就不存在,或者没必要存在。
正像文人鲁迅在批评明清和民国文人时表示:“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民国)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著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
文献意义
艺术价值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为名,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产物,乾隆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向全国征集图书,贯彻“寓禁于征”的政策,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
《四库全书》突出了儒家文献和反映清朝统治者“文治武功”的文献,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排斥了有民主色彩或敢于批评儒家思想的文献及戏曲和通俗小说如宋元杂剧、话本小说、明代传奇等。
作品评价
《四库全书》保存了中国历代大量文献。所据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贵善本,如宋元刻本或旧抄本;还有不少是已失传很久的书籍,在修书时重新发现的;也有的是从古书中辑录出来的佚书,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书有385种。《四库全书》的编纂,无论在古籍整理方法上,还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都给后来的学术界以巨大的影响。
《四库全书》保存中国历代不少接近失传的典籍,并校正典籍中的讹误脱漏。但修书期间同时抽毁及禁制一些书籍。乾隆一朝致力编修《四库全书》,但大兴文字狱,戕害读书人,对中国后来的科技文化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正面评价
- 规模亘古未有。全书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传世的经典文献,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
- 抄录和辑佚《永乐大典》中孤本书籍。“四库“馆臣先后共从《永乐大典》中辑得失传文献500余种,其中380余种收入《全书》,120余种列为《存目》。
- 对图书分类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标准和部别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文献传承的科学体系。乾嘉以后,凡编纂书目者,无不遵循其制度。
- 开创了多层次的古籍编撰和保存工程。用新造木活字排印流通100多种珍本秘籍,即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书》。开馆之初,命馆臣从应抄诸书中撷其精华,编纂《四库全书荟要》。建造南北七阁,大力倡导藏书文化,体现传统文化尊严和价值。
负面评价
成功原因
- 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是在某些方面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也有出版。
- 国学大师季羡林:嘉惠学林,功在千秋。
- 著名学者张岱年:传世藏书,华夏国宝。
- 研究员罗家祥:《四库全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杰作,一直被学界誉为东方文化的金字塔。
- 《解放军报》:《四库全书》几乎囊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12]
文物展出
- 四库全书其实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场表面上的古籍整理,实际上目的是将古代的文籍篡改以删去不利之处保留对其有利的部分。所以这并不是什么文化整理,而是粉饰的焚书坑儒,而且较之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大量珍贵的史料遭到篡改或销毁,不得不称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浩劫。
- 它的收集在客观上其实毫无价值,所谓的“整理之功”只不过是集聚篡改后的糟粕罢了。
- 鲁迅在批评明清和民国文人时表示:“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民国)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著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
- 吴晗:“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词条图册
《四库全书》之所以编纂成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值清王朝如日中天之时,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13]

-
青铜峡水库湿地自然保护区
2025-11-02 23:53:05 查看详情 -
山东莱钢泰达车库有限公司
2025-11-02 23:53:05 查看详情


 求购
求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