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费仲兴

费仲兴
主要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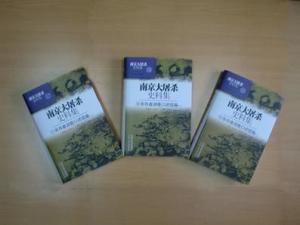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费仲兴主要著作有《线性代数》、《汤山觅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7卷和39卷、《城东生死劫》等。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费仲兴主要著作有《线性代数》、《汤山觅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7卷和39卷、《城东生死劫》等。
事迹介绍
“南京炮校”坐落于汤山镇,是南京的“东大门”,也是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向南京进攻的最后关口。平时,费仲兴喜爱骑车在学校周围遛弯。为了回答学生对“炮校”历史的追问,这位教授有时会探访附近村庄里的老人。
2001年5月的一天,宕山村年近80岁的崔广荣对费仲兴说起,75年前的春节,“炮校”附近的村庄曾被日军放火焚烧。
费仲兴很惊讶。此前他一直认为,南京大屠杀仅发生在南京城内及长江南岸。他跑图书馆、档案馆,查找汤山镇的这一段历史,几无收获。他开始琢磨着,要寻访在世的大屠杀见证者。
对费仲兴来说,这就像是一道“证明题”,需要严密的推论过程,且和所有学术研究一样,“来不得半点虚假”。
一碗稀饭下肚,跨上自行车,费仲兴一般早上7点就从学校出发。2001年他已年近60岁,体力正在衰退,最初他制定的目标是以“炮校”为圆心,半径15公里范围内的村庄,要挨个去一遍。
遇上村民他就打听,村上是否有80岁上下的老人健在。找到人,他先核实年纪,然后便问,“还记得跑反时的事?”“跑反”就是躲避战祸,在汤山工作多年,费仲兴熟悉这里的方言。有些老人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南京大屠杀”,但说起“跑反”的经历,“他们刻在脑子里一样,清清楚楚。”费仲兴说。
“现在讲这些还有什么用呢?”一位老人曾反问他。“我要把你吃过的苦记下来,讲给我的学生听。”他答。
最初两年,他的调查只在周末进行。 2004年退休后,只要时间和天气允许,他都会一早出发,调查的范围也逐渐扩大。
“再不搞清楚,就来不及了。”费仲兴觉得时间越来越紧迫,当年见证历史的老人,正在大批逝去,他停不下来。
早上出门,中午回家,下午把谈话记录整理好,再敲进电脑里——费仲兴严格遵照着这样的时间表。在他书柜的底层,摞着十几本笔记,翻开来看,除了密集写满行间的口述,更显眼的是间或出现的一组组人名。
“说清楚一件事,要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费仲兴扳着手指头慢慢说道,然后他竖起大拇指,重重地强调:“这几个要素中,人是核心。”
 费仲兴在言家村与村民交谈因此,人名是费仲兴最看重的事。在他看来,每个名字都曾是一个具体的生命,他要记下他们生前的样貌和临终的惨状。大部分遇难者姓名完整,但也有“小道士”、“秦大饼”这样的绰号。老人说不出完整名字的,费仲兴就在姓氏后画上圆圈。
费仲兴在言家村与村民交谈因此,人名是费仲兴最看重的事。在他看来,每个名字都曾是一个具体的生命,他要记下他们生前的样貌和临终的惨状。大部分遇难者姓名完整,但也有“小道士”、“秦大饼”这样的绰号。老人说不出完整名字的,费仲兴就在姓氏后画上圆圈。
有时,为了确认一名遇难者,他要找好几位老人独立叙述,相互印证。90岁的庞家边村民刘素珍曾目睹日军“削梨一样”屠杀了13名“跑反”者,费仲兴花了3年时间才找到他们的原籍,证实刘的口述,并获知8个姓名。
一个有价值的访问对象,费仲兴至少要谈3次,最多的要谈十几次。费仲兴习惯先让被调查者“无拘无束敞开来聊”。事实上,除了拍照和确认细节,最后他还会将整理好的材料逐字逐句读给老人听,让他们审校事实。
事迹影响
20个世纪80年代,南京市政府曾发动全市力量,找到大量当年的大屠杀幸存者、遇难者家属进行口述回忆。但这一调查,并未将城外、郊区发生的屠杀纳入统计。
从2004年起,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先后3次立项资助费仲兴的调查。在合作开展的研究活动中,他为志愿者们做方言培训,也为暑期实践的大学生担任领队。
“手把手地教是费老的一贯作风。”王民田回忆道。
一些了解他的同事和学生也曾因钦佩和好奇跟随他走街串巷,寻访老人,但“去个一两次就不再去了”。
身边的同道来来去去,只有费仲兴仍数年坚持奔走在田野调查的路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叫“走进历史的深巷”。然而,这“深巷”中,能被他觅得的人和事,都正在消失。
“这可以说是抢救性的工作。”戴袁支表示。
费仲兴把访谈对象的照片翻得哗哗响,“看这个,再看这个,不过一两年,这几位都不在了。”
在能够被回忆和陈述的往事里,有人失去家人,有人失去邻居和朋友,有人在刺刀下受了重伤,有人至今因受枪声刺激而听不得鞭炮响。“但大多数人都很平静。”费仲兴表示,“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
几年下来,他跑遍了汤山地区3个镇子100多个村庄,超过半数遇难者的故事和名单,是他用自行车蹬回来的。因为身体日渐衰老,他添置了电瓶车。要去更远的地方,他就坐长途汽车。熟悉他的师生遇见他总会问,“又出去啦?今天去哪?”
访查结果
最终,费仲兴的名单上共有834个名字。他收集来的口述被编入《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他寻访来的名字被刻上遇难者名单墙。
比起名单上的逝者,费仲兴同样关注幸存者。在访问过的350位老人中,他帮助22人成功申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放的“幸存者证书”,从而让他们得到生活补贴,很多人的子女都和他保持着联络。戴袁支戏称,“老费好人一个,是军民关系搞得最好的军人”。
83岁的潘巧英至今记得父亲被日军刺死时的景象。那时她只有7岁,前一刻刚饱餐了一顿肉菜,蹦蹦跳跳地出门去玩。后一刻,她已躲在炉膛边的柴草里,眼睁睁看着刺刀把自己变成孤儿。带着这位幸存者,2011年12月,费仲兴受邀登上了日本8座城市的南京大屠杀证言集会论坛。某次宣讲,日方反对者用喇叭对着会场高声抗议。然而,他并未感到畏惧,“因为说的是真话,所以一场比一场讲得更好。”
历史的证言藏在每一个细节里。比对着如今的“炮校”办公楼,费仲兴举起一张黑白照片。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还是不难看出,照片里拍摄的正是那座颇为宏伟的建筑。
费仲兴不想煽动民族仇恨。他也会用佳能牌数码相机,更不反对人们购买日货。对于中日关系问题,这位老人读报纸、看电视,保持关心,谨慎谈论。
只是当日本人拿出种种证据,证明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时,他心里就较劲儿了。“这重要、那重要,还有什么比教育下一代更重要呢?”作为老师,他希望自己能让学生以史为鉴。而作为数学研究者,他更想为这道“历史的证明题”提供“证明条件”。
2003年,南京汤山湖山村建起了民间第一块纪念大屠杀遇难村民的石碑。上面刻有费仲兴等人提供的名字,建设也有他的捐款。此外,他还查清了1938年春节日军在西岗头制造大屠杀惨案的真相。2006年清明,在南京市江宁区西梅村西岗头,另一块更大的纪念碑高高耸起。
“费仲兴教授堪称南京大屠杀民间调查第一人,一位非历史专业出身的南京大屠杀研究方面的专家。”在为费仲兴撰写的书稿《城东生死劫》作序时,张连红写道。
在这面中国的“哭墙”上,已经刻下1 万多个名字。然而费仲兴总觉得,比起30万,这面墙还显得空空荡荡。

-
泸州华润兴泸燃气有限公司
2025-08-25 23:00:53 查看详情 -
江苏兴洲工矿设备有限公司
2025-08-25 23:00:53 查看详情


 求购
求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