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衙北司之争

南衙北司之争
产生背景
唐代宦官得势是从唐玄宗时开始的。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内廷宦官激增至3000人,官至五品以上的即达三成。像玄宗宠侍高力士更是显赫一时、贵盛无比,连当朝太子都称其为二兄,更不用说其他的王公大臣了。自太子以降,诸王公主称他为阿翁,驸马之流称他为爷。不过高力士虽然显贵,但是权势还不是很大,朝政始终还是掌控在皇帝和大臣的手中。
 南衙北司之争配图(5)自天宝后,宦官专政成为唐后期历史上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自韦后之乱至玄宗即位,宦官都有参与官廷政争。而自安史之乱后,李辅国策立了一次不露痕迹的政变,拥立肃宗后,唐肃宗李亨因强藩作乱险亡其国而疑忌将帅,开始用自己宠信的宦官李林辅统帅禁军,开始了宦官掌权的先例。至唐代宗时,宦官的势力又进一步膨胀,充任内枢密史,掌管机密,承诏宣旨。至此,宦官开始逐渐的控制了军队和朝政,而皇帝确逐渐的控制不了宦官,甚至反被宦官所控制。《旧唐书》云:“自贞元之后,威权曰炽,兰钅奇将臣,率皆子畜;藩镇戎师,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
南衙北司之争配图(5)自天宝后,宦官专政成为唐后期历史上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自韦后之乱至玄宗即位,宦官都有参与官廷政争。而自安史之乱后,李辅国策立了一次不露痕迹的政变,拥立肃宗后,唐肃宗李亨因强藩作乱险亡其国而疑忌将帅,开始用自己宠信的宦官李林辅统帅禁军,开始了宦官掌权的先例。至唐代宗时,宦官的势力又进一步膨胀,充任内枢密史,掌管机密,承诏宣旨。至此,宦官开始逐渐的控制了军队和朝政,而皇帝确逐渐的控制不了宦官,甚至反被宦官所控制。《旧唐书》云:“自贞元之后,威权曰炽,兰钅奇将臣,率皆子畜;藩镇戎师,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
宦官势力的膨涨,侵害了旧有官僚集团的利益,宦官控制朝廷,不仅威胁皇帝,而且因利所趋,无事不争,这便和朝臣发生冲突。日积月累,矛盾便开始激化。于是官僚集团便与宦官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变逐渐开始,尤其是王坯、王叔文铲除宦官未果后,宦官更为猖獗。[1]
主要后果
宦官专权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政治方面,他们分帮结派,争权夺利,营私舞弊,以至废立皇帝,使政治更加黑暗混乱。在军事方面,各镇和出征军队中,都有宦官监军,破坏了军队的统一指挥,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削弱了朝廷对藩镇叛乱势力及民族反抗势力进行斗争的能力。在经济方面,宦官大肆掠夺百姓的田产,又通过“宫市”,强买货物,敲诈勒索。总之,宦官专权加重了人民的痛苦,使唐后期的政治和社会矛盾更加尖锐。[2]
代表事件
二王八司马事件
唐朝中期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二王八司马事件(805年),或称永贞革新,就是十几次影响较大的改革之一。这次彗星般耀眼而短促的革新,由于两位旷世文豪刘禹锡和柳宗元的深深卷入,更加令人瞩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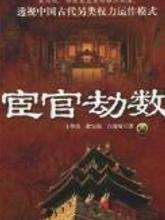 南衙北司之争相关图书王叔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出身寒微,颇知民间疾苦,是庶族文人中的优秀分子,一位有抱负、有活动能力的政治家。他先得到德宗的赏识,把他从苏州司功参军提到朝中任翰林待诏。贞元三年(788年),又因善于下棋而被德宗选去太子身边侍读,陪伴太子近二十年。在太子李诵身边,王叔文经常对他讲叙民间疾苦。有一次太子与诸侍读等一起议论宫市害民。李诵说:“我正要好好向皇上说这件事。”大家都加以称赞,唯独王叔文一言不发。众人退下后,李诵问王叔文刚才为何不说话,王叔文说:“太子的职责是侍奉皇上的饮食和请安,不应过问朝事。皇上在位已久,如果怀疑太子收买人心,你如何解释?”太子深感王叔文很有办事经验和对他的忠心。
南衙北司之争相关图书王叔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出身寒微,颇知民间疾苦,是庶族文人中的优秀分子,一位有抱负、有活动能力的政治家。他先得到德宗的赏识,把他从苏州司功参军提到朝中任翰林待诏。贞元三年(788年),又因善于下棋而被德宗选去太子身边侍读,陪伴太子近二十年。在太子李诵身边,王叔文经常对他讲叙民间疾苦。有一次太子与诸侍读等一起议论宫市害民。李诵说:“我正要好好向皇上说这件事。”大家都加以称赞,唯独王叔文一言不发。众人退下后,李诵问王叔文刚才为何不说话,王叔文说:“太子的职责是侍奉皇上的饮食和请安,不应过问朝事。皇上在位已久,如果怀疑太子收买人心,你如何解释?”太子深感王叔文很有办事经验和对他的忠心。
王伾,杭州人。以书法见长,为太子侍读,与王叔文二人颇得太子信任。通常讲的“二王八司马”的“二王”即指王还与王叔文。
与王叔文、王伾一块儿共商国是的还有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韩泰、凌准、韩晔、程异、陈谏等人。此外,还有吕温、李景俭、陆质等,也与革新集团关系密切。
李诵在太极殿即位后,开始名正言顺地行使皇帝权力,进行政治革新。
他上台仅25天,就贬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李实是皇族宗室,作恶多端,百姓深受其害。自从任京兆尹,他恶性不改,聚敛财富,又枉杀无辜,百姓对他深恶痛绝。顺宗一上台便将他贬官,使百姓人人拍手称快。两天后,顺宗又在丹凤门上宣布:“赦天下,诸色逋负,一切蠲免,常贡之外,悉罢进奉。贞元之末政之为人患者,如宫市、五坊小儿之类,悉罢之。”免除民间欠税和一切杂税,停止地方官对朝廷常贡以外的其他进奉,减轻了人民的负担。革除弊政最有影响力的是整饬宫市和五坊小儿的措施。所谓的“宫市”,是指皇宫的官吏出外采购宫中用物,本来由专设的官吏采办,德宗贞元末改由宦官掌管。宦官或以低价强买,或索性派一批人,叫“白望”,看中什么就白拿强抢。百姓见了他们犹如见了强盗一般。白居易的《卖炭翁》写的就是这种情况。五坊即雕、鹘、鹞、鹰、狗五坊。在五坊服务的差役称“小儿”,均由宦官担任。他们以打猎为名,把捕鸟的网张在老百姓的家门口或水井上,借机敲诈勒索。禁止宫市与五坊小儿,百姓自然拥护叫好。此外,顺宗还放出宫女和女乐九百多人,家人团聚,欢呼万岁。
其次是控制理财权。任命当时的理财名臣杜佑为盐铁转运使,王叔文为副使,免去李琦的盐铁转运使职务。再者是准备剥夺宦官兵权。任命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但这一着棋,没有落到实处。在任命下达后,执掌神策军实权的大宦官立刻意识到这是“二王”的夺权行动。于是密令神策军将领不得接受范、韩的命令。此外还打算裁抑藩镇。这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提出要拥有剑南三川,以扩大自己的地盘。王叔文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还准备将他的心腹刘辟正法。
由于唐顺宗病重不能言语,加上宦官和守旧势力凶狠反扑,使革新最终只经历了短短的六个月便告失败。宦官俱文珍等逼顺宗下制让位给太子李纯。不久顺宗又被迫下制书令太子即位为皇帝,自称为太上皇,改元为永贞。顺宗的退位,意味着永贞革新的彻底结束。
唐宪宗即位后,二王等人纷纷下台。宪宗随即宣布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马。不久,王伾死于开州,王叔文也于第二年被宪宗赐死。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马,韩泰被贬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至此,因二王而被贬的八人均到地方上任“司马”,故人们将这一事件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3]
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发生在唐文宗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当日早朝之时,百官群集。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奏称金吾左仗院中有甘露夜降石榴树,请皇帝亲往观看。树木之上凝有甘露,本来是极其平常的事。如果是在夏秋之季,确实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当时是十一月下旬。地处北方的长安已经十分寒冷了,不太可能有甘露。如果偶尔真有甘露降临,就会被看作是大吉大利的兆头。因此,当韩约称甘露降于皇宫之内,百官立即向文宗拜贺,李训、舒元舆请文宗亲观此祥瑞。金吾左仗院在含元殿左前,文宗与百官到了含元殿内,命宰相李训及中书、门下两省官前往核实。李训去金吾左仗院察看后,报告文宗说:“恐怕不是真的甘露,不敢轻言。”文宗又命左右神策军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等宦官再去验看。这时,金吾院中早已设下伏兵,其实是引诱诸宦官到金吾院内,围而杀之。宦官走后,李训急召守在丹凤门外的兵士进宫以备接应,但将军王璠却因害怕而不敢前行。他手下的士兵虽然到了含元殿下,但却吓得不能正常行走到含元殿。而另一支由郭行余统领的接应部队更是连影子也不见。一时间,含元殿下乱成一团。
再看仇士良等诸宦官,由韩约陪同前往金吾院。韩约因紧张过度而面色发白,汗流不止。仇士良正觉奇怪.恰巧一阵风吹过,吹动布幕,露出伏兵。仇士良大惊,率诸宦官连忙退出金吾院,奔回含元殿。守门人想要把殿门关上,被仇士良一声厉喝,吃了一惊,竟来不及把殿门关上。李训急呼卫士上殿保驾,已经来不及了。宦官对文宗说:“事急矣,请陛下还宫!”即把文宗扶上软舆,准备回宫。李训上前阻止,仇士良大呼李训造反!文宗却说李训不是造反。仇士良将李训击倒,李训还是抓住软舆不放。这时,金吾卫士已到,京兆少尹罗立言率京兆府三百多人从东面来,御史台中丞李孝本率御史台从人两百多人从西面来,三方纵击,宦官死伤十多人。此时,御驾将入宣政门,李训仍抓住软舆阻止宦官把文宗抬进宫。但文宗见大势已去,便呵斥李训放手。御驾进了宣政门,宦官把宫门关上,高呼万岁。百官见文宗落入宦官手中,均知大事不妙,四散而去。李训知道大势已去,就穿上随从小吏的绿色衣服,骑马逃出长安。
不久,宦官调集禁军大杀朝官。李训、郑注、王涯、舒元舆、王璠、郭行余等17人被杀,其族人也无一幸免,朝中几乎为之一空。文宗也差点被废,此后就纯粹成了宦官手中的傀儡,最后忧郁而死。这便是唐代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4]
相关知识
南衙北司
唐代,以宰相为首的政府机构称为南衙,由宦官掌握的各种机构称为北司。南、北本是由于这些机构在宫城和皇城中的位置而得名。宰相议政的政事堂及中书、门下二省在宫城内南部,尚书省及六部、九卿、三监则在宫城之南的皇城内。
唐初内侍省机构原本并不复杂,所领六局都是为皇帝及后妃生活起居服务的但到后来,由于皇帝宠信,宦官逐渐掌握武力,干预政事。如武则天时出现的内飞龙使,名为管理御马,实际掌握一支武装。唐中宗、唐玄宗以后,更以宦官监军,或直接以宦官统领军队(如玄宗时的杨思勗)玄宗晚年深居后宫,宦官高力士等把持了呈进章奏、承宣诏命之权,太子、宰相等都不敢得罪他安史之乱以后,由宦官充任的官职逐渐增多,如唐肃宗时出现的观军容使,唐代宗时出现的掌枢密,特别是唐德宗时出现的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简称神策中尉)控制了禁军及朝廷机密,势力远在外庭朝官之上。当时,又和外庭机构相对应,设立了许多由宦官掌握的使职,如宣徽使、学士使、内弓箭库使、内庄宅使等,其衙门通称为司,故有北司之称。[5]

-
长安除魔司之危机不夜城
2025-09-22 16:43:36 查看详情 -
全新梅赛德斯 或再创纽北赛道圈速纪录
2025-09-22 16:43:36 查看详情 -
北京北机机电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5-09-22 16:43:36 查看详情


 求购
求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