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
基本简介
形成
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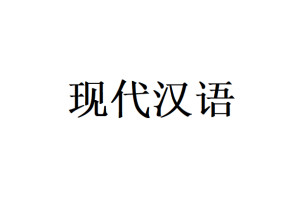 现代汉语同语是在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方言叫做基础方言。哪一种方言能成为共同语言的基础方言,取决于该方言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因素。
现代汉语同语是在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方言叫做基础方言。哪一种方言能成为共同语言的基础方言,取决于该方言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因素。
形式
书面语和口语构成了语言的不同存在形式。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语言叫书面语。口语指的是日常口头应用语。
特点
(一)语音方面
(1)没有复辅音
(2)元音占优势
(3)音节整齐简洁
(4)有声调
(二)词汇方面
(1)单音节语素多,双音节词占优势
(2)构词广泛运用词根复合法
(3)同音语素多
(三)语法方面
(1)汉语表示语法意义的手段不大用形态
(2)词、短语和句子的结构原则基本一致
(3)词类和句法成分关系复杂
(4)量词和语气词十分丰富
普通话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
主要分支
现代汉语方言差异显著。关于方言的分区,学术界的观点还不同意,有7区说、10区说等。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联合编制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将汉语方言分为官语、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语、晋语、徽语、平话10个区。
官方方言
官方方言也称官话或北方方言。官方方言通行范围很广,从东北三省到云贵高原,从江苏的连云港到新疆内陆的汉族居住区,都有官话分布。
吴语
吴语也称江南话,江浙话。吴语分布在江苏南部、上海和浙江,以及江西、福建和安徽的小部分地区。以苏州话或上海话为代表,使用人口一亿。
湘语
湘语也称湖南话。湘语分布于湖南的湘江、资江流域和沅江中游少数地区以及广西北部的兴安、灌阳、全州、资源四县,按照一般说法,湘语以长沙话为代表。
赣语
赣语也称江西话。赣语分布于江西省的赣江中下游和抚河流域以及鄱阳湖地区,湘东、湘西南、鄂东南、皖西南等地也有分布,使用人口4千万。
客家话
客家话也称客话,以广东梅县话为代表。客家话主要分布在广东中部、东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此外,台湾、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也有小片分布,共200多个县市,大约3500万人。
粤语
粤语也称白话,以广东话为代表。粤语分布于广东珠江三角洲、粤中、粤西南及粤北的部分地区,广西的桂东南,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也是海外华人社区的主要交际语之一,使用人口约8千万。
闽语
闽语以福建话为代表。闽语分布于福建沿海大部分地区,广东潮汕地区和雷州半岛,海南东部、南部和西南部沿海,浙江东南部,台湾大部分地区,使用人口约6千万。
晋语
晋语指山西省及其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分布在山西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河南北部、河南北部南部。以太原话为代表,使用人口4570万。
徽语
徽语分布于黄山以南,新安江流域的安徽旧徽州府全境,浙江旧严州府大部及江西旧饶城府小部分地区,共约2.5万平方公里,使用人口320万。
平话
平话分布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要道附近的城市郊区、乡镇和农村。从桂林以北的灵川向南,沿铁路到南宁形成主轴线,鹿寨以上为北段,是桂北平话分布地区;柳州以下为南段,是桂南平话分布地区。使用人口200多万。
发音
(1)每个音节都有声调。汉语音节(差不多相当于汉字)的高低升降,都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例如“汤、糖、躺、烫”四个音节,声母和韵母都相同,之时因为音高变化不同,表示的意义就不一样,写出来也是四个不同的字。这种音节上区别意义的音高变化就是“声调”。普通话有四个声调,分别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简称“四声”。
(2)音节构造简单而有规律。汉语是单音节性很强的语言,音节界限特别分明。汉语里音节是一般人都能感知的基本的发音单位,几乎每个音节都有意义。汉语的音节结构构造严密,每个音节都由声母、韵母和声调三个部分构成。
语音
语音的定义
语音的定义
语音是人的发音器官发出具有一定意义的声音。
语音的性质
物理属性
1.音高:指声音的高低,它取决于发音体振动的快慢。
2.音强:指声音的强弱,决定于声波振幅的大小。
3.音长:指声音的长短,决定于发音体振动时间的长短。
4.音色:指声音的特色,决定于音波颤动的形式。
生理属性
语音是由人的发音器官发出来的,因而具有生理性质。发音器官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1.肺和气管
2.喉头和声带
3.口腔、鼻腔和咽腔
社会属性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具有社会性。社会性也是语音的本质属性。
语音的概念
音素
音素是从音色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的语音单位。
元音
元音是发音时气流振动声带,在口腔咽腔不受阻碍而形成的音。
辅音
辅音是发音时气流受到阻碍形成的音。
元音和辅音的主要区别
1.气流是否受阻
2.紧张均衡与否
3.气流强弱
4.声带是否颤动
音节
音节是语音结构的基本单位,是听觉上最容易分辨的语音单位,也是最自然的语音单位。
声母
声母指音节开头的辅音,如果音节开头没有辅音,则称为零声母。
韵母
韵母是指音节中声母后边的部分,它可以是1个元音,或者是元音的组合,也可以是元音和辅音的组合。
声调
声调指整个音节的高低升降变化。
音位
音位是一种语言(或方言)里能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
词汇
语素
语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
词
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使用的语言单位。
词汇
词汇又称语汇,是一种语言里所有词和熟语的总汇。
语法
定义
语法是语言的构造规则。
性质
1.抽象性
2.稳固性
3.系统性
4.民族性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语音
第二章现代汉字
第三章词汇
第四章语法
第五章修辞
编辑推荐
《现代汉语》(增订4版)(上)上下册后各附网络资源登录账号和登录密码,通过它们,读者可以登录高等教育出版社网站,获取更多的多媒体学习资源,诸如与各章内容相关的参考资料、书后新增"补充练习"的参考答案,以及国家发布的相关语言文字法规。
文摘
第二节 词 义
一、什么是词义
词义是外在的事物或现象在人类意识中的反映。人们通过感官感知这些事物或现象之后,由大脑加以分析和综合,形成一种认识,同时用语音形式将其记录和固定下来,这样,就构成了词义,即语词所表达的意义内容。每一个实词都包含有一个以上的意义,每一个虚词也都有自己的含义(语法意义)。词的意义和声音的结合不是天生的,以什么样的声音表达什么样的意义,是这个词在产生时由人们规定的,这种规定具有任意性质。例如同是猫,汉语用mao这一声音来表达,英语则用cat这样的声音来表达。但是,音义之间的这种联系一旦为语言使用的群体确立起来以后,就获得了社会约定性,任何个人都不能再任意地改变它。再不能用别的声音形式去表达它。
在语言中,词的音和义是互相依存的,任何一个语词都要有一个特定的声音形式去表达它的含义,而不包含任何意义内容的声音形式也就不能成为语言的一个结构单位。在一般情况下,语音表达语义不是一对一的,同一个语音形式可以用来表达多种不同的意义,造成语言中的同音现象和多义现象,产生了同音词和多义词;同一个意义内容也可以用几个不同的语音形式来表达,造成语言中的同义现象,产生很多的同义词。
二、词义的性质
语词的意义具有概括性、民族性、准确性和模糊性等特点。
(一)词义的概括性
词义反映外在的事物、现象都具有概括性特点。外在的事物、现象是纷繁复杂的,必须经过人脑的分析综合,舍弃一些表面的特征,概括出共同性特征,才能形成为词义。例如“人”的词义,已经舍弃掉了男人和女人、大人和小孩、中国人和外国人、工人和农民等的差异,表达了区别于动物的最一般的特点,概括程度是很高的。
序言
本教材是全国新世纪高等师范院校教材编写出版规划中的一本,始编于1988年,1990年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已重印过五次,今年按出版社的安排进行了修订。修订工作贯彻了教材的师范性、专科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的精神,结合了这门课的教学实际和中学语文教学工作的需要,增补了一些内容、删节了一些篇幅、改正了一些错误、改换了一些例证,同时,也重写了一些章节、改写了一些段落,使文字表达更简练、确切、明白、易懂。全书的字数有较大幅度的压缩,约比原版本减少了七八万字,给教师讲授时更大的发挥余地。
《现代汉语》作为一门课程,它有自己的系统性,例如不仅要按惯例分别阐述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容,而且各个组成部分又各有自己的一个系统,是不能残缺不全的。然而,现代汉语又是学生们的母语,他们对母语的听、说、读、写已经有较高的水平了,因此教学时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而对教材的系统性有所突破,例如可以确定每个章节教学的重点和详讲、略讲的内容,即根据教学需要而对教材作出处理。
本教材由著名学者、上海师范大学张斌教授主审,编写人员有:徐青(浙江湖州师专、主编)、曾传兴(厦门市电大、副主编)、何蕴秀(山东泰安师专)、徐静茜(湖州师专)、张家瑞(安徽滁州师专)、俞正贻(湖州师专)。欢迎本教材的使用者和广大读者随时提出意见和批评。
作者简介
陆俭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兼职博导,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17所高等院校兼职教授。曾任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教育部社科司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文科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人文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华文顾问。独立完成、出版的著作和教材7部,主编或与他人合作编写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译文、序文等280余篇。先后获得省部级以上的奖项12个。2000年获香港理工大学“大陆杰出学人”奖。2003年9月,获“第一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先后40余次应邀赴美国、日本、法国等17个国家和地区任教、进行学术访问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后记
《现代汉语》原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师资处组织编写,是小学在职教师进修高等师范专科小学教育专业(文科方向)教材之一,现已作为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的全国通用“小大专”系列教材向全国推荐使用。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李玲璞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何伟渔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巢宗祺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同时得到了编写人员所在单位上海教育学院、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学院、上海市闸北区教育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本书由何伟渔教授主审,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由张捞之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张撝之(绪论)、任芝镆(第一、四章)、王兴伟(第二章)、朱宝元(第三章)。全书由张捞之统稿。
本书吸收了语言学界许多前辈专家的研究成果,因为是一本教材,没有一一注明出处,在此敬表谢意。

-
云南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教育学院
2025-09-27 21:09:59 查看详情 -
广汽丰田汉兰达价格 全新第四代汉兰达骑士版有介绍吗
2025-09-27 21:09:59 查看详情 -
汉兰达越野车 平衡的艺术,试驾全新第四代汉兰达380T
2025-09-27 21:09:59 查看详情 -
丰田汗兰达 全新第四代汉兰达骑士版有介绍吗
2025-09-27 21:09:59 查看详情 -
现代汉语教程(第2册)
2025-09-27 21:09:59 查看详情


 求购
求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