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一夔

徐一夔
基本资料
 相关史料
相关史料
姓名:徐一夔
性别:男
出生年月:1319年
国籍:中国
朝代:元朝
籍贯:天台
民族:汉族
职业:建宁教授
个人简介

徐一夔[约公元一三六一年前后在世]字大章,天台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元惠宗至正二十一年前后在世。元末,尝官建宁教授。洪武初,(公元一三六八年)徵修礼书。与王祎善。祎又荐修元史,辞不往。后起为杭州教授,又召修大明日历。书成,特授翰林官。以足疾辞归。一夔著有始丰集十四卷,艺圃搜奇十八卷,补阙二卷,(均《四库总目》)并传于世。
徐一夔(1319—1398),字惟精,又字大章,号始丰,天台县屯桥乡东徐村人。博学善属文,擅名于时。元至正八年(1348),为避兵乱,隐居嘉兴,与宋濂、王祎、刘基等结交,相与切磋诗文。二十七年,朱元璋平定江、浙,广征宿学耆儒,询安邦治国之计,四方名士云集南京。朝廷设置律、礼、诰3局,一夔入诰局,与著名文士杨维桢、朱右、林弼等撰写诰文。
明洪武三年(1370),诏一夔等撰《大明集礼》。王祎荐其续修《元史》,以足疾辞。五年九月,荐授杭州府学教授。次年九月,复受命参修《大明日历》,成书100卷,一夔之力居多。朝官皆推入翰林,仍以足疾坚辞。诏赐文绮、纤缯各3袭,钱6缗,准其回杭任职。后卒于任,人皆为之痛惜,称“教授之贤,难乎为继”。
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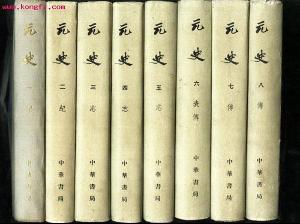
通经博古,著述颇丰,有《 始丰稿》15卷、洪武《 杭州府志》、《艺圃搜奇》等。撰《大明集礼》。 王祎荐其续修《 元史》,以足疾辞。五年九月,荐授杭州府学教授。次年九月,复受命参修《大明日历》,成书100卷,一夔之力居多。
关于徐一夔“织工对”
正 二十年前,吴晗先生首先介绍了徐一夔始豊稿中的织工对,近来我们也时常提到它。但是对于这一资料所叙述的情况,是在元末还是在明初,是丝织业还是棉织业,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解释。有的认为叙述的是元末丝织业,有的认为是明初丝织业,有的认为是明初棉织业。这些不同说法,只有对于棉纺织问题的意见谈到自己的论。
徐 一 夔 生 卒 考
徐一夔是元末明初文史学家,“煜然以文名江南”,(1)终身教授武林,造就儒生勤且广,人称“书拥万卷,才擅三长。淹通之誉,编阅四方”。(2)虽然,《明史》有徐一夔传,但载之甚略,其中他的《与王待制书》就占了大部分篇幅,更没有生卒记载。今之《中国人名大辞典》即避去生卒不写,《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仅言1368年前后在世。今在校注《始丰稿》过程中,发现新的史料,足以证明徐祯卿《剪胜野闻》称一夔因上表犯忌遭杀之荒谬。
生年考
 《始丰稿》卷三《通危大参书》说:“一夔今年四十有五”。又称:“今年谒俊禅师于天竺,禅师所尝过从者,见与阁下有夙昔之好,间语及此……”同卷《谢危大参书》说:“今年三月访俊禅师于钱塘,知其与阁下有畴昔之好,间语及此……”。
《始丰稿》卷三《通危大参书》说:“一夔今年四十有五”。又称:“今年谒俊禅师于天竺,禅师所尝过从者,见与阁下有夙昔之好,间语及此……”同卷《谢危大参书》说:“今年三月访俊禅师于钱塘,知其与阁下有畴昔之好,间语及此……”。
所谓“间语及此”者,即去年(至正二十二年1362)一夔会陈编修(杭州人陈世昌,字彦博,元末由布衣入为翰林编修,后迁居嘉兴,授徒养母。明初征修礼书,官太常博士。与徐一夔是至交,同居嘉兴,同游名胜,明初同修礼书),有五篇文章与他商榷。陈世昌告诉一夔,这五篇文章已经转送给危素了,“公必知子”。(3)一夔与俊禅师“间语及此”,即告诉俊禅师曾有文章给危素一事。
当时,俊禅师劝一夔“宜更以所为文达之,使危公得子之悉。”(4)一夔担心“绍介不通,贽币不修,俯仰拜揖不至于前”,“益自悚惧”。(5)俊禅师称危素“取人以言,不以繁文曲礼。子毋让”。(6)因此,一夔放胆又写了十篇文章,交俊禅师转达危素。出乎意料的是“俄六月十七日,入闽诏使,道出嘉兴,召一夔来前,道阁下之意,授以建宁路教授勒牒”(7)。所以徐一夔特地写信谢危素知遇之情,由此可见这两封《通危大参书》、《谢危大参书》和他得建宁路儒学教授勒牒在同一年。
又据《嘉兴路新建儒学记》文末自署“至正二十三年(1363)建宁路儒学教授”。文中又说:“至正二十三年三月淮南行省郎中陈公来守兹郡,……以兴学为己任,……始于是年八月某日,越七月迄工,明年四月二日也。时一夔侨居嘉兴之野,承公致币俾助教诸生,且属之记。”(8)此记当作于至正二十四年(1364),不可能写于至正二十三年,因为嘉兴路新建儒学动工在至正二十三年八月,迄工在至正二十四年四月。如果文章不是写于二十四年的话,那么他不可能确知新建儒学需要七个月的时间,在至正二十四年四月二日竣工。显然文末所署的“至正二十三年”当指得建宁路儒学教授敕牒的时间。
再者,《始丰稿》的编排体例,大体是按年份分文体组编,这篇《嘉兴路新建儒学记》前文是《重建王贞妇祠记》写于1364年10月,同一文体,又排在其后的《嘉兴路新建儒学记》无疑写于1364年。再说危素任参知政事在至正二十年正月到二十四年五月。
由此可以推断,他得建宁路教授勒牒和写信感谢危素均在至正二十三年,此时他已45岁,从1363年上推45,则徐一夔生于1319年。洪武二年(1369),他祭马生公著时自称“老友”,此时他已五十周岁,故称“老”。洪武五年(1372)他任杭教授时已经54岁,其卷六《初至杭学谒先圣祝文》云:“洪武五年岁次壬子年逾五十”。亦可参证。
卒年考
至于他的卒年,史无明载。仅见于野史稗乘,有关于徐一夔上表罹罪之说。
清人赵翼(瓯北)(1727——1814)《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初文字之祸”条:
《闲中今古录》又载: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下。
明徐祯卿《翦胜野闻》,与稍后之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皆有载录,足见其事流传之广。
徐祯卿《剪胜野闻》载:
太祖多疑,每虑人侮己。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曾作贺表,上,其词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帝览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我耶?光者,僧也。以我尝从释也。光,则摩发之谓矣。则字近贼。罪坐不敬。”命收斩之。礼臣大惧,因请曰:“愚蒙不知讳,乞降表式。”帝因自为文式,传布天下。(9)
《西湖游览志余》所录没有说徐一夔被斩,但称其因表笺罹难。
徐祯卿(1479—1511)字昌谷,苏之吴县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明史有传。祯卿以诗文负名,为“吴中四杰”之一。但对史事喜道听途说,曾遭当时史家王世贞《史乘考误》批评其《翦胜野闻》为“轻听而多舛”。
近现代的一些著名历史学家亦把徐一夔的死当作明代文字狱的例证之一。顾颉刚先生的《明代文字狱祸考略》,吴晗的《朱元璋传》,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罗炳绵《明太祖的文字统治术》,娄曾泉、颜章炮的《明代史话·胡兰之狱和文字狱》等等都援引徐祯卿《剪胜野闻》或赵翼《廿二史札记》记载的徐一夔史料,来阐述明代文字狱的残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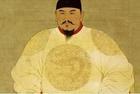 那么,徐一夔是否因上表犯忌被杀呢?从史实看,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徐一夔是否因上表犯忌被杀呢?从史实看,答案是否定的。
明朝开国之初,一切典章制度均重新考订。《明史》记载:
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两局,广征耆儒,分曹讨究。二年,诏诸儒臣修礼书。明年告成,赐名《大明集礼》。……且诏郡县举高洁雅博之士徐一夔、梁寅、周子谅、胡行简、刘宗弼、董彝、蔡深、滕公琰等至京,同修礼书。(10)
朱元璋又亲自几次颁行表笺格式,如《建言格式》、《繁文鉴戒》、《表笺定式》等书,使官民进言者均有所遵守焉。
洪武六年(1373)九月庚戌,诏革四六文辞,以柳宗元《代柳公绰谢表》及韩愈《贺雨表》定为表笺格式,颁行天下。
洪武八年十二月,因为刑部主事茹太素的奏陈,写了一万多字,只说四件事,文繁词冗,浪费时间,于是就制定《奏对式》,朱元璋自己做了一个序言,再颁示天下诸司。
洪武十二年八月,朱元璋觉得官府文移案牍繁冗,命令廷臣减去繁文,奏定成式,让诸司有所遵守。
洪武十四年七月,重定《进贺表笺礼仪》,表笺文词不得用骈俪,务在典雅,其有御名庙讳,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凡凶恶字样俱用回避。(11)
最后一次是洪武二十九年七月,朱元璋让刘三吾等人撰表笺成式,颁于天下有司。
徐一夔出身儒生,一生谨慎,与人无争,以探求文道为务。“专取经史传记与凡诸大家集,伏而读之。……故虽处乱世,饥寒逼迫,不忍弃此,妄有所图,苟富贵于一时也。”(12)科举失利后,埋头苦读,渴求能走上仕途,得个一官半职,解决生计问题,这从《通危大参书》中可见。元末连年征战,百姓不得安宁。明王朝的统一,给百姓带来安定,一夔巴不得有太平盛世的日子,这在他的文章中屡屡可见。他任杭州府学教授之后,不求闻达,惟务教书。正如陈善所说:“严为规范,以身率之。……至今称教授之贤,难乎为继。”(13)他不可能贸然犯忌,触犯龙颜的。此其一。
其次,徐一夔于明洪武二年(1369)应诏参加《明集礼》的编撰,至次年,《明集礼》成,《明集礼》被《四库全书》著录在徐一夔名下。作为《明集礼》的修撰人之一,徐一夔不会不知道避讳的起码道理。当时凡凶恶字样俱要回避的规矩,徐一夔也不可能不懂。再说他与明皇朝无任何瓜葛,何故会自寻灭顶之灾呢?
其三,在明皇朝未颁表笺时,他正参与编撰《明集礼》;洪武六年颁行表笺,刚好他被正式授于杭州府儒学教授;洪武十四年重定表笺时,他正“造就儒士勤且广”,有《始丰稿》的文章为证。洪武十六年(1384)“帝以灵谷寺初建,敕一夔自杭州撰碑文以进,称旨,赐蟒衣彩币。”(14)况洪武二十九年又一次颁布《庆贺谢恩表笺成式》的后二年,他还在西湖官署上为友人作序(详下文)。事实不可能因上表犯忌而遭杀!
其四,史家不受异文所惑。谢铎的弘治《赤城新志}》(1497)、嘉靖《浙江通志》(1561)及陈善万历《杭州府志》(1579)所作的徐一夔传并未及此。汪琬(1624——1690)与朱彝尊(1629——1709)撰写的徐一夔传也没有取《翦胜野闻》之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斥责《翦胜野闻》“称其官杭州教授时,以表文忤旨收捕斩之,殊为荒诞,《野闻》托名祯卿,多齐东之语。”
光绪间丁丙(1833——1899)编校《始丰稿》,考证一夔卒年,力辟野闻之谬。其《始丰稿》跋:
按《上虞顾君墓志铭》,葬在元至正十九年己亥(1359),既葬三十五年始请铭,则在洪武二十六年癸酉(1393),时先生七十五岁。并考陈氏善万历《杭州府志·职官表》,先生洪武六年任教授,下接三十三年,会当革除。实建文二年(1400),教授为蒋良辅(16)。其中即有权代者,表不列名,约记先生寿终当及八秩矣。世因《翦胜野闻》称表文忤旨收捕斩之之诬,几疑不克令终于官,岂非大谬哉!(15)
其五,今校注《始丰稿》,新发现徐一夔一篇逸文《灵溪八咏诗序》,载于清乾隆戊子(1768年)重修的《天台徐氏八族宗谱》(残谱,木活字本)。清道光丁酉重修的《台西徐氏宗谱》亦收有该文。(两谱虽为徐氏之谱,但两徐同宗不同支派,各自为谱,至今如此。)此文还载于天台三合镇《灵溪奚氏宗谱》,只是三本谱所载的文字略有不同。文末署“时洪武戊寅春三月二日杭州府儒学教授同邑徐一夔大章序”。
序云“天台之灵溪虚白山人奚公国贤,字彦光,隐居晦迹,安贫乐道,得山林之美趣,揭其地之尤胜者,目为八颂。”(16)按:洪武戊寅即洪武三十一年(1398)。奚国贤,《康熙天台县志·隐逸》有传:字彦光,自号虚白山人,浙江天台三合灵溪人。醇笃至孝,有《溪斋诗稿》。《灵溪奚氏宗谱》称其“《溪斋诗稿》近已无考,惟《灵溪八咏》存矣。”
徐一夔此序是应天台同乡朋友奚养民之请而作,“予寓西湖书院,乡友养民奚君赴文学之命,过谒予官署处示此卷,将欲表彰以光之。”(17)按:奚养民,一作养明,字宝先,号敦夫,浙江天台三合灵溪人。明初由人才荐举授常熟知县。有《注八景雅颂》。奚养民是奚国贤的侄儿。他在去常熟上任时,路过钱塘拜访徐教授,请徐一夔作的序。
《灵溪奚氏宗谱》收有奚国贤的《灵溪八颂》诗及徐一夔的序,还收有奚国贤的友人陈廷受、周伯明的八颂诗以及奚氏族人的八颂诗。而且,笔者去灵溪田野调查,当地乡亲至今尚能道出八景之名。此序所说的人、事、地、景,均与实际相合,断无作伪的可能。
由此可见,洪武戊寅即洪武三十一年(1398),徐一夔还在西湖书院,教授生徒,怎么会上表犯忌被杀呢?
其六,《始丰稿》卷十五即丁丙搜集整理的《始丰稿补遗》中《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一文载:“齐公庄卿……,其卒也,明洪武戊寅,以明年二月祔葬考墓左,是曰蒋山也。”
此墓志当作于1399年,因为齐公庄卿卒于洪武戊寅即洪武三十一年(1398),祔葬在明年二月,即建文元年二月,也就是说徐一夔在1399年即建文元年还为齐公作墓志铭。此更证明洪武戊寅(1398)年在西湖书院为奚国贤作《灵溪八颂》序的可能。
综上所述,徐一夔并没有因上表犯忌被杀,极有可能是卒于任上,卒年当在1399年2 月至1400年蒋良辅上任之前,他活了至少82岁。正如丁丙所说“世因《剪胜野闻》称表文忤旨,收捕斩之之诬,几疑不克令终于官,岂非大谬哉!”《剪胜野闻》所载“上表犯忌遭杀”的传闻,极有可能是作者自己心理幻想或道听途说而来,当属齐东野语之类,不足信也。
因此可以推断,徐一夔生于1319年,卒于1399年以后。他并没有因上表犯忌遭杀,而是卒于杭州府学任上。

-
解放军151团围剿土匪肖相夔战斗遗址
2025-09-19 12:57:18 查看详情


 求购
求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