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坡志林

东坡志林
书本简介
苏轼是豪放,又具有情趣的人,这一点在《东坡志林》一书中可以体现。谈天说地,出游交友,入仕致仕,他的洒脱豪放,在这本书上体现得淋漓酣畅。《东坡志林》不失为一个文人眼中的另一个世界。其文则长短不拘,或千言或数语,而以短小为多。皆信笔写来,挥洒自如,体现了作者行云流水涉笔成趣的文学风格。
此书宋时或称《东坡手泽》,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即著录《东坡手泽》三卷,并注云:“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谓《志林》也。”《四库全书总目》以为“盖轼随手所记,本非著作,亦无书名。其后人裒而录之,命曰《手泽》;而刊轼集者不欲以父书目之,故题曰《志林》耳。”然黄庭坚《豫章集》卷二九《跋东坡叙英皇事帖》云:“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囊,……手泽袋盖二十余,皆平生作字,语意类小人不欲闻者,辄付诸郎入袋中,死而后可出示人者。”则《手泽》之名为作者生前自定。又苏轼元符三年内移过廉州,有《与郑靖老书》云:“《志林》竟未成,但草得《书传》十三卷。”是作者亦曾预有《志林》之名。此书传本颇多,卷数亦不一,有一卷、五卷、十二卷本。较通行之一卷本有宋左圭《百川学海》本(《百川》本),明成化《东坡七集》本;五卷本有明万历赵开美刊本(赵本),清嘉庆张海鹏重刊赵本(张本),次年复辑入《学津讨原》本(《学津》本),涵芬楼据赵本校印本;十二卷本则有明万历商濬《稗海》本(商本)。一卷本仅载史论而无杂说;十二卷本皆杂说而无史论,虽收罗甚丰,然讹误亦不少;五卷本兼有杂说史论,去取较为精审,一般认为它是宋人所裒录,故《四库提要》以之著录。
图书目录
卷一
记游
记过合浦
逸人游浙东
记承天夜游
游沙湖
记游松江
游白水书付过
记游庐山
记游松风亭
儋耳夜书
忆王子立
黎(左“禾”右上“业”去“一”右下“蒙”去“艹”)
记刘原父语
怀古
广武叹
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
修养
养生说
论雨井水
论修养帖寄子由
导引语
录赵贫子语
养生难在去欲
阳丹诀
阴丹诀
乐天烧丹
赠张鹗
记三养
谢鲁元翰寄(日耎)肚饼
辟谷说
记服绢
记养黄中
疾病
子瞻患赤眼
治眼齿
庞安常耳聩
梦寐
记梦参寥茶诗
记梦赋诗
记子由梦
记子由梦塔
梦中作祭春牛文
梦中论左传
梦中作靴铭
记梦
梦南轩
措大吃饭
题李岩老
学问
记六一语
命分
退之平生多得谤誉
马梦得同岁
人生有定分
送别
别子开
昙秀相别
别王子直
别石塔
别姜君
别文甫子辩
卷二
祭祀
八蜡三代之戏礼
记朝斗
兵略
匈奴全兵
八阵图
时事
唐村老人言
记告讦事
官职
记讲筵
禁同省往来
记盛度诰词
张平叔制词
致仕
请广陵
买田求归
贺下不贺上
隐逸
书杨朴事
白云居士
佛教
读坛经
改观音呪
诵经帖
诵金刚经帖
僧伽何国人
袁宏论佛说
道释
赠邵道士
书李若之事
记苏佛儿语
记道人戏语
陆道士能诗
朱氏子出家
寿禅师放生
僧正兼州博士
卓契顺祥话
僧文荤食名
本秀非浮图之福
付僧惠诚游吴中代书十二
异事上
王烈石髓
记道人问真
记刘梦得有诗记罗浮山
记罗浮异境
东坡升仙
黄仆射
冲退处士
臞仙帖
记鬼
李氏子再生说冥闲事
道士张易简
辨附语
三老语
桃花悟道
尔朱道士炼朱砂丹
卷三
异事下
朱炎学禅
故南华长老重辨师逸事
家中弃儿吸蟾气
石普见奴为祟
陈昱被冥吏误追
记异
猪母佛
王翊梦鹿剖桃核而得雄黄
徐则不传晋王广道
先夫人不许发藏
太白山旧封公爵
记范蜀公遗事
记张憨子
记女仙
池鱼踊起
孙抃见异人
修身历
技术
医生
论医和语
记与欧公语
参寥求医
王元龙治大风方
延年术
单骧孙兆
僧相欧阳公
记真君签
信道智法说
记筮卦
费孝先卦影
记天心正法呪
辨五星聚东井
四民
论贫士
梁贾说
梁工说
女妾
贾氏五不可
贾婆婆荐昌朝
石崇家婢
贼盗
盗不劫秀才酒
梁上君子
夷狄
曹玮语王鬷元昊为中国患
高丽
高丽公案
卷四
古迹
铁墓厄台
黄州隋永安郡
汉讲堂
记樊山
赤壁洞穴
玉石
辨真玉
红丝石
井河
筒井用水鞴法
汴河斗门
卜居
太行卜居
范蜀公呼我卜邻
合江楼下戏
名西阁
亭堂
临皋闲题
名容安亭
陈氏草堂
登春台〔一〕
雪堂问潘邠老
人物
尧舜之事
论汉高祖羹颉侯事
武帝踞而见卫青
元帝诏与论语孝经小异
跋李主词〔二〕
真宗仁宗之信任
孔子诛少正卯
戏书颜回事
辨荀卿言青出於蓝
颜蠋巧於安贫
张仪欺楚商於地
赵尧设计代周昌
黄霸以鹖为神爵
王嘉轻减法律事见梁统传
李邦直言周瑜
勃逊之〔三〕
刘聪吴中高士二事
郄超出与恒温密谋书以解父
论桓范陈宫
绿温峤问郭文语
刘伯伦
房琯陈涛斜事
张华鹪鹩赋
王济王恺
王夷甫
卫瓘欲废晋惠帝
裴頠对武帝
刘凝之沈麟士
柳宗元敢为诞妄
卷五
论古
武王非圣人
周东迁失计
秦拙取楚
秦废封建
论子胥种蠡
论鲁三桓
司马迁二大罪
论范增
游土失职之祸
赵高李斯
摄主
隐公不幸
七德八戒
跋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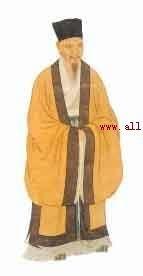 苏轼(一○三六——一一○一),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苏轼是我国杰出的文学家,也是卷入北宋政治斗争旋涡的中心人物之一。青年时代的苏轼以其横溢的才华和渊博的学识,二十二岁中进士,二十六岁入制科第三等,仕途上一帆风顺。神宗初年王安石变法,苏轼上书反对,因此出为杭州通判,嗣转知密、徐、湖三州。元丰二年因作诗讽刺新法,自湖州任上追赴诏狱,狱尽,责授黄州团练副使。哲宗幼年嗣位,旧党秉政,苏轼还朝任翰林学士。时执政大臣尽废新法,一意孤行,苏轼则主张保留新法中的免役法和裁抑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等措施,因此又招致旧党里程颐一派的攻击排挤,先后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哲宗亲政,新党东山再起,苏轼以垂暮之年,被贬至岭南惠州和海南岛儋州,元符三年遇赦内徙,次年病卒于常州,年六十六。
苏轼(一○三六——一一○一),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苏轼是我国杰出的文学家,也是卷入北宋政治斗争旋涡的中心人物之一。青年时代的苏轼以其横溢的才华和渊博的学识,二十二岁中进士,二十六岁入制科第三等,仕途上一帆风顺。神宗初年王安石变法,苏轼上书反对,因此出为杭州通判,嗣转知密、徐、湖三州。元丰二年因作诗讽刺新法,自湖州任上追赴诏狱,狱尽,责授黄州团练副使。哲宗幼年嗣位,旧党秉政,苏轼还朝任翰林学士。时执政大臣尽废新法,一意孤行,苏轼则主张保留新法中的免役法和裁抑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等措施,因此又招致旧党里程颐一派的攻击排挤,先后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哲宗亲政,新党东山再起,苏轼以垂暮之年,被贬至岭南惠州和海南岛儋州,元符三年遇赦内徙,次年病卒于常州,年六十六。
原文选载
王烈石髓
王烈入山得石髓,怀之以饷嵇叔夜。叔夜视之,则坚为石矣。当时若杵碎或错磨食之,岂不贤于云母、钟乳辈哉?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退之有言:「我宁诘曲自世间,安能从汝巢神仙。」如退之性气,虽出世间人亦不能容,叔夜婞直,又甚于退之也。
记道人问真
道人徐问真,自言潍州人,嗜酒狂肆,能啖生葱鲜鱼,以指为针,以土为药,治病良有验。欧阳文忠公为青州,问真来从公游,久之乃求去。闻公致仕,复来汝南,公常馆之,使伯和父兄弟为之主。公常有足疾,状少异,医莫能喻。问真教公汲引气血自踵至顶,公用其言,病辄已。忽一日求去甚力,公留之,不可,曰:「我有罪,我与公卿游,我不复留。」公使人送之,果有冠铁冠丈夫长八尺许,立道周俟之。问真出城,顾村童使持药笥。行数里,童告之求去。问真于髻中出小瓢如枣大,再三覆之掌中,得酒满掬者二,以饮童子,良酒也。自尔不复知其存亡,而童子径发狂,亦莫知其所终。轼过汝阴,公具言如此。其后贬黄州,而黄冈县令周孝孙暴得重膇疾,轼试以问真口诀授之,七日而愈。元佑六年十一月二日,与叔弼父、季默父夜坐话其事,事复有甚异者,不欲尽书,然问真要为异人也。
记刘梦得有诗记罗浮山
山不甚高,而夜见日,此可异也。山有二楼,今延祥寺在南楼下,朱明洞在冲虚观后,云是蓬莱第七洞天。唐永乐道士侯道华以食邓天师枣仙去,永乐有无核枣,人不可得,道华得之。余在岐下,亦得食一枚云。唐僧契虚遇人导游稚川仙府,真人问曰:「汝绝三彭之仇乎?」虚不能答。冲虚观后有米真人朝斗坛,近于坛上获铜龙六,铜鱼一。唐有《梦铭》,云「紫阳真人山玄卿撰」。又有蔡少霞者,梦遣书牌,题云:「五云阁吏蔡少霞书。」
记罗浮异境
有官吏自罗浮都虚观游长寿,中路覩见道室数十间,有道士据槛坐,见吏不起。吏大怒,使人诘之,至则人室皆亡矣。乃知罗浮凡圣杂处,似此等异境,平生修行人有不得见者,吏何人,乃独见之。正使一凡道士见己不起,何足怒?吏无状如此,得见此者必前缘也。
东坡升仙
吾昔谪黄州,曾子固居忧临川,死焉。人有妄传吾与子固同日化去,且云:「如李长吉时事,以上帝召他。」时先帝亦闻其语,以问蜀人蒲宗孟,且有叹息语。今谪海南,又有传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复返者,京师皆云,儿子书来言之。今日有从广州来者,云太守柯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独道服在耳,盖上宾也。吾平生遭口语无数,盖生时与韩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间而身宫在焉。故其诗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且曰:「无善声以闻,无恶声以扬。」今谤我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虚尔。
黄仆射
虔州布衣赖仙芝言:连州有黄损仆射者,五代时人。仆射盖仕南汉官也,未老退归,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孙画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复归,坐阼阶上,呼家人。其子适不在,孙出见之。索笔书壁云:「一别人间岁月多,归来人事已消磨。惟有门前鉴池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投笔竟去,不可留。子归,问其状貌,孙云:「甚似影堂老人也。」连人相传如此。其后颇有禄仕者。
冲退处士
章詧,字隐之,本闽人,迁于成都数世矣。善属文,不仕,晚用太守王素荐,赐号冲退处士。一日,梦有人寄书召之者,云东岳道士书也。明日,与李士宁游青城,濯足水中,詧谓士宁曰:「脚踏西溪流去水。」士宁答曰:「手持东岳寄来书。」詧大惊,不知其所自来也。未几,詧果死。其子禩亦以逸民举,仕一命乃死。士宁,蓬州人也,语默不常,或以为得道者,百岁乃死。常见余成都,曰:「子甚贵,当策举首。」已而果然。
臞仙帖
司马相如谄事武帝,开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犹草《封禅书》,此所谓死而不已者耶?列仙之隐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殆「四果」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赋》,不过欲以侈言广武帝意耳。夫所谓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贾生《鵩[fú]鸟赋》,真大人者也。庚辰八月二十二日,东坡书。
记鬼
秦太虚言:宝应民有以嫁娶会客者,酒半,客一人竟起出门。主人追之,客若醉甚将赴水者,主人急持之。客曰:「妇人以诗招我,其辞云:『长桥直下有兰舟,破月冲烟任意游。金玉满堂何所用,争如年少去来休。』仓皇就之,不知其为水也。」然客竟亦无他。夜会说鬼,参寥举此,聊为之记。
李氏子再生说冥间事
戊寅十一月,余在儋耳,闻城西民李氏处子病卒两日复生。余与进士何旻同往见其父,问死生状。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幕下。有言:「此误追。」庭下一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无罪,当放还。」见狱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系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妪身皆黄毛如驴马,械而坐,处子识之,盖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钱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处子邻里,死已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盘飡及钱数千,云:「付某僧。」僧得钱,分数百遗门者,乃持饭入门去,系者皆争取其饭。僧饭,所食无几。又一僧至,见者擎跪作礼。僧曰:「此女可差人速送还。」送者以手擘墙壁使过,复见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跃,处子惊而寤。是僧岂所谓地藏菩萨耶?书此为世戒。
校勘纪
〔一〕原本此则有目无文,明万历赵开美刊本(以下简称赵本)、清嘉庆张海鹏照旷阁刊本及《学津讨原》本《东坡志林》(以下分别简称《张本》、《学津本》)同。
〔二〕李主 原本误作“李玉”,从正文标题改正。
〔三〕勃逊之 原本目录无此条,从《学津》本目录补。
序言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寸,四川眉山人,他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家,诗、文、词、赋都有很高的廖就,一生著述甚多。
嘉祐元年(1056),二十岁的苏轼与弟苏澈一起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同榜中了进士,不仅深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而且也得到当朝皇帝宋仁宗的称赞,“仁宗以制科得斌兄弟,喜曰:‘吾为子孙得两宰相。’”(《宋吏·后妃传上》)嘉祐六年(1061),苏轼开始步入仕途,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在凤翎刚满一任,其父苏洵病死京师,轼扶丧归里,丁父忧后,于熙宁二年(1069)还朝,这时正值王安石执政为相,安石平素恶其议论异己。仅给了他一个告院判官的官职。过了二年,王安石的新法得到神宗的支持,并迅速向全国推行,苏轼连续上书反对变法。由于意见未被采纳,又激怒了王安石,苏轼自感难以见容于新派,遂请求外放,通判杭州。此后又徙知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了十年左右的地方官。在任职期间,苏轼能关心人民的疾苦,重视农田水利及水、旱、蝗灾的救灾工作,特别是熙宁二年(1077)移知徐州时,黄河决口,大水汇于城下,又加大雨日夜不止,城墙未被淹没的部分仅三版厚,“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宋史·苏轼传》)可以说在此次抗洪抢险中,苏轼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时王安石已经两次罢相,彻底退出朝廷。苏轼虽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外放,安石罢相后,他不但未得到丝毫重用,一场更大的灾难反而落到苏轼头上。元丰二年(1079)他刚徙知湖州不久,便被逮捕,原来是新进派官僚何正臣、舒宣、李定等,在享轼诗文中找茬口,罗织罪状,弹劾苏轼“指斥乘舆”、“包藏祸心”,把苏轼投进监狱,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经过几个月的折磨,幸赖曹太皇太后亲自向神宗求情(见《宋史·后妃传上》),苏轼才幸免于一死,责贬黄州,为团练副使。被贬黄州的四年中,他躬耕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元丰七年(1084),改贬汝州,离黄州北上的途中,苏轼上书自言饥寒,有田在常州,愿居常州。诏准,逐过金陵,会见了与他政见不合但私交尚可的王安石。苏轼至常州后,神宗去世,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朝廷启用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刚徙知登州,便被召回京,任礼部郎中,不久,迁起居舍人、中书舍人。次年(元韦占二年),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元祐三年(1088),权知礼部贡举。这时苏轼与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又产生了矛盾,他不同意旧党尽变新法,不同意废免役法,由此引起旧党对他的猜疑。司马光死后,旧党发生分化,苏轼遭到忌恨,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元祐四年(1089),苏轼第二次到了杭州,在杭州近三年,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杭州市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宋史》本传),足见他赢得了人民的爱戴。
元祐六年(1091)苏轼又被召回京,原拟任礼部尚书,以弟苏辙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苏轼在翰林院数月,又以受谗请外,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次年,徙知扬州。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病死,哲宗亲政,时局又发生变化,一些投机新法的分子如章悖、吕惠卿、曾布、蔡京之流,以绍述熙宁、元丰新政为名,尽复高太后临朝时所废新法,大肆迫害元祐旧臣。这时苏轼正任礼部尚书,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知制诰。苏轼已感到形势对他不利,又请求外放,以两学士出知定州。然而苏轼外放并没躲过一场灾难。绍圣初(1094)御史论轼知制诰时所作制诰,有“讥刺先朝”之处,以此罪名贬知英州(今广东英惠),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又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一月之内三次贬职。如此一贬再贬,当权者犹不解恨。绍圣四年(1098)四月,又把苏轼贬至海南的儋州(任州别驾),苏轼此时已经六十岁了,他只得只身携幼子苏过,浮海南渡,垂老投荒,北归无望,真正是“海南万里真我乡”了。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病故,其弟端王赵佶即位,是为徽宗。徽宗即位后,宽赦元祐旧臣,苏轼遂奉石内迁。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苏轼过大庾岭,四月经庐山,五月至金陵,闻朝内又有排挤元祐旧臣迹象,遂决计定居常州,六月海倒在由金陵去常州的船上,七月二十八日,六十六岁的苏轼不幸溘然长逝。
《东坡志林》所载各篇,相当一部分留下了写作年代,较早的是元丰年间,较晚的是元符四年,前后历二十除年,大体上是从被贬黄州始,至元符四年遇赦内徙止,共二百零三篇,内容相当丰富,正像万历二十三年(1595)赵用贤《刻东坡先生志林小序》所言:“皆纪元祐(当为元丰)、绍圣二十年中所身历事,其间或名臣勋业,或治朝政教,或地理方域,或梦幻幽怪,或神仙伎术,片语单词,谐谑纵浪,无不毕具。而其生平迁谪流离之苦,颠危困厄之状,亦既略备。然而襟期廖廓,风流辉映,虽当群口见嫉、投荒濒死之日,而洒然有以自适其适,固有不为形骸彼我,宛宛然就拘束者矣。”
综观《东坡志林》,我们可以窥见东坡的学养、思想、世界观的诸多方面,东坡是位于学无所不窥的大学问家,他对于经学、史学巧至诸子百家都很有研究,而且特别重视经世致用和以史为鉴,尽管他所总结的历史经验有些是片面的、不足取的,但可以看出他的用心是古为今用,是欲垂戒于后世。苏轼不是纯儒,他对儒、道、释三家颇能兼融贯通,关于这一点不仅在《志林》中的“佛教”、“道释”类中各篇可以看到,在“修养”与“异事”类中亦可以看到。他的佛学修养很深,与众多的和尚、道士交往密切,叉读过不少佛经,对佛典之熟悉,如数家珍,但他并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的谈佛论道,有时近于戏谑。如卷一的《论修养帖寄子由》篇,即可看到此点。《志林》涉及道家者,主要不是道家的哲学观点,而是道家的养生、导引、炼丹、辟谷等。苏轼对《易经》颇有研究,他不仅有《东坡易传》九卷传世,而且精通占卜,卷三之《记筮卦》,是用《周易》为其弟子由占卜的,他自以为“考此卦极精详”,昔口传授给小儿苏过,又“书而藏之”。苏轼有点迷信,且相信命运。“命分”类的三篇,可见其一斑。他认为“人生自有定分”,韩愈以磨蝎星为身宫,他自己以磨蝎为命,所以“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乜”。又说友人马梦得与他同年同月而生,生日比他晚八天,“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东坡又颇通医术,《修养》、《疾病》、《技术》三类,不乏此类记载,从《志林》一书可以看出,苏轼是一位杂家。
苏轼的思想比较活跃,也比较解放,他的思想虽以儒家为主,但儒家经典并不能拘束化,评价历史人物,议论古人古事,多所创见,发前人之所未发。如巷五之《武王非圣人》,提出武王伐纣是以臣弑君,并连及汤之伐桀,认为如当时有良史董狐,必以叛、弑书。对孟子所言“吾闻武王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也”,苏轼指出这是乱了孔子的家法。在封建时代,“薄汤、武而非周、孔”往往成为名教之罪人,苏轼公然指责汤、武之篡弑,这是非常大胆的。在《摄主》篇中,苏轼强烈反对母后临朝摄政,他举出许多例证说明因母后摄政而使国家乱亡以至江山易姓的事实。其实这个问题在宋代是较为敏感的,北宋出现四次母亏临朝听政,除苏轼提到的曹、高、向三皇后、皇太后外,就在他遇郝的元符四年徽宗刚即位时,也是皇太后临朝,他虽然说宋代几位临朝的皇后,都是千中挑一的好皇后,但他的前提却是反对太后于政,为此,他引用了孔子“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牝鸡之晨,惟家之索”,这是相当有刺激性的话,也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罗织罪名。他数次获祸,与此是有关系的,其个性可以说至晚年一点未改。
《志林》一书,可略见东坡鲜明的个性,他是一位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人。卷一之《涝沙湖》,写于被贬黄州时期,当他下临兰溪,看到溪水西流时,高唱一首充满豪情的歌:“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其精神真是难能可贵。卷二《书杨朴事》,叙述了隐士杨朴的故事,杨朴以能作诗被召进京,及召对时,自言不能作诗,皇上司他:“临行有人作诗送卿否?”杨朴回答说:“惟臣妾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元丰二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于湖州,妻子送出门,自觉无生还希望,皆哭。轼却回头对妻子说:“独不吨如杨子云(实即杨朴)处士妻作诗送我乎?”妻子不觉失笑。在皂死关头,苏轼尚能如此旷达,又如此诙谐,这是常人所不能做到的。卷一的《措大吃饭》、《题李岩老》,读之让人捧腹大笑,可入《笑林》。
众所周知,苏轼是反对王安石的变法的,他为何反对新法,晚年对新法的看法有无改变,我们可以在《志林》中找到答案。苏轼对法家人物,对严法峻刑,对革新派,可以说都没有好感,而且不时地对他们进行口诛笔伐。卷五《司马迁二弋罪》,把司马迁论商鞅变法之功及汉代桑弘羊设平准法、实行盐铁国有,使“民不加赋而上用足”的功劳,目为战国游士的邪说诡论。司马迁颂扬二人之功,是司马迁的二大罪过。卷四之《王嘉轻减法律见梁统传》,言梁统上书说“高、惠、文、景以重法兴,哀、平以轻法衰”,请增重刑法即用严法峻刑治国。苏轼说梁统“一出此言,遂获罪于天”,梁统的两个儿子皆死于非命,至孙子辈梁冀梁家秽灭族,这都是梁统造下的孽,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卷四之《柳宗元敢为诞妄》中,批判柳宗元极力称赞吕温、吕恭兄弟(王叔文革新集团的成员)是诞妄,并把柳宗元与王、王叔文交友,视为与恶名昭著的裴延龄联姻一样的耻辱等等,可见苏轼的固执与偏见,是不可讳言的。卷二的《唐村老人言》,写于元符三年被贬海南时,篇中叙述了一位老农对“青苗法”和均贫富的评论,这位老友认为:贫富之不齐,是天经地义的,“民之有贫富,由器用之有厚薄也”。如“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动,而薄者先穴矣”。苏轼称赞这位“负薪”者“能谈王道”,可见他对王安石新法的看法至晚年也未改变。
有些研究者指出:“元丰七年,苏轼改贬汝州,离黄州北上时,路过金陵,曾拜会退休宰相王安石,两人政治见解虽有分歧,但依然保持了良好的私交。他们共游蒋山,互相唱和,翰墨友谊又有了发展。”这虽然是有据的,但也不过是表面的应酬而已,苏轼对王安石的看法,至晚年也并无改变。卷二之《记盛度诰词》中,苏轼提到“论周□擅议宗庙”事,为了注释的需要,笔者从苏轼的《奏议集》中,查到了《论周檀擅议配享自劾札子二首,看了之后不免有点吃惊,周檀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原为江宁府右司理参军,经苏轼举荐,做了郓州的州学教授,在王安石死后,他曾上表请求将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苏轼自劾札子云:“谨按汉纪,擅议宗庙者弃市。……窃以为安石平生所为,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难逃圣鉴,先帝盖亦知之,故置之闲散,终不复用。今已改青苗等法而废退安石党人吕惠卿、李定之徒,……而先帝配享已定用富弼,天下翕然以为至当。□复何人,敢建此议,……谨自劾以待罪。”从苏轼对王安石的评价看,是带有个人成见的,虽曰自劾,但“擅议宗庙者弃市”一句,未免令人毛骨悚然,由此我们不能不怀疑王、苏之间的“翰墨友谊”了。
《志林》中有些文献资料弥足珍贵。卷一之《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说明北宋时民间艺人所说的“三国语”已带有尊刘抑曹的正统倾向,常为文学史家所引用。卷四的《筒井用水鞴法》,是北宋重要的科技史料,其他各篇,可史料价值的亦不在少数。记述人物故实的篇章,亦有足资参考考。
《志林》各篇,虽大多篇幅短小,但由于作者是大手笔,往往随手挥洒,涉笔成趣,实为晚明小品之滥觞,其影响是较大的。
迄今为止,笔者还未看到《东坡志林》的注本。我所用的白文底本,是1919年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校印本,它的母本是明万历乙未的赵刻本,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的王松龄校点本,亦是以涵芬楼校印本为底本,我吸收了王松龄先生的不少校刊成果,在此对他表示感谢。由于注释的需要,笔者标出了部分《志林》中涉及的人物、事件的出处,为读者提供了方便,同时也发现了苏东坡的一些张冠李戴的误记。
以笔者的知识结构,深感注《东坡志林》的困难,缺点和错误定然存在,恳切欢迎海内外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刘文忠
2007年4月
编辑推荐
《文华丛书:东坡志林(套装共2册)》由广陵书社出版。
文摘
【注释】
①悴:做官。
②武林:杭州旧称。
③禁中:皇宫内殿。
④既毕进御:写好以后呈给皇帝。
⑤敏:文思敏捷。
⑥睇视:斜视;流盼。
【点评】
这一则可与《记梦赋诗》对照来读。同一首诗,出现在两个梦里,令人怀疑东坡所说的梦的真实性。其实梦就是梦,又何必过分认真?至少东坡描绘的这两个梦为我们解读这首《裙带词》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背景,娇娜的贵妃被宫女围侍、裙裾飘飘的场面宛在眼前,令人心驰神往。
记梦予尝梦客有携诗相过者,觉而记其一诗云:“道恶贼其身,忠先爱厥亲。谁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文有数句若铭赞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之所以修,不贼其牛。”

-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
2025-09-22 13:58:44 查看详情 -
上海邃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5-09-22 13:58:44 查看详情 -
广东达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09-22 13:58:44 查看详情


 求购
求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