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尚爱兰

尚爱兰
人物经历
如今的尚老师在襄阳市致远中学执教高中语文,自从调往学校团委工作之后,开始组建社团。在她手下汇聚了街舞社等青春社团,不久又将这些社团整合为“致远剧社”。 尚爱兰如今的剧社正在为话剧《第一女生》的开演做着准备。
尚爱兰如今的剧社正在为话剧《第一女生》的开演做着准备。
尚爱兰辞去教师工作,成为一名《南方都市报》的专栏作家。蒋方舟文章里曾说,尚爱兰辞职去写专栏有女儿的激励。2000年蒋方舟的《打开天窗》出版,接着第二年《正在发育》出版,作为作家的妈妈,尚爱兰也被调动了积极性,为女儿做示范,自己动手写了一两年专栏。[4]
尚爱兰的文学高光时刻很短暂,“最后终于因为体力和脑力不支而写不下去。”尚爱兰向澎湃新闻记者坦承自己才华不够,“我和安妮宝贝是差不多一起出来的,她的才华是高于我的。我发现有才华的就是有才华,我很佩服他们。”
在为专栏写作一年后,尚爱兰告诉好友七格,自己写空了,对网络也厌倦了;她同时还给其他杂志写明星八卦评论,给中学生杂志写作文辅导,但即使约稿也常常被退稿。尚爱兰决定回到自己原来的人生轨迹,重新回去教书。
不管怎样,尚爱兰短暂的作家生涯结束了。此时的尚爱兰还想做两件事,第一是写一个“关于狒狒的中篇”,另一个就是写一本用素质教育培养孩子的书。
主要作品
| 书名 | 作品时间 | 作者名称 | 备注 |
| 《蒋方舟的作文革命》 | 2003年8月 | 尚爱兰 | 《蒋方舟的作文革命》是2003年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尚爱兰。 |
| 《作文课》 | 2019年10月 | 尚爱兰 | 《作文课》是尚爱兰所著书籍,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
| 《性感时代的小饭店》 | 1999年 | 尚爱兰 |
|
| 《永不原谅》 | 尚爱兰 |
小说 | |
| 《数字美人》 | 尚爱兰 |
散文集 | |
| 《焚尽天堂》《性感时代的小饭店 | 尚爱兰 |
短篇 |
荣誉记录
| 书名 | 作品时间 | 作者名称 | 备注 |
| 《蒋方舟的作文革命》 | 2003年8月 | 尚爱兰 | 《蒋方舟的作文革命》是2003年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尚爱兰。 |
| 《作文课》 | 2019年10月 | 尚爱兰 | 《作文课》是尚爱兰所著书籍,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
| 《性感时代的小饭店》 | 1999年 | 尚爱兰 |
|
| 《永不原谅》 | 尚爱兰 |
小说 | |
| 《数字美人》 | 尚爱兰 |
散文集 | |
| 《焚尽天堂》《性感时代的小饭店 | 尚爱兰 |
短篇 |
主要成就
《性感时代的小饭店》获榕树下首届网络文学奖的小说类一等奖。
蚊子的《蚊子的遗书》获得散文一等奖。[4]
人物关系
尚爱兰的《性爱时代的小饭馆》获得小说一等奖,蚊子的《蚊子的遗书》获得散文一等奖。[4]
母亲和女儿
蒋方舟,1989年生,中国青年作家、杂志副主编,曾任中国少年作家学会主席。7岁开始写作,9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此书被湖南省教委定为素质教育推 荐读本并改编为漫画书,同年在8月起,在《南方都市报》开设专栏。
2002年,12岁的她又接连出了两本书。 蒋方舟(3)
蒋方舟(3)
一本是《青春前期》,写小学五年级时和同学发生的趣事,另一本叫《都往我这儿看》,记录生活中的小故事。
2005 年4月,蒋方舟通过华师一附中自主招生考试,被该校提前录取,蒋方舟在该校的寝室已被命名为“蒋方舟创作室”。
2008年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
2009年获得第七届人民文学奖散文奖。
2012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就任《新周刊》杂志副主编。[5]
《打开天窗》出版后,凭借9岁出书的超低龄写作,媒体纷纷关注。很快,这本书被湖南省教委列为中小学生素质教育读本。
蒋方舟也一举走红,成为众人眼中所谓的“天才少女”。[6]
蒋方舟上小学三年级之前,第一本书稿已经交付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个时候,同年龄的孩子,作文还刚刚起步。蒋方舟赶在上三年级前写作,有很大一部分考虑,就是很害怕她受到“正规”作文训练的影响。
但这还不够,18岁之前的蒋方舟被母亲推着不断向前走,步履不停。其中,《蒋方舟的作文革命》一书的宣传语如此写道:“对一个写作天才成功之路的智慧解读。”[6]
作家妈妈和作文老师
2016年,在北京和女儿一起住的尚爱兰终于找到了新的兴趣,剪纸。先从人物肖像开始,接着不满足于模仿,去日本看了纸艺切绘美术馆,想要创作有思考的剪纸艺术品。尚爱兰的微博里,分享了很多她的剪纸作品。就像很多年前的作家尚爱兰一样,她的剪纸作品仍然关注女性和生命,比如“子宫中的娃娃”。[4]
这样的作品让女儿蒋方舟感到一些不安,“我自觉意识到一个家庭空间里是容不下两个艺术家的,狭窄的空间里总会撞着对方膨胀的灵魂。”她有意识地一大早就离开家在外写作,每天晚上才回家吃饭,和尚爱兰聊聊她的新剪纸和其中的创作理念。
尚爱兰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的特殊互动。作为写作者,她和蒋方舟之间有某种磁场吗?尚爱兰直白而简单地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没有,我写作比她要可能低端很多。”作为母亲,尚爱兰无疑认为蒋方舟要胜过自己百倍,她也从没有把自己当作艺术家或者作家。
2001年,十一岁的蒋方舟说自己最喜欢的作家是三毛、张爱玲、余华、王朔,觉得妈妈的写作是“老土落后的”。而刚刚获奖,处在人生高光时刻的尚爱兰也不反驳,只说自己不敢乱指导蒋方舟的写作了。
2002年,专职写作不到两年的尚爱兰,已经觉得自己才华耗尽,不适合当作家。去年接受虎嗅采访的蒋方舟,也认为自己不得不承认,确实没有很高的小说写作天赋。想必蒋方舟也逐渐可以理解当年尚爱兰的心境了。母女的人生轨迹,在近20年后,似乎正在相互贴近。
和母亲尚爱兰相比,蒋方舟无疑是幸运的。不仅仅是少年成名,让她的人生走得更轻快,不需要像尚爱兰一样面临写不出来就无法生存的窘境。更重要的是,蒋方舟一直有着母亲尚爱兰的陪伴。
蒋方舟出生不久,尚爱兰的母亲就因患病不想拖累家人,喝农药自杀了。蒋方舟对于这个据说矮小严肃的外婆,几乎完全没有印象。在尚爱兰一举成名的时刻,在她自觉才华耗尽的时刻,她都没法和母亲分享自己的欢乐和惶恐。
尚爱兰的经历或许也影响了她的写作,死亡一直是尚爱兰作品中的重要主题。无论是在《永不原谅》还是《焚尽天堂》中,读者都必须直视甚至触碰死亡。
“此文给死去的人,所有我记得的曾经生活在我身边的死去的人,爱过的和不爱的,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体内的和体外的,也给注定要在不远的将来死去的我自己……因为反复温习和完善幻想中的死亡影像,死亡由狰狞模糊变得柔和亲切。就像一个黑白的恐怖照片变成了色彩分明的生活照。死亡从前是个泛着青光的吸血鬼,而现在是脸色红润的醉汉。人生烂醉如泥,一脚踹进路边的泥塘里就死了,死得很难看。将死的人生不会因为将死就变得美丽起来。临死的胡言乱语,也不过是对着无辜的生活乱箭齐发。”(尚爱兰《永不原谅》)
从去年开始,诸多媒体就开始讨论将“三十不惑”的蒋方舟,互联网的目光已经略过了今年57岁的尚爱兰,不再关注一对母女曾经引起的争议,遗忘了网络文学的二十年。一代人的青春,需要另一代人的青春去铭记。
人物评价
对于自己身上的各种标签“教师”、“作家”、“蒋方舟妈妈”,尚爱兰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作家’肯定就不算了,‘蒋方舟妈妈’这个称号就挂在《作文课》的腰封上,其实我都不挣扎,我都可以。”[3] 作文课
作文课
尚爱兰还是希望通过《作文课》,留下一些她的教育理念,“教了30年的书,都是反复实验出的心得,我认为有效的,最后才用这么一种‘幼稚’的方式,大家容易理解的方式把它写出来。”
不少人问这本《作文课》与蒋方舟什么关系,尚爱兰是不是也教过蒋方舟这些。尚爱兰否定了,“这本书所谈的东西,但凡健康的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都会知道的。我在书里讲的这些,蒋方舟都知道,但并不是我教给她的。”
其实,早在2001年,尚爱兰就以蒋方舟妈妈的身份,在媒体访谈中畅谈自己的育儿经验:“我研究了一套自己的教学法:每天只教方舟认一 到两个字,将所有要教的字写在卡片上,教方舟反复诵读……我不允许方舟通过看图来识字。”2003年,尚爱兰的第一本作文书《蒋方舟的作文革命》出版了。
《蒋方舟的作文革命》,尚爱兰著。母女两个人的名字是很难分开的,就像两人当时“战友/教练和运动员/陪练和种子选手的关系”。
尚爱兰辞去专栏写作的工作后,蒋方舟接过了妈妈的笔,为《南方都市报》写专栏。蒋方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那时她的月收入就已高达4000元,是全家收入最高的人,一度尚爱兰和丈夫都靠蒋方舟写作养家。
2005年,蒋方舟上高中了,湖北华师大一附中给她安排了可以上网的单人宿舍,方便在校继续写作。但因为学校给予的超常规待遇,引起了其他学生的不满,加上蒋方舟无法融入集体生活,她在高中里很痛苦。于是,蒋方舟和尚爱兰大吵了一次,她认为是妈妈让她变成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永远丧失了快乐的能力”。
从此以后,蒋方舟默默解除了和妈妈“教练”聘约。写作上分道扬镳,但蒋方舟仍然是尚爱兰生活的重心。尚爱兰新浪博客里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大多都是谈论蒋方舟的高中生活和学习:参加家长会,如何学数学,怎么整理错题,怎样写高考作文等等。
2008年6月,蒋方舟参加高考。尚爱兰挤到了考场外等待的家长的第一排,对“作文高分秘诀”她也很津津乐道,就像一个普通的学生家长。最终蒋方舟以语文117分,数学131分,总分561分的成绩,以自主招生降低60分,进入清华大学入读。尚爱兰依然是一名普通的语文老师,稍有不同的是,她已不再试图从自己学生里寻找下一个蒋方舟,只是专心自己的本职工作。
2009年10月27日,蒋方舟的20岁生日,这一天她过得并不顺利:去修笔记本电脑被骗,坐车丢了公交卡,打车又丢了钱包,回去之后还没有人给她庆祝生日。尚爱兰回忆当时因为忙于学校社团活动而未接到蒋方舟的多个电话,接通电话后尚爱兰只回了一句“回家再说”。这让蒋方舟非常不开心。两人都认定,总有一天要摆脱对方,这样蒋方舟才能有更大成就,尚爱兰也才可以有自己的生活。但谁也没想到,是尚爱兰首先离开蒋方舟。
蒋方舟有试图修补过这种母女关系。从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后,她入职《新周刊》一跃成为副主编。接着,她劝尚爱兰提前退休,搬到北京和她一起住。
离开襄阳来到北京的尚爱兰并不习惯,不仅仅是一开始不习惯大城市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她在北京没有自己的生活,也不想主动开展新的生活。蒋方舟曾在文章中写道:“第一次来我家做客的人经常会觉得我妈是个冷漠的人,她不会像别的热情长辈一样招呼人吃饭聊天,而是做完饭放下菜转身就走,就像刚刚掷下一盆狗粮,我的朋友们都很尴尬。只有蒋方舟的日本朋友说‘你妈妈真是很害羞的人’,他洞穿了她的本质,极度害羞的人经常会显得很冷漠。”
退休没事可干的尚爱兰,耐不住亲戚们的劝说,开始带起了作文课,学生就是亲戚朋友们的几个孩子。这几年的私人作文课,给了尚爱兰更多时间和回转余地,去反思她作为老师的三十年。
尚爱兰不再期待培养另一个蒋方舟了,甚至希望蒋方舟的孩子也不要再写作了。尚爱兰和澎湃新闻记者直言:“千万不要都来干这件事情,蒋方舟真的是很幸运。一般人眼里走上职业作家道路的小孩,都是不幸福的,要么你最后自杀了,要么神经病要么穷。
面对这个小小作文班的孩子们,尚爱兰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服务者”。“服务者”有两层含义,首先,她不想成为孩子们作文的评判者,而是帮助他们去写好作文的服务者。小孩子写不出来怎么办?“家长有责任去想办法,或者说有能力为他提供一些比方说人生体验。比如说买条鱼,多养几天,让他可以看到整个从生到死的过程,我觉得老师也是一样。”
其次,尚爱兰会判断孩子们的需求,如果他们想写高分作文,她就提供这样的“服务”。有的孩子就一直跟着她上作文课,连着好几年,直到小学毕业。[4]
词条图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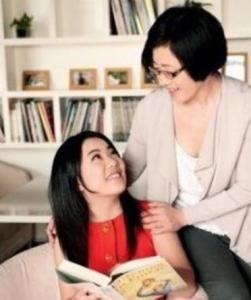 尚爱兰母女尚爱兰应该更有资格说“除了写作我不能生存”,因为她现在已经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了,这是一个有勇气的女人,这从她敢于辞去公职,专门以卖字为生即可窥见一斑。
尚爱兰母女尚爱兰应该更有资格说“除了写作我不能生存”,因为她现在已经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了,这是一个有勇气的女人,这从她敢于辞去公职,专门以卖字为生即可窥见一斑。
尚爱兰在网上,尚爱兰是一个不喜欢跟风的人,颇有点独来独往的女侠之风。尚爱兰在有些网管的心中名气并不算太大,虽然她获过榕树下首届网络文学奖的小说类一等奖,因为那则《性感时代的小饭店》也只是一个短篇,有人以为那不足以说明她的写作才能。
尚爱兰自己最好的作品是短篇《焚尽天堂》,读来惊心动魄,里面传达出的悲天悯人足够震撼读者毛骨悚然之时的心灵。至于她在报纸上写的那些专栏,只是为了生存而浪费时间罢了。我猜测,尚爱兰是一个从小被宠着长大的,应该是有着傻乎乎的善良的那种美女,照片上看,她的眼镜片的厚度直逼某些人的脸皮,眼镜下面那张脸显示出大智若愚的狡猾。尚爱兰的作品如果仔细雕琢一下是有可能走进文学史的。
总的来说,这个时代似乎更欢迎卫慧、棉棉们那样年轻、骚动、容易被勾引的心灵。与卫慧们相比,尚爱兰的另一个不利之处是她已经结婚,而且有一个10岁的女儿。这样的女人往往不仅有稳定的生活轨道,而且有稳定的心智,有自己坚强的生活法则,她们不容易动摇,不容易为外在的东西迷惑,不容易再编辑干脆利落的青春之梦,也不容易引发倾国倾城的迷狂,所以尚爱兰和卫慧们的区别不仅仅在文学上。

-
广州车展上市 爱驰U6正式上市
2025-08-24 15:21:47 查看详情 -
TSI锐尚版正式上市 EM
2025-08-24 15:21:47 查看详情


 求购
求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