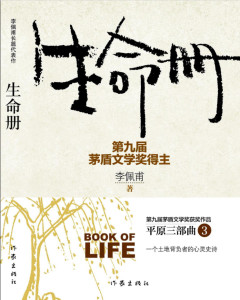- 生命册

生命册
内容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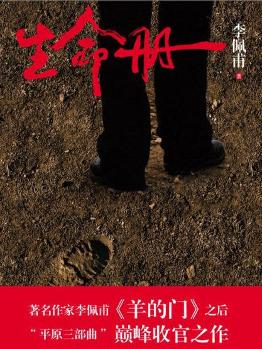 生命册“我”是从乡村走入省城的大学教师,希望摆脱农村成为一个完完整整的“城里人”,无奈老姑父不时传来的要求“我”为村人办事的指示性纸条让“我”很是为难,在爱情的憧憬与困顿面前,“我”毅然接受大学同学“骆驼”的召唤,辞去稳定的工作成为一个北漂。北京的模样完全不是我们当初预想的那般美好,在地下室里当了几个月的“枪手”挖到第一桶金后,为了更宏大的理想,“我”和“骆驼”分别奔赴上海和深圳开辟新的商业战场。
生命册“我”是从乡村走入省城的大学教师,希望摆脱农村成为一个完完整整的“城里人”,无奈老姑父不时传来的要求“我”为村人办事的指示性纸条让“我”很是为难,在爱情的憧憬与困顿面前,“我”毅然接受大学同学“骆驼”的召唤,辞去稳定的工作成为一个北漂。北京的模样完全不是我们当初预想的那般美好,在地下室里当了几个月的“枪手”挖到第一桶金后,为了更宏大的理想,“我”和“骆驼”分别奔赴上海和深圳开辟新的商业战场。
“骆驼”虽有残疾,却凭借超出常人的智力和果断杀入股票市场并赢得了巨额财富。而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骆驼”的欲望和贪婪也日益膨胀,他使出浑身解数攀附进官场名利场,不惜用金钱和美色将他人拉下水,而自己也在对欲望的追逐中逐渐走失了最初的理想,最终身陷囹圄,人财两空。
生“我”养“我”的无梁村,有“我”极力摆脱却终挥之不去的记忆。哺育“我”十多年的老姑父为了爱情放弃了军人的身份,却在之后的几十年生活中深陷家庭矛盾无法自拔;上访户梁五方青年时凭借倔强的干劲打下了一片基业,却在运动中成为人们打击的目标,后半生困在无休止的上访漩涡里;为了拉扯大三个孩子,如草芥般的虫嫂沦为小偷,陷入人人可唾的悲剧命运;村里的能手春才,在青春期性的诱惑和村人的闲言碎语中自宫……在时代与土地的变迁中,似乎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书中人物
吴志鹏
骆驼逸出凡尘的最大特点是他在立身行事上对极致的追求。因为身体的残疾,他在生活自理的动作上追求逾于健全人的准确和敏捷,服饰衣着上力求表现出超过常人的精致、优雅和整饬。在学业的进修、性爱的征途上他也屡屡表现出超越常规的逆序猛进,在他身上,生命的能量因受挤压而反弹,表现为一种极致的挥洒和强劲的弹射。
这种对极致的追求,一旦注入他跃入商海后的充满颠簸欹侧的险航,便有了一连串炫酷惨烈的征战。因了童年时极度饥寒的经历,骆驼对天文数字的金钱的占有欲便分外强烈,永难满足。他像城市高楼之间呼啸而过的响箭频频出击和突进:要炒股就炒成巨富,炒成股神,炒出了“包下一周两趟的船票”去镇江“打新股”,大大提高“中签率”的豪举;若是买房就买出了“撒泡尿就挣了一千多万”的收益率;他的双峰公司一旦上市就上出了用尽威胁、利诱、诈骗种种手段,一下子圈钱过亿的惊天效益;当他为了达到卑鄙的目的需要买官、养官时,用尽了迂回包抄、无缝钻出缝来也要摘心夺魂的丑闻和劣迹……
这一切在商海、“钱途”上的搏击和得获,都是在自觉的灵魂冒险和观念更新的指导下进行的。骆驼虽然有些匪气,在吴志鹏心目中却是一个具有领袖气质的人物,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充满着洞察力。他讲信用,会用人,颇具恢弘大气,他有侠骨剑胆,也有热血琴心,他有独特的时间观,心里永远揣着一个“抢”字,他有透辟的善恶观,似乎深谙“恶”在历史发展、时局变易中巨大的杠杆作用,他还有自己的时代观,时时欢呼“一个伟大的时代已经开始”,抓住机会的时刻就在眼前。他又认为这是一个方向不明、规则不细、法律边界模糊、道德底线沉降的时代,他相信钱砸下去,事无不成。正当他志得意满,眼高于顶的时候,他无意中伤害了“烧包文盲”房地产商宋心泰,踩到了年轻气盛、嫉恶如仇的京城记者“宋剑”宋保平的剑刃,立即像膨胀的气球瞬间爆裂一样,在被“边控”后的第9天跳楼自尽。被他漠视、蔑视的法制规则、道德律令,终归成了这个天才的投机客无法逾越的天网。
骆驼这个人物形象,是作家观察时代现象、体验社会生活之后的一个发现。这个形象被作家用钻旋尖利的笔触刻画得活力四射、邪气冲天、灵府洞张、声态并作,具有咄咄逼人的气势,令人难忘的艺术魔力,是一朵剧变时势中怒放贲张的“恶”之花。
梁五方
梁五方曾是1960年代无梁村的“名片”。他在建造镇政府大礼堂的工程中,大胆捏塑麒麟脊,创造了具有不对称美的“龙麒麟”屋脊造型,一举成名。那时,他是何等聪明,何等自信。尔后他一个人在水塘上盖起了一座房屋,举办了最简朴的婚礼,成家立业。那时,他又是何等坚毅,何等心旺。但他的太“独”、太“各色”的立世行事,使他成了无梁村人群中的异类。一旦“运动”到来,他便为自己的傲慢和伤人付出了惨烈的代价。梁五方最终家破人散、一蹶不振,生命淋漓的元气,劳动创造的绝技,在漫长的上访路上湮灭净尽。天生异秉的生活执著者,被异化为平反后仍然纠缠不休的偏执狂,几乎成了四处流窜、诈骗的社会祸害。直到最后被安置到村福利院后,才成了远近闻名、信众广有的命相师。
虫嫂
虫嫂和老拐组成的“一不全活、一小人国”的家庭,从一开始就面临异于常人的生存压力。尽管虫嫂又机灵又活泼,但在接连生下两儿一女之后,生存压力与日俱增,为了把三个孩子养大,虫嫂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的挣扎和拼搏,以一种极度扭曲的方式,展开在无梁村的草野上,漫衍在中原大地的夜气中。她从在生产队场院里顺手牵羊的小偷小摸,渐渐变成了夜间游荡在集体庄稼地里的“惯犯”。(请注意,她只偷生产队里的,从不偷一家一户个人的!)她的活泼的、旺盛的生命能量,尽情地挥洒在她那“神偷”的种种技艺之中。不幸的是,这个草根神偷,又是一个身手灵活,健旺皮实的女人。她有“短”在不怀好意的男人手中,时间长了,终于被人突破了一个女人的心理防线,破罐破摔地沦为男人们约“谈话”的对象,同时也就成了村里女人们嫉恨的公敌。这个遭到命运重创的女人,独自继续着为自己、为家人的生存的挣扎。支撑她坚持下去,并开辟新的生路的,仍然是她憋屈而坚韧、无私而温厚的妻性和母爱。当她发现自己的儿女被村里顽劣的孩子谩骂、欺负时,她找到村支书,举着农药瓶以死相争。这一幕,让我们看到了她的母性尊严,甚至是威严。虫嫂这种护犊的怒吼、生命火花的爆发,形象地阐释了母性的伟大。
虫嫂在结束了她那草根神偷的生涯之后搬到城里,以拾破烂、卖废品为生,有时甚至卖血换钱,为得恶疾的老拐送了终,把3个儿女都供上了大学,创造了让无梁人啧啧称羡的奇迹。进城搞“商品经济”后这一段生活,是虫嫂生命中最快乐、最有光彩的时光。但是,当她老了病了,不得不让3个儿女接去轮流养活时,却阴差阳错地在三九寒冬被晾在了门外,于是便孤独地又回村了。
春才
春才曾是无梁村最帅气的小伙子,他一米八的个头,秀美壮硕、一脸红润,聪明而有艺术气质。但这样一个草根美男子,却是一个孤僻的闷葫芦。这个才禀独异的年轻生命,突然在一个诡异的日子里,在望月潭的苇荡深处,用蔑刀自宫了。作家描写了姑嫂婶娘对他的挑逗、刺激;描写了兔子家女人给他造成的别扭和尴尬;还描写了蔡苇秀与春才似有似无的接触引起的“案件”疑云等等,试图对“春才下河坡”事件给出一个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解释。其实,从小说对春才与性的种种幽隐闪烁现象的描写看,春才的悲剧是“性瘾症”病患者的一种病态。“性瘾者”是一种对性欲无法控制的心理疾病患者,这种病患者并不能从性活动中获得满足,相反会因性的或纵逸或压抑而陷入不能自拔的精神痛苦和肉体冲动中,其恶性发作足以导致摧毁一个人的生理系统。春才在不能见容于环境和社会的羞耻感的驱迫下,不能自控地“下了河坡”以求解脱,结果陷入另一种社会歧视和压力之中。作家对春才这个人物的描写,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描写他成为“废人”之后重新立身于世的生活故事。在传达有关“九一三”事件时他爆出的那一声“我不相信”,让我们窥见了这个“闷葫芦”内心沸腾、煎熬的底里和率真耿直的个性。此后,春才承包的豆腐坊赢得了与昔日“春才的席”一样的声誉。尔后,远方来的惠惠姑娘给予春才短暂的“幸福”之后席卷了豆腐坊的钱财,从此失踪,但春才对此却平淡处之。最后,他坚守着自己不掺假的豆腐坊慢慢老去。这个“很有骨气的失败者”,在他生命临近终点的时候,似乎返回到自己人生举步时的原点,守住了自己虽然残缺却纯粹的生命本真。
蔡国寅
他做村支书后成了抵御农村种种运动对村民伤害的刹车器,也逐渐沾染了山大王难免的一些坏习气。作为村支书,他举全村之力把孤儿“丢”即吴志鹏养大成人并让他上了大学,后来也因此当了用一张张“见字如面”的纸条,代表无梁村乡亲向吴志鹏求助的代言人。这个人物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似乎是有点讨人嫌的;写到最后,却让人由衷地敬重了。作家透过他性格上浮游的暗影不断地穿掘下去,一点一点地掘出那暗影下“埋藏的光耀”和“真正的洁白”来。[2]
杜秋月
杜秋月因“生活作风”问题以坏分子的身份被下放到无梁村,受改造、被歧视甚至批斗,在老姑父和乡亲们的帮助下,他和寡妇刘玉翠组成家庭,过起了略能温饱而不无苦涩的生活。这一知识分子融入农村、在颠簸中生存、变形、心灵渐渐粗砺化的过程,被描写得充满了喜剧色彩和反讽意味。世局变异之后,杜秋月开始了另一种磨难——这是他以欺骗手段使刘玉翠“被离婚”、被抛弃付出的代价。刘玉翠如影随形的纠缠,又泼又韧的“人肉搜寻”把他搞得颜面尽失,成了失业丧魂的废物。幸运的是刘玉翠没有抛弃他,而是一边养着这个废物,一边向人炫其余光。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杜秋月一心脱离无梁村的回城之旅,不但没能抛弃刘玉翠,反而开启了刘玉翠的进城经商之门。因历史的偶然性拨弄而落草成了山寨畸人的杜秋月,有时畸得可怜可爱,有时畸得可气可憎,最终让“历史的讽刺”对他作了“无情的修正”。杜秋月和刘玉翠夫妇的命运变化,像一面凹凸镜,照出了历史的变形与进步。
蔡苇香
蔡苇香是老姑父3个女儿中最小也最叛逆的异类。她从一个被退了3次学的不良少女,到跟人跑进城在“洗脚屋”和吴志鹏相遇,再到回无梁村盖起了村里第一座小白楼,最后在滚滚红尘中变成了无梁村板材公司的“蔡总蔡思凡”。在望月潭、芦苇荡和村野莽原的绿色大片大片地消失的沧桑变化中,蔡苇香这个山寨女畸人是“尽”了她的一份“力”的。她为老姑父迁坟,为父母合葬的尽孝盛事,也是在乡亲们眼前揭开所谓“汗血石榴”的真相,澄清流言为自己“平反”、恢复名誉的有力举措。小说结尾,她向漂泊在外、与她多有交集的吴志鹏提出了“投点资”的要求,却被吴志鹏嗫嗫嚅嚅地搪塞推托掉了。在吴志鹏看来,这个叫他“丢哥”,脸上已没有水气却堆满了“钢”色,说话透着狠劲的“蔡总”如此强势的存在,说明那个在“脚屋”里曾经偶遇过的身上还散发着无梁村的气味的苇香已经永远消失了。
作者简介
 李佩甫李佩甫,男,汉族,河南许昌人。1953年10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国家一级作家。1984年毕业于河南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系。1979年参加工作,历任许昌市文化局创作员,《莽原》杂志编辑、第二编辑室主任,河南省文联、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莽原》杂志副主编,河南省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金屋》、《城市白皮书》,《羊的门》、《城的灯》、《李氏家族》等7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黑蜻蜓》、《村魂》、《田园》、《李佩甫文集》四卷等,《颖河故事》、《平平常常的故事》、《难忘岁月——红旗渠的故事》、《申凤梅》等4部电视剧,电影《挺立潮头》以及多卷文集。曾先后获全国庄重文文学奖(1994年)、飞天奖、华表奖、五个一工程奖、人民文学优秀长篇奖、《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小说月报》优秀小说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奖。
李佩甫李佩甫,男,汉族,河南许昌人。1953年10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国家一级作家。1984年毕业于河南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系。1979年参加工作,历任许昌市文化局创作员,《莽原》杂志编辑、第二编辑室主任,河南省文联、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莽原》杂志副主编,河南省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金屋》、《城市白皮书》,《羊的门》、《城的灯》、《李氏家族》等7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黑蜻蜓》、《村魂》、《田园》、《李佩甫文集》四卷等,《颖河故事》、《平平常常的故事》、《难忘岁月——红旗渠的故事》、《申凤梅》等4部电视剧,电影《挺立潮头》以及多卷文集。曾先后获全国庄重文文学奖(1994年)、飞天奖、华表奖、五个一工程奖、人民文学优秀长篇奖、《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小说月报》优秀小说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奖。
作品赏欣
一个土地背负者的心灵史诗
以简单写复杂,以黑暗照见光明 以欲望的轻为灵魂的重作证
李佩甫习惯于从中原文化的腹地出发,书写平原大地上土地的荣枯和拔节于其上的生命的万般情状。
在他的笔下,乡村与城市、历史与现实、理想与欲望并置,其试图从中摸索出时代与人的命运之间的关联。
《生命册》中,既有对二十世纪后半期政治运动中乡民或迎合或拒绝或游离的生存境况的描摹,亦有对乡人“逃离”农村,在物欲横流的都市诱惑面前坚守与迷失的书写。
而横亘在所有叙事之下的,则是古老乡村沿袭而来的民间故事和传奇。在这里,民间世代相传根深蒂固的意识已经植入“背着土地行走”的“城里人”的灵魂记忆中,为“城里人”在新的价值观面前的迷茫和困顿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反哺和滋养。
借助这次写作,李佩甫完成了对知识分子在时代鼎革之际的人生选择与生命状态的诸多可能性的揭示,在无限逼近历史和人性真实的过程中,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具有哲理反思意味的人物群像图。
获奖记录
2015年8月16日,《生命册》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7]

-
做自己与别人生命中的天使
2025-11-03 23:11:20 查看详情 -
云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25-11-03 23:11:20 查看详情 -
长城汽车发布生命体征监测技术 16.68万元
2025-11-03 23:11:20 查看详情 -
长城汽车发布生命体征监测技术 主打硬派越野风格
2025-11-03 23:11:20 查看详情 -
长城汽车发布生命体征监测技术 或仍将以动物命名
2025-11-03 23:11:20 查看详情


 求购
求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