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呼愁

我的呼愁
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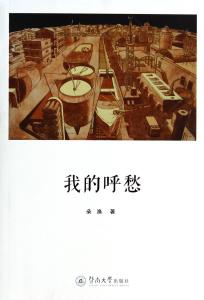 封面
封面
本书是一部人物杂记、亲情散文和成长小说合集,其中既有对故乡人物的杂忆,对故乡现状的忧思,也有对童年生活的追忆等。体裁多样,有短小的人物札记、随笔化的亲情散文,也有篇幅较长的成长小说,是一部诗性、纪实与望乡的交响。其中大部分文章为作者近些年来在各大媒体的专栏精选,如《财经·LENS》上的人物专栏、《南方周末》上的时评专栏、《晶报》上的散文随笔等。
作者简介
朵渔:独立诗人,专栏作家。1973年出生于山东,199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居天津,写作诗歌、随笔。曾获华语传媒年度诗人奖、柔刚诗歌奖、后天及奔腾诗歌奖、《诗刊》《诗选刊》《星星》等刊物的年度诗人奖等。著有《史间道》(天津人民出版社)、《追蝴蝶》(《诗歌与人》专刊)、《最后的黑暗》(北岳文艺出版社)、《意义把我们弄烦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原乡的诗神》(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生活在细节中》(花城出版社)等诗集、评论集和文史随笔集多部。
媒体推荐
四诗人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
暨南大学出版社倾情推出“还乡文丛”
近日,由诗人余丛主编、知名编辑杜小陆策划出版的“还乡文丛”第一辑已由暨南大学出版社正式推出。该文丛以“还乡”为立意,找寻精神的栖居之地,第一辑首先推出的是当今极具代表性的四位中坚诗人的散文随笔集,分别为朵渔的《我的呼愁》、育邦的《潜行者》、小引的《悲伤省》、周公度的《机器猫史话》。诗人们的非诗歌文本让读者得以全新的视角发现他们的精神世界,“还乡文丛”第一辑便是这四位诗人的“另一副笔墨”。
“还乡文丛”主编余丛在总序中以苏轼的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点出这套文丛的主旨——诗人们的“精神还乡”。所不同的是,朵渔的《我的呼愁》在精神还乡之外,还有对本义的故乡的深切回忆,这双重含义的望乡相互扭结和承载,形成浑融一片的乡愁;育邦的《潜行者》则一面对西方文学进行孜孜不倦地采撷,一面又警惕知识对心灵的蒙尘,作者在书籍与冥想间默默踩踏出一条精神还乡之径;小引的《悲伤省》是以居住的城市为原点,辐射向纹理多样的外乡,且行且思,对比更迭;佛学学者周公度的《机器猫史话》又是以仿若禅语的简洁,在还乡途中抛洒下大量留白的种子在读者心中落地开花。但诗人们在还乡之旅上的真诚是相同的,他们为此在字里行间倾注满满的恳切,并希望也能够告慰那些愿意阅读的知己。
在以受众数量衡量创作高低、码洋数量决定出版与否的时代,太多严肃文学作品和它们的作者被湮灭,而诗人是其中境况最为惨烈的一群。就这一背景而言,暨南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还乡文丛”并首推诗人的四部专著可谓“偏向虎山行”的大胆之举。“市场”与“评奖”是所有出版社都必须面对的现实,但在这两者的夹缝中努力为已式微的严肃文学保留一席之地,便体现了一家出版社在气格上的与众不同。也许文学还原了出版者最初的梦想,而“还乡文丛”的出版便是向初衷致敬,也便同样具有着“精神还乡”的意义。
(顾星环)
图书目录
辑一
3妈妈,点灯
6母亲的教诲
12父亲在杀一只羊
16他终于输掉了最后一枚硬币
20一家人在吃饭时讨论的政治话题
23五个父亲
28还差五分钱
34爬瓜
38迷藏
42抓小偷
45高音喇叭
47一坨屎
53一碗汤
56阿德
64老歌三首
71记忆练习
辑二
85表兄小宝的生与死
88那一年,我们去河滩看杀人
92战斗英雄白跑路
96草原啊月光啊战马
100五火上树
104小巷里的第欧根尼
108雨季来临之前死去
112牛棚记
116一头猪,两只羊
120红旗家的儿女们
124我们的黄司令
128枪和爱情
132在一起,在一起
136夜晚的疯国王
140王蝴,你还记得我吗
144能人今喜
辑三
151在社会上
170亲爱的舅舅你好
185树袋鸟
200夕光照影
213附:“其实你的人生是被设计的”——朵渔访谈
233故乡就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地方(代后记)
后记
故乡就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地方(代后记)
朵渔
返身回视那道深渊……
读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被他的“呼愁”感动。“呼愁”,土耳其语“忧伤”的意思。这汉语翻译得真好,比忧伤更加忧伤,且多了一层历史的悠长感。在帕慕克眼里,这种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准确地说,这是整座废墟之都的忧伤,覆盖在整个斜阳帝国一切残留之物上的忧伤。当帕慕克穿行在那破败、灰暗、没落而又处处遗留着古老帝国残砖断瓦的街头巷尾,他慨叹道:“我出生的城市在它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它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它成为自己的忧伤。”在帕慕克的笔下,整个帝国的残留物汇入他个人的生命里,渗入他的血液和生命,成为他个人的命运。
一切庞然大物的轰然倒塌,都会留下一堆使人忧伤不已的历史废墟,让人凭吊、感叹。克里米亚战争瓦解了伟大的奥斯曼帝国,使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成为单调、灰暗的“呼愁”之城。“泥泞的公园、荒凉的空地、电线杆以及贴在广场和水泥怪物墙上的广告牌,这座城市就像我的灵魂,很快地成为一个空洞,非常空洞的地方。”相对于帕慕克那座伟大的城,我的“呼愁”则来自于一个带着集体主义余温的贫瘠的村庄。离开家乡二十多年了,我对家乡的很多记忆已渐渐模糊,但每次忆及,都忧伤不已。
我出生在70年代初期,和很多同龄人的记忆不同,我最初的记忆就是:吃。我记得我吃过榆树皮、地瓜干、槐花、榆钱、茅根、桑葚、癞葡萄、玉米秆、高粱秸、炸蝉蛹、烤蚂蚱、烧麻雀……冬天是最艰难的岁月,因为土地封冻了,连田鼠也不再出来活动,需要靠一堆地瓜干、萝卜和白菜挨过去。春天一到,土地复活,一些可以充饥的东西渐渐从土里长了出来。我们脱掉棉裤,钻进麦田里,找吃的。夏天上树,瓜果梨枣;秋天要奢侈一些,偷生产队的玉米、黄豆,生一堆火,烤着吃;我记得还有一条人工河,河水清澈,水草茂密,我们跑去捉鱼,摸虾……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期。
我记得,那时候生产队最大的产业是一座牛棚,黄牛、马、骡子和拉磨的驴。那时候,公社的拖拉机站已经废弃,巨大的锈红的铁疙瘩被扔在黄叶枯草间;一座被鸟巢占据的烟囱早已不冒烟,围墙倒塌,废料遍地,那是乡村唯一的工厂……那时候,最爱闻的是汽油味,穿绿衣的邮递员,骑着一个小电驴……最爱玩的是火和水,冬天玩火,夏天玩水。那时候,家里唯一的工业品是一个汽水瓶子,唯一的玩具是一只黑狗,我把它训练成了全村最凶猛的狗……
这几乎是一种无法选择的命运,成为我身后的一道深渊。如今一切都已远去,但不是变得更好了,而是更糟。新的“呼愁”出现了——河流变黑了,鸟巢变少了,烟囱一座座竖起,田地一片片圈起,残垣断壁中,住着老人和孩子……帕慕克尚有“如丝巾般闪烁微光的博斯普鲁斯”可以守望,而我们却成为失去传统的人,失去乡村的人,依然处在自己长长的“呼愁”里,走不出。
我是如何滚出故乡的
我时常设想:假如我没有考上大学,那么我现在在干什么?哦,这一设想实在太残酷了。如果没考上大学,我大概也不可能走出那片村庄,不可能读书、写作,不可能完成自我的启蒙和自救;我也许会走出村庄,进入都市,像大部分打工者一样,处在挣扎的境地,从一道深渊跌入另一道深渊……事实上高考对于我一直是一个噩梦,直到几年前,我还时常被这噩梦惊醒。梦的内容几乎是一致的:坐在大学的教室里,突然被宣布没考上,然后是头脑一片空白……为什么对高考如此“刻骨铭心”?实在是因为在专制制度的安排下,我们改变自己命运的途径太少了,而“高考”作为唯一的“窄门”,唯一通往生命上升之途,被我们寄寓了太多的厚望。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一员,在教育资源严重分配不公的情况下,要想闯过那道命运的窄门,将是怎样的幸运,其中又夹杂着多少的不幸!
我接受的是中国乡村最普通的学校教育,而且还成了不幸中的幸运儿。我不仅闯过了高考的窄门,并且由此改变了生命的轨迹。而我的大部分儿时的伙伴则没有这么幸运,他们被一道道门所阻拦,绝大部分倒在小学毕业线上,一小部分熬到了中学,如此一层层筛选,我成了唯一的“漏网之鱼”。如今,大部分“光荣”的毕业生们仍处在社会的底层,或外出打工,或在家务农,重复着他们父辈的命运。
当我从村中那所小学校开始,经过层层肉搏,滚出故乡后,就很少回乡下了。最近每次回去,都觉得惭愧不已、悲哀不已。像我这样中举般滚出乡村的,实在算是祖坟上冒了青烟,幸运之极。其他的同龄人,也大多走出了乡村,但他们是另一种轨迹:打工。打工者,大多是一个人出去,而家依然在乡村,根依然在乡村。往往是过年时回来一趟,播下颗种子,再出去谋生路。那种子生根、发芽,而父母已不在身边。现在的乡村,几乎就是儿童和老人的世界。每次看到那些光腚游戏的孩子、那些弯腰驼背的白发老人,心中就会有隐痛。谁来教育这些孩子?谁来传承乡村文明?面对1914—1918战后一代的德国人,本雅明曾慨叹,那些在壁炉前为子孙们讲故事的人彻底消失了,“哪儿还有正经能讲故事的人?哪儿还有临终者可信的话,那种像戒指一样代代相传的话?”本雅明痛感一代人经验的贫乏,并称之为一种“新的无教养”。如本雅明所说的那“在壁炉前讲故事的絮叨者”,如今又在哪里?是那些留守乡村的祖父祖母们吗?他们终日劳碌、奔波与蒙昧,又如何充当一个“讲故事者”?于是,我们这里的“新的无教养”出现了,新的“经验的贫乏”出现了。“我们变得贫乏了。人类遗产被我们一件件交了出去,常常只以百分之一的价值押在当铺,只为了换取‘现实’这一小块铜板”。
为了一小块铜板,那些乡村的打工者甚至抵押上了自己的后代——这唯一的改变命运的窄门也被迫关闭了。而作为从乡村出去的知识分子,我的责任与承担又在哪里呢?我甚至很少回到乡下!在空虚的乡村,我成了一个新的“抽取者”,只有抽取,没有回报。
从乡村到城市的路有多远
在前两年召开的“两会”上,有政协委员表示“不鼓励农村孩子读书”,理由是现在读大学费用太高,农村孩子出来读书往往会使整个家庭返贫;再加上没有家庭背景和人脉资源,因此很难找到工作;即便勉强留在了城里,还要面临买房难、结婚难,“人生中有这么多难,不是悲剧是什么?”
该委员这番建立在“出身论”基础上的糊涂建言,也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一个人的出身对人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史记·高祖本纪》说刘邦其母“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而项羽就差远了,“少时,学书不成,却学剑,又不成”,看来本非“真命天子”。这当然都是“祛魅”前的春秋笔法,仅供一哂。近读杨联升先生解读《侈靡论》,讲到一个“倒吃甘蔗”的故事。故事引自《世说新语》“排调”篇:“顾长康啖甘蔗,先食尾。问所以,云:‘渐至佳境。’”顾长康即东晋名画家顾恺之。说当顾恺之吃甘蔗的时候,通常由尾部向中间嚼起,最后“渐入佳境”。杨先生将其解读为一个用来贬斥奢侈与浮华的心理方面的个人事件,“提高一个人的生活水准是很容易的,而降低则甚痛苦,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倒联想到一个人的出身问题。大凡出身贫寒,童年时衣食匮乏者,长大后吃好东西时常会战战兢兢,倍加珍惜。吃苹果先从青的一面吃起,吃饭把肉留在碗底最后享用。此是经验之谈。本人出身贫寒,兄弟又多,常觉食物匮乏,每得美食,猫狗护食一般,衔至一边,由苦至甘,慢慢享用。此等上不得台面的独食方式,至今犹保留着,常遭人嘲笑。我只能以“出身论”搪塞,找不到更好的理由。
不承认“出身”对一个人的巨大影响,也是不客观的。出身代表一个人的成长背景,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城乡二元结构的国家,出身的影响更加明显。出身农家,很多机会、资源、背景均与城里人相差霄壤,一个农村孩子首先想的是如何变作一个“城里人”,这是第一步。再往前,成家、生子、供房子,每一步都不轻松。而在这个新“城里人”的背后,还有一大堆乡下穷亲戚需要照顾。巴尔扎克说三百年才能造就一个贵族,在我们这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三百年太久,但也绝非一朝一夕。
关于这本书里的这些文字
这里所集的这些文字,大多与童年和故乡有关。有几篇曾收在北邮版随笔集《原乡的诗神》里,这里拆借几篇,以使本书稍显完整。文字拉杂,风格不一,有些甚至写于二十年前,大概也是我最早的习作了,幼稚不堪自然难免。如今重新扫作一堆,敝帚自珍之,实在是觉得还有一点天真在,还有一点时光的印记在。这些文字不尽是纪实与回忆,有不少篇什是当年学习小说的练笔之作,真实与虚构穿插其间。在此稍作说明,心中仍不免惶惶然。
2013年9月
序言
总 序
余 丛/文
苏轼说,此心安处是吾乡。还乡是喜悦的,是恳切的,但也仅仅是一种愿力。
我们捡拾的是内心。如何写?写什么?在此都顺应了内心,那也是精神还乡唯一的去处。
还乡是一个梦,是乡愁,是永无止境的抵达。我们寄望于怀旧、后退,甚至是保守的;我们寄生于乡土、故里,甚至是故步自封的。
不是我们流离失所,而是我们还乡之乡已经沦陷。灵魂向何处安顿,没有精神的还乡,就永远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说:“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
还乡者在路上,在返程的途中;还乡者是过客、旅人,是不合流俗的边缘人和问津者。在漂泊不定的异乡,还乡是我们的忧伤艺术。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彷徨四顾,对未来又充满希冀。但是故乡在远方,于我们而言,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还乡文丛”是立意,是重塑,而非局限;是敞开的,融合的,也是繁殖的。哪怕仅仅是文字上的还乡,虽然它无法抵达,但或许能安放我们的心灵。
一方故土,是源头,是离散的地方……却又在等候着还乡者的归来。
2013年10月22日



 求购
求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