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恋爱中的男人

恋爱中的男人
内容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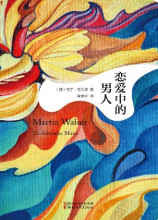 恋爱中的男人(3) 80岁的德国老作家 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2月29日出版了小说新作 《恋爱中的男人》(Einliebender Mann),赫然以大 文豪 歌德为主人公,写他在1823年, 古稀73岁,戴着 面具参加 温泉城 马里昂 巴德的异装舞会,对19岁少女乌尔丽克 一见倾心。
恋爱中的男人(3) 80岁的德国老作家 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2月29日出版了小说新作 《恋爱中的男人》(Einliebender Mann),赫然以大 文豪 歌德为主人公,写他在1823年, 古稀73岁,戴着 面具参加 温泉城 马里昂 巴德的异装舞会,对19岁少女乌尔丽克 一见倾心。
“他看到她时,她早已捕获了他的目光”。 老翁少女 眉目传情,歌德 神魂颠倒,再也不能自拔,先是百般勾引,继而发动连番 情书攻势,欲娶少女入门。孰料女儿妒意横生,从中作梗,坏了老诗人的好事。歌翁伤心作别,回到 魏玛,终日 郁郁寡欢,至1832年去世。时光如梭,乌尔丽克亦成老妇,临终前将歌德的情书 付之一炬,一段奇特的 祖孙恋情就此深埋。
这段 黄昏恋并非作家杜撰,而是大体上实有其事。乌尔丽克·冯· 莱维措(1804-1899)据说 才貌双全,年轻时一度与晚年歌德关系密切,歌德曾动过娶她的念头,还因为她写了不少 情诗,最有名的是《玛丽昂巴德悲歌》。
出版商为《恋爱中的男人》打出 广告词,称此乃“歌德最后一爱――马丁· 瓦尔泽首部 历史小说”。评论界大举鼓噪,推动此书在市场上 快马加鞭。截稿前,我看了一下本周 《明镜周刊》的畅销书榜,《恋爱中的男人》仍然稳稳地排在第十名的高位。
在德国,老 瓦尔泽是国宝级的作家, 毕希纳奖和德国书业和平奖的得主,论文笔,论阅历,绝对不在任何人之下。为歌德 代写情书一事,他做起来游刃有余,足可乱真,而老翁钟爱少女时的迷乱 春心,也刻画得 入木三分。
他写 德国史上头号文豪晚年 春情上头,十分有趣――如果不是让 老无所依的翁叟们略感心酸的话。书中歌德裸身对镜自赏,验证是否 雄风犹存――结论是:还行。而少女乌尔丽克 花枝招展,刁蛮可爱。一老一少, 共谱恋曲,其音调必是古怪别致,妙趣横生。
瓦尔泽曾应邀在 读书会上朗读新作,联邦总统亲自到场, 正襟危坐, 洗耳恭听。大作家开读不久,席间即爆出笑声,稍顷复笑。这可是德国,不是美国。更何况台上是瓦尔泽,台下是总统。听众 笑场一事遂成媒体津津乐而道之的 花边新闻。3月25日出版的 《法兰克福汇报》还特地为此专访了当时也在现场 乐不可支的老评论家约阿希姆·凯泽(Joachim Kaiser),主题是:瓦尔译的新作有那么可笑吗? 德国人怎么会笑成这样?老先生说:那实乃发自内心的笑声,瓦尔泽写得好,尤其是歌德与少女互施媚术的部分,实在令人愉悦。
笑归笑,也有女读者就书中的 情欲描写向瓦尔泽发问,比如,他为啥反复使用“ 那话儿”(Iste)一词?瓦尔泽从容回答,他写的不是德语,而是个 拉丁语词,且无具体词义。的确,在拉丁语中,Iste是个阳性代词,以“那话儿”译成中文,大抵不错。
大部分评论家认为,瓦尔泽的小说不会令他们心目中的歌德形象发生改变。 曼弗雷德·奥斯滕(ManfredOsten)说,瓦尔泽准确描写了老翁春心重萌时的心理,寄托了人类对生命回春和永存不朽的渴望。托马斯·安茨(Thomas Anz)则通过书中歌德对 法国革命的关注,注意到了一个政治化的歌德,以及一个政治化的瓦尔泽。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书大唱 赞歌。沃尔夫冈·弗吕 瓦尔德(Wolfgang Frühwald)便说:“这是瓦尔泽的歌德,不是我的。至多是1823年的歌德。……我心目中的歌德不会改变,但我心目的瓦尔泽变了。”他指出,年龄总是让作家感到困扰,瓦尔泽晚年作品的性成分越来越多,这也许是因为越是老人,越要表现出年轻的感觉。韦尔纳·弗里岑(Werner Frizen)则认为,瓦尔泽写的不是歌德,而是 维特;躲在面具后面的也不是歌德,而是瓦尔泽。
本书作者
马丁·瓦尔泽生于1927年3月24日,二战期间在德军 防空部队服役。据2007年6月公开的档案显示,他可能曾于1944年1月30日加入过 纳粹党。战后瓦尔泽在 雷根斯堡和 图宾根求学。1951年以关于 卡夫卡的论文获得 博士学位,同时开始 文学创作,并加入了 先锋文学团体 四七社。他以1978年出版的 《惊马奔逃》(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过 郑华汉、朱 刘华等人的 译本)广获文坛承认。中国内地还出版过他的《 迸涌的流泉》、《 爱情的彼岸》、 《菲城婚事》等书。
瓦尔泽得到过 联邦德国的多种文学奖项,如1957年的 黑塞奖,1981年的毕希纳奖,1998年的德国书业和平奖。
他也是个多次引起争议的作家。1998年,在接受书业和平奖时,他因口出“ 奥斯维辛不应该被工具化为道德俱乐部”一语而闯祸,为此受到 犹太人团体的攻击,但得到了诺贝尔奖得主 君特·格拉斯的声援。
2002年,瓦尔泽的小说 《批评家之死》(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有黄燎宇的中译本)在正式出版前,被 《法兰克福汇报》拒绝选载,同时受到该报严厉的公开批评,称该书充满了对犹太人的仇恨。瓦尔泽的确在书中影射了德国最著名的评论家之一、犹太人 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Marcel Reich- Ranicki),但他坚决否认在主人公的犹太人身份上 大做文章。争论之激烈,使《批评家之死》成了当年德国最受瞩目的小说。
当代 德国文学不仅有君特·格拉斯、恩岑斯贝格等人,还有一个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马丁·瓦尔泽创造一种马丁·瓦尔泽式的“角色散文”。他以刻画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为主,像他的前辈 托马斯·曼一样,笔底汇集了哲学、 诗学、批评等不同门类的思想精髓,有时也流露出沉静的嘲讽和悲伤。他的格言是:“对于小说家来说,观点犹如短路。”或许,他的写作正是由此而得以避熟就生。
在德国战后文学史上,排在 海因里希·伯尔和君特·格拉斯这两位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之后的著名作家,恐怕就要数马丁·瓦尔泽了。
瓦尔泽多次短期到美国和英国的大学讲学,讲授德国文学和创作课程。他是德国四七社成员、国际 笔会 德国中心理事、柏林艺术科学院院士、德意志语言文学科学院院士。
瓦尔泽被誉为“驾驭语言的能手”(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莱希-拉尼茨基语),他的小说被称作优美的散文作品。在叙述中插入对话是他的小说的一个特色,这些对话不加 引号,读者必须细心阅读方能辨出说话者。瓦尔泽称自己是古代 阿雷曼人的后裔,因此他的作品中常有方言出现。他的不少小说在情节上虽然并无上下承接关系,但是一个主人公常常出现在几本书里,如 《间歇》(1960年)、 《独角兽》(1966年)和 《堕落》(1973年)中的昂塞姆·克里斯特莱因,《爱情的彼岸》(1976年)和《致洛尔特·李斯特的信》(1982年)中的弗兰茨· 霍恩,《惊马奔逃》(1978年)和《 激浪》(1985年)中的赫尔穆特·哈尔姆,《天鹅之屋》(1980年)和 《狩猎》(1988年)里的 房地产商格特利布·齐日姆。
《惊马奔逃》一书在1978年春出版之后在联邦德国文坛引起轰动,它不仅跻入当年十大畅销书之列,而且获得评论界几乎 众口一词的赞扬。莱希-拉尼茨基在联邦德国最有影响的日报《法兰克福汇报》文学版上发表文章,他写道:“我认为,马丁·瓦尔泽的中篇小说《惊马奔逃》是他最成熟、最出色的书。这个描写两对夫妇的故事是这些年来德语散文的一部杰作。”
瓦尔泽本人对这部小说也非常得意,他曾独自或与人合作将小说分别改编成剧本和 广播剧。
正像 德国书业协会在向瓦尔泽颁发书业和平奖时所称:“瓦尔泽以他的作品描写和阐释了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德国现实生活,他的小说和随笔向德国人展现了自己的祖国,向世界展现了德国,让德国人更了解祖国,让世界更了解德国。”
德国“齐切罗”月刊再次发表了五百名在世德国知识分子排名榜。这里知识分子指的是接受过科学或艺术教育、从事 脑力劳动的人。出人意料的是, 罗马教皇 本笃十六世高排榜首。
排名顺序并非某个评选委员会的评选结果,也不是 民意调查的归纳,而是电脑查询情况的总结。调研人员按照一些关键词,对电子数据库进行过筛式的挑选。此外,还借助互联网,查找160家 德文报章杂志中引用的“字句”和文章段落,对得出的数据进行评估,决定上榜的人选和 座次。另外,还精确标明上榜人选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座次上升或下降的情况。
大致看一下这个排名榜,就可以发现,新闻界成了德国社会中思维和诠释的主流。一半评上的人选虽然座次有前有后,但他们都来自新闻媒体的编辑部,另一半是作家、导演和个别科学家。
高踞首位的是教皇本笃十六世。两年前,这位名为拉青格的 红衣 大主教选为教皇,成了首任“德国教皇”。以他渊博的知识,在这五百名知识分子之中,他也许是少数不愧知识分子称号的真正知识分子之一。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分别是德国首屈一指的名作家兼戏剧家马丁·瓦尔泽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家君特·格拉斯。 格拉斯以 和平主义著称,但前一段时间,他承认自己在二战后期是纳粹党卫军成员,此事一度在德国媒体引起了轰动。名列第四的是德国电视主持人 哈拉尔德· 施密特,此人嘴快、言辞犀利,是谈话类 电视节目的“ 开心果”。
前东德共产党-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1990年之前一直担任东德作协主席的赫尔曼·康特也排上了座次,位居第249名。当年,他主持下的作协曾把一系列持不同政见的东德作家开除出作协。甚至 萨沙·安德森这名早被揭发的前东德国家安全局著名特务也排上了倒数第二位。
其实,德国的知识分子多年来处于沉默状态,对重大的政治问题很少表态,更不用说发表一些 原则性的观点。如果说点什么,也只是老一套。老一代的作家和其它知识分子中,一些人仍然背有“历史 包袱”,因为曾经追随过纳粹党,他们慎于言行,恐怕被媒体抓住 辫子,作家格拉斯就是一个例子。而三十岁至四十岁的一代知识分子很少意识到自己在道义和思想上负有的责任,对世界和社会更多采用无所谓的态度。如此看来,这样的知识分子排名榜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编辑推荐
《恋爱中的男人》:晚年歌德的最后一段传奇恋情,当年逾七旬的老诗人遇见十九岁的少女……德国当代作家马丁•瓦尔泽力作,面市以来畅销不衰。
作者简介
作者:(德国)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 译者:黄燎宇
马丁·瓦尔泽,德国著名作家。生于博登湖畔的瓦瑟堡。1957年成为职业作家。代表作有《菲城婚事》(1957)、《惊马奔逃》(1978)、《进涌的流泉》(1998)、《批评家之死》(2002)等。曾获毕希纳奖等多项文学大奖。《恋爱中的男人》曾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
 恋爱中的男人图册(3)
恋爱中的男人图册(3)
序言
谁是马丁·瓦尔泽?二○○九年六月三十日,当瓦尔泽在柏林的中国文化中心朗诵《恋爱中的男人》选段时,进行报道的两位记者给出了形象生动而又言简意赅的答案。其中一位写道:“他是我们在世的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位。马丁·瓦尔泽一说话,德国人都会侧耳倾听;瓦尔泽的书一问世,德国人就会争先恐后,先睹为快,然后展开激烈辩论。”另一位则指出:“马丁·瓦尔泽在哪里出现,哪里就座无虚席。柏林的中国文化中心的多功能厅也不例外。”通过这两句相映成趣的话,瓦尔泽在德国的文学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可谓跃然纸上。
对于瓦尔泽,我们的读者并不陌生。他的好几部小说已译成中文出版,他的短篇小说、演说稿以及随笔也上过我们的文学期刊,有的杂志还做过他的作品专辑,介绍和研究他的文字也越来越多。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必要在此对其生平进行简要交待。
瓦尔泽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博登湖畔的瓦瑟堡。父母经营祖传下来的餐馆兼旅店,同时做点木柴和煤炭生意。父亲在他十一岁的时候病逝。他很早就跟哥哥一起做母亲的帮手,做过账,也运过煤,由此长了不少见识,也锻炼出一副好身骨。一九四四年他应征入伍。一九四六年上大学。先后在雷根斯堡和图宾根攻读文学、哲学、历史、宗教、心理学。一九五一年以研究卡夫卡的论文《对一种形式的描述》获图宾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标题与卡夫卡小说《对一次战斗的描述》相呼应)。随后在位于斯图加特的南德意志电台做了几年记者和导演。他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写作,一九五三年开始参加堪称联邦德国文学家摇篮的四七社的活动,一九五七年成为职业作家。瓦尔泽是写作多面手,既写小说、剧本,又写文论、政论、随笔、杂文;他也是写作快手和写作高手。经过几十年的写作积累,他不仅著作等身,而且有多部作品脍炙人口,雅俗共赏。一九九七年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了十二卷本的《马丁·瓦尔泽文集》。如果今天再出一套瓦尔泽文集,估计得有二十卷。
瓦尔泽的文学成就得到了社会的充分认可。他获得的各种大奖就有二十来个,其中包括联邦德国最有分量的文学奖格奥尔格·毕希纳奖,还有德国政府颁发的大十字功勋奖章。各种顶尖级文学团体和学术机构授予他的头衔也有一长串。此外,他还享受着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德国作家在有生之年享受过的待遇:雕塑家彼特·林克受其著名中篇小说《惊马奔逃》的启发,塑造了一尊具有怪诞风格的瓦尔泽驾驭惊马像。塑像矗立在博登湖畔的于伯林根市中心广场,因为瓦尔泽是于伯林根市的市民和选民。但是这样的待遇也不算过分。今天的瓦尔泽已被视为“文学君主”,在德国文坛牢牢地占据了数一数二的位置。对此,一位俏皮的德国作家调侃说:“没有文学君主的德国和没有冲突的中东一样难以想象。马丁·瓦尔泽是我们当今的文学君主。有一阵他不在位,在位的是君特·格拉斯,格拉斯登基之前瓦尔泽在位,瓦尔泽登基之前又是格拉斯在位。”
瓦尔泽在文学上很成功,在生活中也同样成功。作为享誉世界的作家,他常常人在途中,云游四方。但他同时拥有一个仙居,一个安乐窝。他生在博登湖畔,长在博登湖畔,成家立业之后又扎根博登湖畔。一九六八年,他率领全家搬进了于伯林根市东郊的努斯多夫镇的一栋别墅,一幢能够将博登湖的美景尽收眼底的亲水豪宅。这里就此便成为他永远的居所。这栋房子不仅有仙风道气,而且充满人气和亲情。瓦尔泽是一个早婚早育的作家。他二十三岁就与青梅竹马的卡塔琳娜·诺伊纳一耶勒结婚,婚后有四个女儿。她们个个才貌双全。约翰娜、阿丽莎、特蕾西娅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弗兰齐斯卡成为小有名气的演员。瓦尔泽一家也由此成为与托马斯·曼一家类似的文学豪门。但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瓦尔泽远比作为一家之主的托马斯·曼幸运,因为他是孩子们的慈父、朋友、领路人,托马斯·曼与其子女的关系却令人遗憾。有趣的是,瓦尔泽最推崇的德语作家也叫瓦尔泽——罗伯特·瓦尔泽。这位在二十世纪初昙花一现的瑞士德语小说家是一个文学奇才,通常被视为卡夫卡的先驱。也许因为瑞士是遍布世界的瓦尔泽们的发源地,马丁·瓦尔泽对其瑞士本家情有独钟,自述将罗伯特·瓦尔泽的小说《雅各布·封·贡腾》认真读过不下二十遍,随便翻过近千遍……
瓦尔泽也是德国文坛数一数二的性格人物、话题人物、争议人物,是一个有人捧、也有人推的不倒翁:他的演讲会或者作品朗诵会很容易招惹热血青年,反对他的标语和口号屡见不鲜,另一方面,德国总统也在他的演讲会和朗诵会上频频现身,德国驻外大使在他来访之时待他总是如接待总统、总理一般。难怪他连续几年在德国权威的政治学杂志《西塞罗》颁布的知识分子影响力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二○○七年他还排行第二,紧紧跟在教皇本笃十六后面。瓦尔泽有如此耀眼的人生,是因为他有三颗灵魂:他有一颗艺术魂,所以他把自己的作品当自己的孩子对待,谁对他的孩子好他对谁好,谁欺负他的孩子他跟谁急,在他这里,文坛恩怨很容易成为政治事件的根源;他有一颗英雄魂,讲义气,重尊严,遭遇不平的时候既敢动口也敢动手,有时还被裁定为防卫过当;他还有一颗民族魂,因为他痛切地感觉到沉重的历史包袱给当代德国人造成的精神不正常和思想不自由,所以他时不时地要充当德意志火山,喷出德意志熔岩。
瓦尔泽的性格刚柔相济。他是勇士和斗士,但同时也是绅士和骑士。他充满智慧和幽默,讲话有分寸有品位。他知道如何对人进行表扬,更知道如何接受表扬。对于“文学君主”的称号和瓦尔泽一格拉斯轮流执政说,他的回应是:“有些作家如果有幸活到八十岁,他们就会进入我和格拉斯这样的角色。有些事情需要你活到八十岁。到时候一切都会送上门来。”他的歌德小说几乎人见人爱,大家都想知道为什么,他却是一脸的无知和无辜:“我是第三次遇到这种情况了。《一匹在逃的马》、《一座奔涌的流泉》、《一个恋爱中的男人》——这三本书的标题都是‘一’字开头,读者的反应都很热烈。我也不清楚这是为什么。”需要指出的是,中文比较忌讳不定冠词,所以这三篇小说的中文标题分别为:《惊马奔逃》、《进涌的流泉》、《恋爱中的男人》。笔者在他家里享受了几天五星级待遇,过后写信致谢,他却回信宣布笔者获得“客人表现金牌”;读了笔者高调赞美他的文章,他的来信落款就成了:“您的瓦尔泽原型”;他对中国有好感,就把“中国”解构为“依然位于世界中央的帝国”,就说德国媒体制造“符合政治正确原则的中国形象”。他让笔者悟出一个大道理:大师的标志之一就是出口成章。
《恋爱中的男人》取材于真人真事。人非普通人,事非平常事,因为这是七十三岁的歌德在疗养胜地马林巴德爱上十九岁的姑娘乌尔莉克·封·莱韦措的故事,不朽的《马林巴德哀歌》就是从这未果的爱情绽放的艺术花朵。马林巴德的故事在德语文学圈内几乎路人皆知,同时也是歌德研究中的一大悬案。人们明里暗里总想知道歌德为何“老不自重”,为何“晚节不保”。一百年前,托马斯·曼就想以“歌德在马林巴德”为题写篇小说,后来却因为某种顾虑而改弦易辙,写出了中篇杰作《死于威尼斯》。也许是巧合,喜欢跟托马斯·曼唱对台戏的瓦尔泽偏偏在托马斯·曼留下的创作废墟上搞起了建筑。二○○七年夏,八旬老翁瓦尔泽全力以赴投入了歌德小说的创作。他写得异常顺手,也异常投入,他几乎是在情感沸腾和情感地震状态中写作,以致搁笔之后好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心情都无法平静,他的情感也无法冷却。但是他没有白费工夫,也没有浪费感情,因为他把“歌德在马林巴德”的故事变成了一部出版前就好评如潮、上市之后又持续热销的爱情小说。这本小说不仅让本来就喜欢瓦尔泽的读者和评论家欣喜若狂,也让中立的评论家和读者发出赞叹,甚至连此前与瓦尔泽势不两立、与他处于热战或者冷战状态的机构和个人也跟他握手言欢……
《恋爱中的男人》为何如此成功?这个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说它复杂,一是因为好作品都以多义性为标志,写得越好的小说,涵义就越是丰富。好的作品全都拒绝单一和最终的阐释,全都历久弥新,常说常新。再者,文学阅读就是读者与文本的精神碰撞,同样一个文本,在跟阅历、知识、情感、趣味各不相同的读者碰撞的时候自然会进出不同的精神火花。有的火花还会让作者本人瞠目结舌。简言之,成功的作品总让人一言难尽,伟大的作家都是“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是歌德最先喊出这不朽的口号)。说这个问题简单,是因为成功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表达了千万读者的心声、引起千万读者共鸣的作品。尽管《恋爱中的男人》的主人公是伟人歌德,尽管它讲述的是年龄悬殊的老少恋,但是爱情和人性的本质依然在恋爱中的歌德所经历的天堂地狱、在歌德的爱欲引发的人性光辉和人性阴暗中若隐若现。读着歌德的故事,不论男女老少都有可能暗自感叹“这就是我!”与此同时,常识又告诉我们,深刻的文学认识有赖于高超的艺术刻画,所以说文学作品的成功与否,与其说看它“写什么”,不如说看它“怎么写”。说到底,就是看它的语言。
瓦尔泽是公认的语言大师或者说语言魔术师。他的句子大多没有长度,但多半充满深度和弯度,多半曲里拐弯、耐人寻味;他从不打引号,迫使读者在叙述者和人物之间来回奔波,左顾右盼(译文中加的几个引号是为了避免冲撞中文语法和阅读习惯的底线);他深谙文学语言的本质,轻外延重内涵,喜欢玩内涵游戏,让读者的知识和想象接二连三地受到挑战和刺激。他的语言是思想者的语言,对于读者具有健脑益智之效。但瓦尔泽不单是思想者,他还有着丰沛而强烈的情感,还能够让丰沛而强烈的情感活跃在字里行间。从《恋爱中的男人》可以看出,瓦尔泽的语言让诗意和思辨、讽刺和忧伤水乳交融。它再次证明作家是天之骄子,是上帝的宠儿,证明文学家在语言表达方面具有两栖优势,从而优于诸子百家。这正如托马斯·曼在《死于威尼斯》中所说,“作家的福气”在于“思想能变成情感,情感能变成思想”,在于作家们既有“沸腾的思想”,又有“精确的情感”。也正因如此,《恋爱中的男人》一面闪耀着思想和智慧的光芒,让读者享受思维快乐和精神保健,一面也具有情感震撼力和情感杀伤力,可以让人肝肠寸断、泪流满面。
这样的语言,翻译起来自然是无比的快乐,但是也无比地艰难。歌德在给乌尔莉克的第一封信中承认自己“也是一家公司”,因为自己有很多“手下”。这句话别人看了也许不会有什么触动,笔者却是感慨万千。歌德是伟人,当然需要别人给他打杂、垫背。瓦尔泽让歌德做老板可谓合情合理。无独有偶,托马斯·曼笔下的歌德也有老板的身影,因为《绿蒂在魏玛》中的歌德总是让别人去“卖力、开采、冶炼、积累”,自己只“等着打制金币”,所以他身边的人纷纷感叹“伟人乃公众之不幸”。让笔者长吁短叹的是,像笔者这样一个区区小人物,翻译瓦尔泽的一本小说仿佛也需要成立一家公司,也需要做一回老板。这是因为:德文理解需要请教包括瓦尔泽在内的德国人,遇到其他外文则必须求助其他语种的同行,中文表述需要高明的同胞帮着推敲(吾友沈中明功不可没),专业词汇必须跟各路神仙虚心请教,定稿之前不仅需要友人在文字上面把关,而且需要学习“妪解则录”的白居易精神。掐指一算,笔者前前后后至少动用了一个排……翻译这么点东西就动用这么多人,不知是因为自己太笨、太离不开人,还是说译者本来就不应单打独斗(马丁·路德似乎就是这种观点)。但不管怎样,我必须向帮助过我的一排人深深地鞠上一躬。同时我要郑重声明:如果读者喜欢译文,那是原作和全排人员的功劳,如果什么地方让人觉得别扭、拗口乃至文理不通,责任由译者独自承担。
黄燎宇
二○○九年九月

-
做自己与别人生命中的天使
2025-10-08 08:23:25 查看详情 -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2025-10-08 08:23:25 查看详情 -
奥迪a8w12多少钱(奥迪a8w12中的w是啥意思)
2025-10-08 08:23:25 查看详情 -
计算机技术在医疗仪器中的应用
2025-10-08 08:23:25 查看详情 -
软测量技术及其在石油化工中的应用
2025-10-08 08:23:25 查看详情


 求购
求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