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宪权

制宪权
概述
宪法制定是指制宪主体依据制宪程序实现制宪权的过程,其中制宪权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所谓制宪权是一种价值体系,既包括制宪事实的力量,也包括把宪法加以正当化的权威与价值。
 制宪权、修宪权与立法权是属于不同层次的权力形态。修宪权是依据制宪权而产生的一种权力,可以理解为制度化的制宪权。当一个国家通过全民投票决定宪法修改时,这种国民投票权也是一种源于制宪权的修改宪法行为,但不可能是原始的制宪权。有时制宪权与修宪权行使的主体相同,但其行为的性质不同。而立法权活动则要遵从制宪权宗旨,不能脱离制宪的目的与原则。
制宪权、修宪权与立法权是属于不同层次的权力形态。修宪权是依据制宪权而产生的一种权力,可以理解为制度化的制宪权。当一个国家通过全民投票决定宪法修改时,这种国民投票权也是一种源于制宪权的修改宪法行为,但不可能是原始的制宪权。有时制宪权与修宪权行使的主体相同,但其行为的性质不同。而立法权活动则要遵从制宪权宗旨,不能脱离制宪的目的与原则。
制宪权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是随着近代西方立宪国家的建立而产生的一种法律现象,这种法律现象描述了一种适应社会正常发展所需要的基本宪政秩序。制宪权的确立彻底摧毁了神权、君权产生国家的神话,重塑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改变了公民对国家认识所形成的基本观念。一个基本的共识由此达成:国家权力应当由制宪权而产生,因此,它应当臣服于制宪权。
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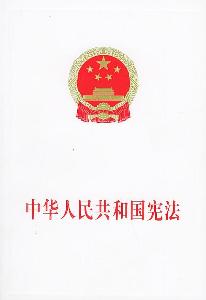 原创性。制宪权的原创性是指它是国家权力原始创立的唯一依据。国家权力在来源上决不是空穴来风,也不可能是难以捉模的神的意志,而是国家主权者──全体人民所拥有的制宪权。正如卡贝所说:“用不着说,人民就是主权者,主权属于人民的,只有人民才有权制定或者委托别人制定社会公约、宪法和各种法律;任何一个个人、一个家族或者一个阶级妄图充当人们的主人,在我们这里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制宪权的原创性具有如下法理意义:其一,制宪权是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渊源,制宪权构成了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合法性基础;不通过制宪权直接或间接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不具有要求人民服从的权威性,人民因此也就获得了否定此类宪法和法律的正当性理由,必要时可以采用适当的手段瓦解这种“宪政秩序”。其二,制宪权可以有多种实现方式,但人民所拥有的制宪权不可剥夺、也不可让渡。因为,制宪权所构成的基本要素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而这种基本权利与生俱来,不可转让。进而可知,确立制宪权的基本前提是必须无条件地承认每个公民所拥有的基本权利。没有这一前提,制宪权无疑是空中楼阁。
原创性。制宪权的原创性是指它是国家权力原始创立的唯一依据。国家权力在来源上决不是空穴来风,也不可能是难以捉模的神的意志,而是国家主权者──全体人民所拥有的制宪权。正如卡贝所说:“用不着说,人民就是主权者,主权属于人民的,只有人民才有权制定或者委托别人制定社会公约、宪法和各种法律;任何一个个人、一个家族或者一个阶级妄图充当人们的主人,在我们这里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制宪权的原创性具有如下法理意义:其一,制宪权是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渊源,制宪权构成了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合法性基础;不通过制宪权直接或间接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不具有要求人民服从的权威性,人民因此也就获得了否定此类宪法和法律的正当性理由,必要时可以采用适当的手段瓦解这种“宪政秩序”。其二,制宪权可以有多种实现方式,但人民所拥有的制宪权不可剥夺、也不可让渡。因为,制宪权所构成的基本要素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而这种基本权利与生俱来,不可转让。进而可知,确立制宪权的基本前提是必须无条件地承认每个公民所拥有的基本权利。没有这一前提,制宪权无疑是空中楼阁。
至高性。制宪权的至高性是指它高于一切由制宪权创设的国家权力,任何国家权力或者其他社会组织都必须臣服于制宪权。制宪权的至高性有助于形成一个统摄社会秩序的最高权威,从而确保社会的有序化。制宪权的至高性内蕴如下内容:其一,制宪权不基于任何法律形式而独立存在,其主体属于组成国家的全体人民。因此任何国内法或者国际法对制宪权的规定不仅是多余的,而且也是违背法理的。其二,制宪权的至高性在其逻辑体系中演绎出的结论必然是,宪政之下的政府都应当是有限的政府,即政府的各种权力都是由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划出了政府权力的有效范围,只有在这个范围内,政府权力才具有合法、有效性。“宪政的本质的确是而且必须是限政。在宪政主义看来,不论一个政府的组织形式如何,都不得存在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力。” 当然,强调制宪权下的政府是一个有限政府,并不是政府在行使权力时没有任何自由度。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制宪权之下的政府权力是一种受宪法和法律导控的权力,即允许政府权力有一定的自由裁量范围,但自由度的最低界线应当是权力足以维持社会的正当秩序。
政治性。制宪权的政治性表现为作为全体人民所拥有的权力是全体人民行使的自治权。制宪权就内容而言它具有自治权性质,表现为全体人民为实现共同达成的目标而进行自我管理的一种基本方式。制宪权的政治性可分解出如下内容:其一,政权是制宪权行使的前提条件。近现代每一个立宪国家的历史都表明,人民只有取得国家政权,才能行使制宪权。但这并不说人民在没有取得政权之前就没有制宪权,而只是没有条件行使。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制宪权的产生与形成及其运用过程中离不开国家权力活动,即国家权力是制宪权产生的前提条件,没有国家权力就谈不上有完整的制宪权,而且制宪权本身可以看作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主要的活动形式。”我认为,这种观点的缺陷可能是混淆了政权与国家权力,把因制宪权所产生的国家权力当成了制宪权产生的前提条件。其二,制宪权的政治性还表现为在人民内部,一部分人不能凭借制宪权支配另一部分人,并使之臣服。因为,在宪政主义看来,一种可以支配他人的权力,只能通过一定程序授予,任何人都不能声称自己天生拥有可支配他人的权力。制宪权不是经过一定程序被授予的,而是人民基本权利的集中体现;人民基本权利的平等性使一部分人凭借制宪权支配另一部分人失去了正当性基础。
因此,制宪权是一国的全体人民亲自或者通过一定的组织机构,根据预设的立宪程序制定宪法的权力。与制宪权有关的宪法修改权、宪法解释权和违宪监督权则通过宪法授予相关的国家机关行使。
界限
①受宪法目的的制约——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
②受法理念的制约——法的预期性、稳定性、公开性、普遍性、平等、正义等制约
③事实上受到人民认识能力局限性的制约
④受国际法的制约——主要表现在战败国的制宪权受战胜国宪法的影响或国际条约的影响。
主体
 制宪权主体是制宪权得以运行的首要因素。西哀耶士曾认为,只有国民才能构成制宪权主体。但在历史上,君主、少数者组织、一定团体等也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了制宪权主体。近代以前,由于民主政治不发达,制宪权基本上由君主掌握,君主主权成为国家活动的基本原则。1791年《法国宪法》虽规定了国民主权原则,但事实上主权由国王和国民共同行使。在从君主主权向人民主权转化过程中,只有国民中的一部分才能充当制宪权实际上的主体。国民成为制宪权主体是现代宪法发展的基本特点,这表明政治社会中国民的宪法地位。现代各国宪法中普遍规定,国民是制宪权主体。如《美国宪法》、《日本国宪法》、《联邦德国基本法》序言中明确规定,制宪权主体是国民,并规定了国民行使制宪权的方式。国民作为制宪权主体,表明制宪权来源于权力的享有主体,但它并不意味着全体国民都直接参与制宪过程,具体行使制宪权。实际参与制宪过程的只是一部分国民或者经选举产生的代表。因此,享有制宪权主体与具体行使制宪权是不同的概念。为了使国民有效地行使制宪权,各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制宪机关,并赋予制宪机关相对独立的职权。
制宪权主体是制宪权得以运行的首要因素。西哀耶士曾认为,只有国民才能构成制宪权主体。但在历史上,君主、少数者组织、一定团体等也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了制宪权主体。近代以前,由于民主政治不发达,制宪权基本上由君主掌握,君主主权成为国家活动的基本原则。1791年《法国宪法》虽规定了国民主权原则,但事实上主权由国王和国民共同行使。在从君主主权向人民主权转化过程中,只有国民中的一部分才能充当制宪权实际上的主体。国民成为制宪权主体是现代宪法发展的基本特点,这表明政治社会中国民的宪法地位。现代各国宪法中普遍规定,国民是制宪权主体。如《美国宪法》、《日本国宪法》、《联邦德国基本法》序言中明确规定,制宪权主体是国民,并规定了国民行使制宪权的方式。国民作为制宪权主体,表明制宪权来源于权力的享有主体,但它并不意味着全体国民都直接参与制宪过程,具体行使制宪权。实际参与制宪过程的只是一部分国民或者经选举产生的代表。因此,享有制宪权主体与具体行使制宪权是不同的概念。为了使国民有效地行使制宪权,各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制宪机关,并赋予制宪机关相对独立的职权。
机构
为了使制宪权的实现具体化,各国通常根据制宪的需要,成立各种形式的制宪机关,如制宪会议、国民会议、立宪会议等机关。制宪机关依据民意行使制宪权,具体负责宪法的制定。实际行使制宪权的议会或代表机关一般是由国民经过选举而产生的。制宪议会不同于一般国会或民意机关,可不受旧宪法的约束,具有政治议会的性质。如印度制宪议会根据1947年7月15日的《独立法》,自动获得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并于1947年8月组织了由7名委员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1948年完成宪法草案后,同年11月提交给宪法制定会议。经审议后,宪法制定会议于1949年11月正式通过《印度宪法》。
 制宪机关与宪法起草机构是不同的,主要区别在于:制宪机关是行使制宪权的国家机关,而宪法起草机构是具体工作机关,不能独立地行使制宪权;制宪机关一般是常设的,而宪法起草机关是临时性的机关,起草任务结束后便解散;制宪机关有权批准通过宪法,而宪法起草机关无权批准通过宪法;制宪机关由公民选举产生,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而宪法起草机关主要通过任命方式产生,注重来源的广泛性。
制宪机关与宪法起草机构是不同的,主要区别在于:制宪机关是行使制宪权的国家机关,而宪法起草机构是具体工作机关,不能独立地行使制宪权;制宪机关一般是常设的,而宪法起草机关是临时性的机关,起草任务结束后便解散;制宪机关有权批准通过宪法,而宪法起草机关无权批准通过宪法;制宪机关由公民选举产生,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而宪法起草机关主要通过任命方式产生,注重来源的广泛性。
对制宪机关的规定,各国宪法不尽相同。有的国家宪法明确规定行使制宪权的制宪机关,并赋予其独立地位。也有国家的宪法对制宪机关不作具体规定,只规定修宪权主体。如我国宪法没有具体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制宪机关,只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修改宪法。从宪政实践与宪法原理上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制宪机关的地位是十分明确的,其根据在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宪权是国家权力存在的最高体现,自然由全国人大行使;全国人大行使组织国家权力行使的职权,国家具体权力的组织以制宪权为基础;从宪政实践看,在我国,制宪权与修宪权行使主体是相统一的,第一部宪法的制定与几次修改都由全国人大通过。这就说明,尽管在我国宪法条文中,没有具体规定制宪机关,但从宪政原理与实践中我们可以认定,全国人大是我国的制宪机关。这种理解并不带来逻辑上的矛盾。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组织与活动原则应根据宪法规定,制宪本身是最高权力的体现与组成部分,故宪法上制宪机关的地位与全国人大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是相一致的、它们之间并不矛盾。

-
长城汽车正式获得泰国罗勇工厂所有权 长城炮全球版正式上市
2025-11-01 09:09:04 查看详情 -
长城汽车正式获得泰国罗勇工厂所有权 长城汽车申请注册新商标
2025-11-01 09:09:04 查看详情


 求购
求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