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黛敏郎

黛敏郎
人物简介
Toshirô Mayuzumi ( 1929-02-20 至 1997-04-10 ) 日本作曲家。1929年 2月20日生于横滨。194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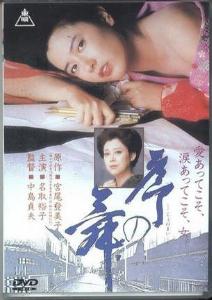 黛敏郎的作品年东京音乐学校,师从桥本国彦、池内友次郎、伊福部学作曲。1949年演出了他的毕业作品《十件乐器演奏嬉游曲》,技巧成熟,风格清新。1951年于该校研究毕业后留学法国,入巴黎音乐学院,翌年归国。在50年代, 黛敏郎积极探索新的作曲技法。
黛敏郎的作品年东京音乐学校,师从桥本国彦、池内友次郎、伊福部学作曲。1949年演出了他的毕业作品《十件乐器演奏嬉游曲》,技巧成熟,风格清新。1951年于该校研究毕业后留学法国,入巴黎音乐学院,翌年归国。在50年代, 黛敏郎积极探索新的作曲技法。
黛敏郎是前卫的,他有《X·Y·Z》,有《7的变奏》;黛敏郎是成功的,有《涅盘》,有《曼荼罗》,有《金阁寺》,《古事记》……。
他潇洒、时髦,追求新潮,他爱香车宝马(美洲虎、奔驰),慷慨大方;他又有条有理,严格认真,是“59分30秒的男人”。
他求新求变,每有创获,便引起轰动,他有着大多作品均能在日本和世界首演的幸运;而他又能坚持在电视台作音乐普及讲座节目,数十载而不辍,直至逝世。
他身前担任着日本作曲家协议会会长、日本音乐著作权协会会长,是日本音乐界的头面人物;同时他又是右倾的“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的议长,就靖国神社、二战罪行问题,他发表了很多右倾的言论。
黛敏郎就是这样一个丰富多彩、意味深长的人。所以,我给本文选用了“意味(IMI)”这样一个词,而没用意义、影响、作用之类。
黛敏郎的身后确实是意味深长的一串……。
获奖情况
1967
金球奖(Golden Globe) 最佳原创配乐(提名)圣经:创世纪(1966)
奥斯卡(美国电影学院奖) 最佳原创配乐(提名)圣经:创世纪(1966) 黛敏郎作品
黛敏郎作品
1966
Mainichi Film Concours(Mainichi Film Concours) Best Film Score东京奥林匹克(1965)
1964
Mainichi Film Concours(Mainichi Film Concours) Best Film Score日本昆虫记(1963)
Mainichi Film Concours(Mainichi Film Concours) Best Film Score不良少女(1963)
1958
Mainichi Film Concours(Mainichi Film Concours) Best Film Score気違い部落(1957)
Mainichi Film Concours(Mainichi Film Concours) Best Film Score幕末太阳传(1957)
早慧的音乐天才
黛敏郎1929年2月20日出生于横滨。家庭富裕,父亲是山下汽船会社横滨支店的店长,虽然不特别喜欢音乐,但是家中有风琴。母亲稍微会弹一点筝。黛氏很具音乐天分,也可以说在音乐方面是早慧的神童。十岁时他随镝木学了三、四年的钢琴,后进入横滨栗田谷小学校、县立第一中学校学习,加入了那里的合唱团与口琴乐队。他具有创作才能,在随中村太郎大约学习了仅仅半年的和声学与音乐理论后,不过十四岁的他,就创作了二、三十首钢琴曲、歌曲、室内乐等。
1945年,他进入了东京音乐学校(今天的东京艺大)作曲科。日本语把教课写成汉字“授业”,而把用功,学习写成汉字“勉强”。黛氏氏在大学里接受的教育还真有点类似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授业,那是因为空袭激烈无法集体上课,便依个人要求和兴趣,单独地去找业师请求授业,单练。黛氏就这样向桥本国彦学习作曲法、向池内友次郎学习和声学、对位法、向伊福部昭学管弦乐法、此外还学习了钢琴和指挥法。不过,他的学习是努力用功的,一点也不“勉强”。他的毕业作品《为10件乐器演奏的嬉游曲》获得好评。“由其神妙轻巧的感觉带出了战后派登场的印象”。在本科三年时,进入爵士乐队,弹了大约一年的爵士钢琴,这一体验在感性上给予他的音乐以重大影响。
进入研究科后,50年6月作曲的《楔型文字》入选51年ISCM现代音乐节,获得一致承认。这是富有南国基调,加入有洒脱的女声的小编成管弦乐,“确认了在日本,也越来越显示出战后派般的醒人耳目的才能” 。50年受NHK交响乐团委约作曲的《交响的气氛》也是以爪哇音乐为模型的作品。同年在每日新闻电影会演上,他的“归乡”获得电影音乐奖,以后又着手创作了很多电影音乐。
黛敏郎小荷才露尖尖角,便不同凡响,他的风格“神妙轻巧”“醒人耳目”,被评论家誉为战后新时代音乐的未来与希望。而这时他不过刚刚二十一岁。
新潮音乐的弄潮儿
51年,黛氏作为与法国政府交流的留学生进入巴黎音乐学院,大约一年后回国。关于他为什么如此短就结束了在巴黎的留学生活,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是他感到这里不是学习传统技法的地方;而另一种则认为是因为巴黎音乐学院有不太符合他气质的东西。但是对于充满了前卫精神的他,留学绝非白费。他得到了两件东西:其一是奥利维·梅西安的现代作曲技法,另一个是比埃尔·谢费尔的具体音乐。
他53年受日本文化放送委约作曲、播放的《为具体音乐而作的作品X·Y·Z》,使世人大感瞠目结舌。他就此发表了自己的主张:
“只会有这样的看法,这是一部仅仅汇集噪音而录音的东西。这一音乐,乐谱是不限定的中介物,演奏者是麻烦的存在,全是没必要的,作曲者以自己的手制造出直接的音响,具备构成的方法,它完全是另个世界的音乐。近年流行的十二音音乐,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主义主张,其结局本身还都是局限于音乐观念内部所存在的表现技法之上的问题,而具体音乐的出发点是音乐本质的变革,观念的转换,这是必须要注意到的。”
接着55年亲自着手,在NHK电子音乐制作室制作了日本最早的电子音乐《电子音乐·习作Ⅰ》,翌年与诸井诚合作了可称得上日本初期电子音乐的代表作的《7的变奏》。在器乐作品中展开了音乐集合体、音色构造的想法。在管弦乐作品《响宴》(1954)中尝试了力学的音响的流动;《EKUTOPURASUMU》(1954)中,以电子乐器,KURA小提琴、电吉他、打击乐器群、弦乐合奏变化了的构成,实验流动音乐的构造。在《音的丰满55》使用五个萨克斯管、五个小号、管乐器群与打击乐器群,以及乐锯(musical saw ),使之咆吼出混浊化音响的能量。在《6重奏曲》(1954)、为七人演奏者所作的《微观世界》(1957)等作品中,导入了十二音技法与节奏的基本音型(serie)手法等,在《为特调钢琴与弦乐四重奏而作的小品》(1957)中,则将特调钢琴作为音色构造的重要角色使用。
在这一时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积极吸收西方音乐文化,贪婪地采用所有新素材、新技法,创作上求新求变,沿着现代主义大步前进的激进尝试者,风头雄劲,名气大振,他担当了常常走在时代前头的宠儿的角色。
对此,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看法,指挥家岩城宏之说:
“承蒙黛先生,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介绍了所谓的前卫,许多作曲家当然地接受了惊人的刺激。因此可以很轻易地说,没有黛先生,就没有今天日本作曲界的隆盛。”
而作为“三人会”(芥川也寸志、黛敏郎、团伊玖磨)之一的团伊玖磨就此却有自己的看法:
“《涅盘》以前的黛氏,还没有自立。……他法国留学以来直到登场‘三人会’,比如他受比埃尔·谢费尔的音响,写作了具体音乐的试作并介绍到日本,又写作了电子音乐的模仿作品。我不认为那样的工作是作曲家的工作。那只不过是介绍介绍欧洲已有的事情。那样的介绍者的工作应当是相当文化后进国的初学者干的,将欧洲前卫音乐通过自己作品介绍到日本,可以认为是没什么意思的。即使已是战后,世道荒废,但日本并不是那样程度的音乐后进国。……我认为,作曲家要自己掘进自己的道路,应自己创造方法。……因此,最初期与次一个阶段的黛氏,由于这些变得非常有名,但没有音乐的收获。其后,黛氏作为作曲家自立的是《涅盘》。”
倜傥潇洒的明星
黛氏应该说是属于少年得志的名士那一类人物,恃才傲物,畅情适意,潇洒倜傥。在同辈音乐家作曲家中,他是属于先富起来的一个。比他稍小的后辈回忆起当年的黛氏,无不津津乐道他作曲家之外的生活风采:
岩城宏之,他可以说是黛氏的专职指挥,对黛氏充满了深情、佩服、甚或景仰。他比黛氏小三岁。他说:黛先生是真正的明星。我进入东京艺大时,黛先生已然是辉煌的星了,他时常带着夫人来学校游玩。每当此时,一声“黛先生来了”,惹得所有人都嗡得一下子,簇拥过来。女生们都去看黛氏,而男生们则去看他新婚的太太桂木洋子。而载着这位有着吉永小百合般清纯明星风采的美女的,是帅气漂亮的美洲虎跑车。
他深情地回忆拜承黛氏的室内乐曲,他才得以能够在大一、大二时就成为现代音乐的专业打击乐演奏者,在大四时成为专业指挥,在当指挥的初期,指挥的大多都是黛氏的曲子。更让他难忘的是指挥黛氏的《涅盘》首演。那是1958年“三人会”的第三回目,在《涅盘》之前,芥川也寸志和团伊玖磨都分别指挥了自己的曲子。黛氏对他说,这次自己的曲子过于庞大复杂,要由专业指挥的你来担任。当时的岩城是N响的指挥研究员,月薪五千元,税外实得四千五百,每场临时演奏会补贴三百元。此次演奏会终了,黛氏边说着谢谢边送给他了丰厚的三万元酬金。事后随便提及,黛氏说:不对,我给了你五万吧。岩城说:就是三万。黛氏说:不行,你太太该说了,那么大个曲子,才给三万元,这人,也太抠门了。翌日,黛氏就又拿了一万元送给了岩城。黛氏氏就是如此的不拘小节,潇洒脱俗。
岩城又拿武满彻与黛氏相比。他说:我感觉武满彻像个外星人,虽然对我也很亲切,工作之余也一起游玩、喝酒,大醉之后他也纵情地唱长歌(长呗)。但无论如何只能是尊敬他,除了一同工作,演奏他的曲子之外,常待之以外星人而保持怖畏感。而对黛氏除了尊敬之外,则是可以亲近,可以寄托、可以吵架的。黛氏是怀抱着母爱的人。“黛氏是可爱的人,这对于——只知道有很多右倾言论的黛氏——一些人来说,或许是难以想象的。但他又是任性肆意的、磨人的小子。”
同样是作曲家的池边晋一郎,青少年时代也极仰慕黛氏这一代作曲家。他贪婪地阅读音乐杂志,透过“TNTER VIEW”栏目,看到了两位截然相反风采的作曲家:黛氏手扶着坚固良好的跑车的发动机外罩,齐腰而立,芥川也寸志穿着木屐骑着自行车在小茶馆里约见记者。他初次见到黛氏,是1972年国际笔会世界大会在京都召开,黛氏是笔会的主持人,他的出色的主持与流利的英语,让满场哑然。
到了更为年轻一点的另一位作曲家、大提琴演奏家、黛氏的门生松下功眼里,美洲虎早已变成了“大奔”。当师生间有过一番紧张而满意的教与学的讨论过后,黛氏便说:累了吧,走,到食堂喝茶去!这样,学生食堂的黛氏班级茶话会就开张了,大家奔向学校的大商店。老板娘是黛氏学生时代的老熟人,也算是艺大的知名人物之一。黛氏快乐地与她亲热地打招呼,“随便地大聊其天的样子,完全地象征了先生洋溢着诙谐幽默的一面。对于常常是潇洒利落的先生,也不知是怎样看我们这些邋遢不整的学生的!”。除了茶会,有时课后师生也一起去上野的美术馆与博物馆,还多次一起去听音乐会,这时的学生们就有了坐坐先生那时髦漂亮的“奔驰”的机会了。
黛氏是追求时尚的,追求生活享受与质量的。而他也有着极为理性,要求严谨,做事认真的另一面。黛氏是一个多面体。他还有一个“59分30秒的男人”的绰号,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个绰号是奈良药师寺的高田好胤管长给他起的。黛敏郎是这个寺院的信徒总代表之一,去参与花会式的声明演出。大会请高田与黛敏郎讲话,时间各为一小时。高田说:我依自己的性情,有1个小时的时间,也可以讲50分钟,也可以讲1小时10分钟。而黛敏郎呢,却是边讲边看表,讲话恰好在59分30秒时结束,剩下30秒。黛敏郎显得面貌跃如,在剩下的30秒里,返回自己的席位,当他把腰放在椅子上时,正好60分。这样的完美主义者,被高田管长认为是不会享高寿的,不幸而言中。
但是无论如何,《涅盘》之前的黛敏郎还是给人一种前卫、先锋,激进、新潮的印象,尤其是他那香车宝马、美妻佳肴,一派风流才子相,更营造了他的明星气氛。这也难怪有人把他的作品“发射出那种不谐和音的惊人的风格”与他那“氢弹型的头发,穿紧蹦细筒型的裤子悠哉游哉的样子”联系起来。
黛氏的前卫精神除了他自己的因素,也与他师承有关系。
“从他进入东京音乐学校师事桥本国彦和伊福部昭两位来思考,是肯定没错的。桥本是巴黎归来的花花公子,经常身着很华丽入时的服装,作曲也是创作被称为《斑猫》的歌曲,作为日本作曲家,他是最初从勋伯格接受影响采用了清唱剧的人。伊福部昭是富有在野精神的现代主义者,是受到了以斯特拉文斯基为首,拉威尔、法利亚、萨蒂等影响的人。黛氏后来通过电影的工作也结识了早坂文雄,可以认为,从伊福部和早坂那里,受教到了要做任何人从未做过的事情的精神与为向世界进发就必须强调日本的独自性。”
成功的名作涅盘交响曲
是的,确实如此。模仿介绍并不能获得真正的自我。黛敏郎显露出要做任何人从未做过的事情的精神和才能,向世界强调了日本独自性的作品,也是使黛敏郎遂成大名的,正是作为“三人会”之第3回目于1958年4月2日首演的《涅盘交响曲》。
关于这首作品产生的契机,岩城宏之介绍了一个说法:黛氏经常是信马游缰,一次他把不需要了的太太的钢琴,悄悄地送给了武满彻,也没跟武满说。过了几年,当武满知道送东西的人是黛氏的时候,便要回赠点什么样的礼物,可是贫乏得也拿不出适当的礼物,唯一象样的就是古代声明的卷子,是第二卷,第一卷残缺。便拿着这个声明卷子送给了黛氏。看到了这个卷子,黛氏深为声明所感动,因而急速地倾向于日本音乐的方向。这是武满彻的说法。不管这种说法的准确性如何,黛敏郎确实是这样一个很豪气很肝胆的人,而他也正是自此走向了重视日本音乐,重视佛教音乐,重视东方音乐的新阶段,走向他成熟的丰收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新境界。这也算是因缘果报的一个显现吧!
这首管弦乐乐队与男声合唱表演的作品,被认为是日本作曲家创作的交响曲中最重要的作品。他灵活运用了57年从录音带分析日本梵钟而创作的《鸣钟术CAMPANOLOGY》的经验,将梵钟的音响以电子工学的分析,以管弦乐的各种乐器分担它们中所蕴含的音色,以哼吟的效果与音色的效果攫取了称之为CAMPANOLOGY EFFECT (拟音效果)的音色构造。又加上十二音技法与基本音型技法、梅西安的管弦乐法,以及使用天台声明的男声合唱,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功。甚至有评论家认为:“《涅盘交响曲》是黛敏郎的最具代表性的大作,与此同时说它是日本交响乐的代表作也不为过。在日本,年末上演《贝多芬第9》已成为惯例,堪称它的替代物的,笔者以为可以上演黛敏郎的《涅盘》。”
这是被称作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黛敏郎创作道路的一个转折点。黛敏郎完成了自己的正—反—合的过程,从此,他的创作更加勤奋,更加显现出个人的风格。黛敏郎急速地显现出尊重日本文化传统,重视传统佛教音乐声明的姿态。他为一大批采用传统的民族音乐与佛教题材的作品作曲:在“三人会”的4回目上(1960)发表的《曼荼罗交响曲》,为纽约尝城市芭蕾舞团所写的演奏会用的《舞乐》(1962),交响诗《轮回》(1962)、《咒》(1967)等的管弦乐作品为首,继之以为独唱与合唱所作的《由天台声明的始段呗·散华》(1959),康塔塔《悔过》(1963),通过文字修改文乐和三味线的为大提琴独奏所作的《文乐》(1960),还有一重要的,是1970年国立剧场委约黛氏,宫内厅式部职乐团初演的《昭和太平乐》。关于此,作曲者这样论述道:“开始从彻头彻尾的欧洲音乐改变到重新认识雅乐与印度音乐的悠久无边的伟大,与自然发生的能量。当我们接触这种音乐时,感知到与作为欧洲音乐标牌的人间性、情绪、建筑的整齐、意匠美、色彩感等等之类诸多属性无缘,或是一个可称之为另外不同宇宙、自然的茫漠的巨大音响世界的存在。由此故,雅乐所具有的今日之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黛敏郎这些成功的作品使得他成为“继松平赖则之后使日本现代音乐闻名于世界的先达”,很早就具有了世界性的影响,他有着能够在世界、日本首演他所有作品的幸运。黛敏郎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从蝤崎洋子所编的《黛敏郎作品表》来看,有管弦乐作品:28;器乐作品:19;声乐作品:24;歌剧、芭蕾作品:8;电子音乐作品(TAPE):10;剧音乐:24;电影音乐:190;其他作品:10,合计大约有三百多号。
黛敏郎对电影音乐涉猎较早,作品很多,从1950年松竹《花的容貌》到1984年东映的《序之舞》,松竹、东宝、东映、日活……,三十多年来他几乎为所有有名的电影公司都写过作品。作为可以在日本电影史上保留的作品,朝日新闻列举了《赤线地带》(沟口健二监督)、《炎上》(市川昆监督)、《幕末太阳传》(川岛雄三监督)、《NIANCHAN》(今村昌平监督)、《有化铁炉的街道》(浦山桐郎)、《黑部的太阳》(熊井启)等等。还有众所周知的外国电影美国琼·休斯顿的《天地创造》的音乐,亦出自他的手笔。
从年轻时起,为了生活动手写了为数众多的电影音乐作品,而且是一炮就红,他获得的第一个奖项,就是每日新闻的电影音乐作曲奖,而《归乡》这部电影的音乐不过是他的第二部电影音乐作品,这无疑给了当时的黛氏以很大的激励,使得他有了比较可观的收入。
而岩城宏之却以为从黛氏的电影音乐目录来看,几乎全是社会派的作品。言下之意是,黛氏在挣钱的同时,也还是关注社会关注政治的。但他的政治态度是完全右倾的。这从他和三岛由纪夫的交往,对三岛他及其作品的倾慕,以及他的歌剧《金阁寺》中会看得更清楚。
代表作金阁寺
富坚康认为:歌剧和管弦乐的作曲,是成为大作曲家的目标所在,是必须的条件,斯特拉文斯基以其《火鸟》、《彼德鲁什卡》、《春之祭》三部曲奠定了他二十世纪初叶不变的地位,由此例子看黛氏对此绝不会视而不见。是的,黛氏的作品很多,真要举出其代表作,除了管弦乐作品外,重要的就是他的歌剧。而其中最重要的是《金阁寺》。
《金阁寺》是日本著名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名篇。描写口吃的青年主人公失望之极,以烧毁金阁寺求得解脱。这种行为的意义在于:他要破坏一直束缚住他的认为只有金阁寺才是唯一的、绝对美的观念世界。这正反映了三岛本人的“心情”(这是三岛的说法,他标榜意识形态的相对性,“右,并非是思想,纯粹是属于心情的问题。”)。他坦言战败对自己来说是受到“凶狠的挫折”,战败给人们带来的,不是解放,而是回复了讨厌的日常性。正因为“没有比恶与死与血以及包含这一切的某种危险物更能吸引三岛由纪夫的心了”,所以要获救就要毁灭,要追求理想就要否定现实。
尽管我不能肯定这是否确实反映了部分战后日本人的心态,但是这种“心情”绝非象一些评论家所认为的那样:“作为对‘悲剧性事物’、‘生命的无目的的充足’的憧憬和渴望而表现出来的‘心情’的纯粹性和完美无缺性,才具备得以在文学这个场所获救的有本质意义的价值。”;《金阁寺》的故事也绝非是什么“立志要从其错误中摆脱出来的人的故事”;三岛也绝非是一个“不过问道德内容本身的是非如何,说得广一些,不过问思想内容本身如何”的“非政治性作家”。我们完全可以从他后期发表公然颂扬战前天皇体制,颂扬法西斯国家主义的小说《忧国》,以“满足空虚的自我对强力的绝对权威之美的追求”,乃至到自卫队“深入生活”,参与士兵法西斯小团体的骚乱,最后完成了他“不想作为文人,而是想作为武人死去”的愿望,剖腹自杀的事实中得到回答。
关于黛敏郎与三岛的交往,1955年6月23日,三岛由纪夫在“三人会”第2回目演出的特大型节目单上载文说“与黛氏是1952年的早春,在巴黎就相识的了。连a·be·se都不会的我,去一站地外的邮电局,还是拜托黛氏,跟着一起去的呢。回到日本后,不久就不再放在心上了。渐渐听到了他的音乐理论,与我正是论敌,不共戴天之敌。而我正是有从正当的论敌中才能看出真正的朋友的癖好。”
他们二人虽是学术论敌,却是思想之友,到了1965年柏林·德意志·歌剧院委约黛氏创作歌剧《金阁寺》而发展。黛氏本来让原作者三岛(他亦擅长此道,有剧本行世)来创作台本的邀请没能实现,就由同剧院所属的海涅布鲁克创作了德语的台本。三岛没看到它的上演,70年剖腹自杀了。
据说,世界一流歌剧院委约日本的作曲家自此始。这部歌剧1976年6月23 日首演于德国,数回成功之后;82年在SANTORII音乐财团主办的“作曲家个人展”上以音乐会形式在日本首演;在相距首演十五年之后的91年在果园会堂的舞台完全上演,用德语台本的同时,配以字幕进行。出演是岩城宏之指挥的东京爱乐乐团和东京混声合唱团。导演本来预定是柏林·德国歌剧院的艺术监督泽鲁纳,但他于一年前去世,便由其高徒巴威伦费因特执行。很碰巧的是,当这部歌剧95年10月19 日在美国纽约上演时,又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这次演出据说是有着多重意义,二战结束五十周年、金阁寺烧毁四十五周年、《金阁寺》出版四十周年、三岛去世二十五周年,但正当公演之际,指挥克里斯托弗·金却因爱滋病而猝死。
为了表现三岛由纪夫这个作品所要展示的“心情”(亦即阐释思想),这部歌剧在舞台左右的暗部配置有合唱,在剧情的衔接中间,由一边唱出登场人物的心理状态,另一边发问,使人联想到歌舞伎的净琉璃的表现形式。演沟口的男中音与其父亲的扮演者男中音是比较主要的人物,可以说是没有主要角色的一部歌剧,因此仅有女高音与男高音的配角,也没有普通歌剧中的演唱咏叹调的高潮场次。舞台则是高高地倾向于内部的黑色平面,就在那上面演出。背面全按上了镜子,可以看到舞台上所有表演的人物在镜子上晃来晃去地映动。还利用灯光布景,数次浮现出金阁寺的象征、在大火烧起来时达到了高潮。黛氏的管弦乐法是充满了以梅西安为范本的华丽的不谐和音,在调性与无调性之间往来,充分地表现这个歌剧所要突出的“最高价值”的任务。
黛氏的另一部歌剧是受奥地利林茨州立剧院创立百年纪念的委约,96年作曲的《古事记》(Tage der Gotter众神的岁月),96年5月24日在同剧院初演。这个歌剧在日本还没有上演,据在林茨观看了本剧初演的作曲家铃木行一的观感:“象前作《金阁寺》一样,表现主义的深刻音响、隐藏的影子、从何处而言都豪放地流丽、滔滔流向终幕的大海、可感到就象从其源流到河口一条粗壮的潮流。”无论如何从其所选材的内容来看,这也是一部表现日本独有民族精神的作品,这于黛氏晚年的思想路数是吻合的。
黛氏对三岛由纪夫的认同是深刻而自然的。这不仅仅只是两人右倾思想的媾和,而且还是在此种思想背景下艺术、美学主张与实践的契合。93年7月初演的《M》,是黛氏以邦乐器为主的的原创雅乐。题名的《M》是选取了〈Mishima〉(三岛由纪夫)、〈Mort〉(死)、〈Mer〉(海)、〈Metamorphose〉(变容)四个词打头的M。由此可见此中三昧。
三岛、黛敏郎,确实是成功的,有个性的,有创见的艺术家,但我们在欣赏他们的艺术时所不能忘怀的,是其中的三岛式的“心情”,无论这种心情与其艺术水平的比例如何,无论这种心情在作品中是多么的隐晦。当然,我绝没有要给黛氏作阶级分析的打算,更不会给他按上一个定性的帽子。我只是觉得我们在认识一个多色彩的立体的黛敏郎时,不要忘记他的这一个侧面。更不要忘记在日本思想界、文化艺术界,一如在日本政界一样,右翼势力有着不可低估的市场。文部省的篡改教科书,阁僚崇拜靖国神社,大臣的大放厥词,皆此类也



 求购
求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