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叠题乌江亭

叠题乌江亭
作品原文
叠题乌江亭①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②,肯为君王卷土来③?
这首诗开篇以史实扣题,指出项羽的失败实在是历史的必然。项羽的霸业以“鸿门宴”为转折,此后逐渐从顶峰走向下坡,到了“垓(gāi)下一战”,已经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彻底失败的命运已经无可挽回了。项羽失败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就是他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倒行逆施,表尽人心。更为可悲的是,他毫无自知之明,至死不悟,“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他临死前的这番话,可为“壮士衰”作注脚,也可为“势难回”作证明。所以,三、四句诗人进一步深入剖析:“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以辛辣的反问指出:即使项羽真的能重返江东,但对这么一个失尽人心而执迷不悟的人,江东子弟还肯为他拼死卖力吗?“卷土重来”实在是痴人说梦而已。
王安石的诗,十分辛辣冷峻,但却抓住了人心向背是胜败的关键这个根本,可以说是一针见血。[2]
译文:经过战争的的疲劳的壮士非常的悲哀,中原一败之后大势难以挽回。即便江东的子弟现在还在,但是,谁能保证他们为了项羽而卷土重来?
疑难点注释:①乌江亭:故址在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为项羽兵败自刎之处。
②江东:指长江下游芜湖、南京以下的江南地区,是项羽起兵之地。
③肯:岂肯,怎愿。
赏析点拨:这是针对杜牧的诗写的一首诗,表现了王安石对项羽失败的看法。杜牧在他的《题乌江亭》中写到:“ 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意思是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如果项羽能够再回江东重振旗鼓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卷土重来。而王安石则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项羽的失败已成定局,即便是江东子弟还在,项羽也不可能再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以为他们不一定再肯为战争卖命了。
创作背景
王安石于神宗熙宁二年(1069)。被任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他积极推行变法。由于保守派固执反对,新政推行迭遭阻碍。熙宁七年辞退;次年再相,九年再辞,退居江宁(现在江苏省南京市)。《叠题乌江亭》就写于这个时期。(朱成广,庞云龙 .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 语文 高中课程新学案 必修4 选修· :明天出版社 ,2008.8 :第151页 .) 西楚霸王项羽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悲情英雄,关于他的传说一直在民间流传,这其中又以他乌江自刎最为慷慨悲壮,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反复咏叹的历史题材。杜牧的《题乌江亭》说:“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杜牧在其诗中批评了项羽胸襟不够宽广,认为项羽如果能够重振旗鼓依然能够卷土重来。一代英雄的末路引起两代人的争论:项羽能够重回江东,是否还能卷土重来?王安石不同意杜牧的看法,认为即使江东父老仍在,项羽注定是失败的结局。(中华活页文选·高一版 2014年10期)
原文鉴赏
诗词赏析
杜牧在他的《题乌江亭》中写到:“ 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意思是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如果项羽能够再回江东重振旗鼓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卷土重来。而王安石则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项羽的失败已成定局,即便是江东子弟还在,项羽也不可能再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以为他们不一定再肯为战争卖命了。
诗歌开篇就以史实扣题,针对项羽的失败直接指出“势难回”。楚霸王的转折点在“鸿门宴”,没能杀成刘邦,到“垓下之围”时已经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境地。而细数项羽失败的原因,最大的因素恐怕就是他自身的刚愎自用了吧。所以文章“壮士哀”就隐含着这样的信息,那时的项羽已经失去人心,天时、地利、人和中,人和是最重要的因素,而项羽已经失去,要挽回大业是十分艰难,概率也是很低的。
所以,王安石在三、四两句中进一步阐释“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他以辛辣的口吻明确地表示,即使项羽真的重返江东,江东子弟是不会替他卖力的。杜、王的观点不同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同。杜牧着眼于宣扬不怕失败的精神,是借题发挥,是诗人咏史;王安石则审时度势,指出项羽败局已定,势难挽回,反驳了杜牧的论点,是政治家的咏史。这首诗表现了王安石作为政治家的冷峻与沉静。诗中最后的反问道出了历史的残酷与人心向背的变幻莫测,也体现出王安石独到的政治眼光。如果说杜牧是为项羽翻案,那么王安石则是为历史本身翻案,人与历史的关系本来就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从这首诗中,我们还能看出,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将变法中的革新精神带到咏史诗的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对前人提出质疑,这也是一种创新。这种史论史评是王安石完成咏史诗从叙事体向抒情体,最终走向议论体的转变,对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王安石则属意史论史评,延伸了咏史诗的内容深度,有着独到的政治见解。(葛全德 .百家专题突破:高考古代诗歌阅读鉴赏训练一百篇 :百家出版社 ,2008.8 :第113页 .)
名家点评
北宋·魏泰《东轩笔录》评曰:“王荆公初为参政,闲日阅晏元献小词而笑日:‘宰相为此可可乎?’”(李诚主编;孟德著 .宋词小百科 :巴蜀书社 ,2013.06 :第32页 .)
清·袁枚《随园诗话》评曰:“文忌平衍,而公天性拗执,故琢句选词,迥不犹人。诗贵温柔,而公性情刻酷。故凿险缒幽。自堕魔障。”(江天主 .中国才子文化集成 第4卷 小品、民歌、元曲 :新世界出版社 ,1998.09 :第302页 .)
相关信息
题乌江亭
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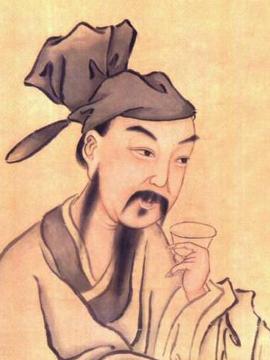 杜牧 此诗与前选《赤壁》诗一样,议论战争成败之理,提出自己对历史上已有结局的战争的假设性推想。首句言胜败乃兵家常事。次句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缺乏大将气度。三四句设想项羽假如回江东重整旗鼓,说不定就可以卷土重来。这句有对项羽负气自刎的惋惜,但主要的意思却是批评他不善于把握机遇,不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不善于得人、用人。司马迁曾以史家眼光批评项羽"天亡我,非战之罪"的执迷不悟。杜牧则以兵家的眼光论成败由人之理。二人都注重人事,但司马迁是总结已然之教训,强调其必败之原因;杜牧则是假想未然之机会,强调兵家须有远见卓识和不屈不挠的意志。
杜牧 此诗与前选《赤壁》诗一样,议论战争成败之理,提出自己对历史上已有结局的战争的假设性推想。首句言胜败乃兵家常事。次句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缺乏大将气度。三四句设想项羽假如回江东重整旗鼓,说不定就可以卷土重来。这句有对项羽负气自刎的惋惜,但主要的意思却是批评他不善于把握机遇,不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不善于得人、用人。司马迁曾以史家眼光批评项羽"天亡我,非战之罪"的执迷不悟。杜牧则以兵家的眼光论成败由人之理。二人都注重人事,但司马迁是总结已然之教训,强调其必败之原因;杜牧则是假想未然之机会,强调兵家须有远见卓识和不屈不挠的意志。
首句直截了当地指出胜败乃兵家之常这一普通常识,并暗示关键在于如何对待的问题,为以下作好铺垫。“事不期”,是说胜败的事,不能预料。
次句强调指出只有“包羞忍耻”,才是“男儿”。项羽遭到挫折便灰心丧气,含羞自刎,怎么算得上真下的“男儿”呢?“男儿”二字,令人联想到自诩为力超过山河,气可盖世的西楚霸王,直到临死,还未找到自己失败的原因,只是归咎于“时不利”而羞愤自杀,有愧于他的“英雄”称号。
第三句“江东子弟多才俊”,是对亭长建议“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的艺术概括。人们历来欣赏项羽“无面见江东父兄”一语,认为表现了他的气节。其实这恰好反映了他的刚愎自用,听不进亭长忠言。他错过了韩信,气死了范增,确是愚蠢得可笑。然而在这最后关头,如果他能面对现实,“包羞忍耻”,采纳忠言,重返江东,再整旗鼓,则胜负之数,或未易量。这就又落脚到了末句。
“卷土重来未可知”,是全诗最得力的句子,其意盖谓如能做到这样,还是大有可为的;可惜的是项羽却不肯放下架子而自刎了。这样就为上面一、二两句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而这样急转直下,一气呵成,令人想见“江东子弟”“卷土重来”的情状,是颇有气势的。同时,在惋惜、批判、讽刺之余,又表明了“败不馁”的道理,也是颇有积极意义的。
议论不落传统说法的窠臼,是杜牧咏史诗的特色。诸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题商山四皓庙》),都是反说其事,笔调都与这首类似。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谓这首诗“好异而畔于理……项氏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清人吴景旭在《历代诗话》中则反驳胡仔,说杜牧正是“用翻案法,跌入一层,正意益醒”。其实从历史观点来看,胡氏的指责不为无由。吴景旭为杜牧辩护,主要因这首诗借题发挥,宣扬百折不挠的精神,是可取的。 (陶道恕)
译文:
战争的胜败是很难预料的,
能够经受失败、挫折等羞辱的考验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江东的子弟中藏龙卧虎人才济济,
如果当年重返江东再整旗鼓,有朝一日卷土重来也是说不定的。
王安石
字介甫,号半山,北宋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1021-1086)。庆历二年(1042),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提点江东刑狱等职,政绩显著。嘉□五年(1060),呈《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视时势之可否,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临川集》卷三十九)的变法纲领。熙宁二年(11069),任参知政事,以“变风俗,立法度”为当务之急,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实行变法。因守旧派的反对,熙宁七年王安石辞职。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封荆国公,世称“荆公”。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许多学者闻其名而从学,著名弟子有陆佃、蔡卜、龚原等。
所创学派称“荆公新学”。执政期间,设置经义局。他与子王□及吕惠卿等重新注释《诗经》、《尚书》、《周礼》。各书不用先儒传注,多以己意解经,时称《三经新义》,颁之学官。黜《春秋》之书,戏为“断烂朝报”,不使列入学官。他博通经史,治学主张“以经世务”。哲学上,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认为“道”就是天,是宇宙的本原,是生成万物之母。“道”的质体是物质性的“元气”。“元气”分化为阴、阳二气,“阳极上、阴极下”。阴阳交合之气为“冲气”。冲气流转运行生“五行”。“天(阳)一生水”,“地(阴)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原性》)。由这五种物质元素形成万事万物,所谓“五行,天所以命万物者也”(《洪范传》)。万物生成后,在一定时间和条件下还会消亡,归复于“元气”,此谓“归根复命”。而道、五行、万物所变化,“新故相除”的原因,是皆有“耦”(事物内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柔一刚,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恶,有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音皆在是矣。而且耦中又有耦,使万物变化无穷。对立双方又互相依存,善者恶之对,有善就必有恶,轻者必然以重为依,躁者必以静为主。
对人性问题,他认为性生于诚,诚则生于心,心生于气,而气生于形。人性是人形体的属性,人体形成时就天然存在。它不具有道德品性,但性是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太极。性与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喜怒哀乐好恶等欲,未发于外而存于心,谓性;喜怒哀乐好恶等欲,发于外而见于形,则谓情。性是情之本,情是性之用。情可以为善,也可以为不善。善与不善,取决于后天的习染。“上智下愚”是后天修养的结果。他把“新故相除”的思想推广到社会政治生活,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提出挑战。强调“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主张革新变法。认为祖宗之法,“不必尽善”,可改者则改,不足循守。夏之法至商而更改,商之法至周也有更改,皆是因世就民而有改动,无世代相承的法。故君子为政,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执行天下之法者乃官吏,吏不良,则有法莫守。方今之急,在乎人才而已。为培养人才,他提出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措施。
强调贤者治不肖,贵者治贱,是古之道。臣是顺承者,应绝对服从君主,仆是卑顺者,要绝对服从主人。还提倡加强教化,认为仁义礼智信,是天下之达道,君主以仁义礼智信修其身而移其政,则天下莫不化。故善为教化者,致吾义忠,则天下君臣义忠;致吾孝慈,则天下父子也慈孝;致吾恩于兄弟;而天下之兄弟也皆相思;致吾礼于夫妇,而天下之夫妇也皆相为礼。他还反对以富侵贫,主张用政令均有无,使富者不能侵贫,强不得凌弱,“损有余以补不足”。对生财和理财,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理财应去掉重敛,而宽农民,国用可足,而又民财不匮。理财不可以不义,应以义理天下之财。王安石的宇宙生成说,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新故相除”的观点,把我国古代的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撰《三经新义》,黜《春秋》之书,戏为“断烂朝报”之举,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使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主要著作有《易义》、《诗经新义》、《论语解》、《孟子解》等,多已散佚。《临川集》一百卷。[4]

-
二叠纪-三叠纪灭绝事件
2025-09-23 04:51:38 查看详情 -
世界竞技叠杯运动协会
2025-09-23 04:51:38 查看详情


 求购
求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