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安卧雪图

袁安卧雪图
袁安其人
袁安(?-公元92年),中国东汉大臣。字邵公。汝南 汝阳(今 河南商水西南)人。他是 袁绍的 高祖父。少承家学。 举孝廉,任阴平长、任城令 ,驭属下极严,吏人 畏而爱之。明帝时,任楚郡太守、 河南尹 , 政号 严明,断狱公平,在职10年,京师肃然,名重朝廷。后历任 太仆、司空、司徒。和帝时, 窦太后临朝,外戚 窦宪兄弟专权操纵朝政, 民怨沸腾。袁安不畏权贵, 守正不移,多次直言上书,弹劾窦氏种种不法行为,为窦太后忌恨。但袁安节行素高,窦太后无法加害于他。在是否出击北匈奴的辩论中,袁安与司空 任隗力主怀柔,反对劳师远涉、 徼功万里,免冠上朝力争达10余次。其后代多任大官僚, 汝南袁氏成为东汉有名的世家大族。
明帝时,任楚郡太守、河南尹,以公正严明著称。后历任太仆、司空、司徒。和帝即位,外戚窦宪兄弟专权,他不避权贵,曾多次弹劾窦氏的专横。其子孙世代任大官僚,“汝南袁氏”成为东汉有名的世家大族。袁安的发迹,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任何背景的凭恃,完全是靠他自己苦苦努力出来的,给后世的国人塑立了一个自力更生、奋斗成功的最佳典范。
卧雪典故
【袁安困雪】《后汉书•袁安传》 李贤注引晋 周斐《汝南先贤传》:“时大雪积地丈余,洛阳令身出案行,见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门,无有行路。谓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户,见安僵卧。问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饿,不宜干人。’令以为贤,举为孝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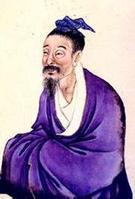 《后汉书•袁安传》李贤注引晋周斐《汝南先贤传》载,有一年冬天, 纷纷扬扬的大雪一连下了十 余天,地上积雪有一丈多厚,封路堵门。洛阳令到州里巡视灾情, 访贫问苦, 雪中送炭。见家家户户都 扫雪开路,出门谋食。来到袁安家门口,大雪封门,无路可通,洛阳令以为袁安已经冻馁而死,便命人凿冰除雪, 破门而入,但见袁安偃卧在床,奄奄一息。洛阳令扶起袁安,问他为什么不出门乞食,袁安答道:“大雪天人人皆又饿又冻,我不应该再去干扰别人!”洛阳令嘉许他的品德,举他为孝廉。并又在 汉章帝的建初年间出任河南尹,在职十年,政尚慈爱,被朝廷誉为"孙宝行 秋霜之诛,袁安留冬日之爱",并且自此 扶摇直上,成为了汉室的社稷之臣。 谢安以一扇赠行, 袁宏曰:“辄当 奉扬仁风,慰彼 黎庶”,古有“卧雪情操,扬风惠政”之赞。宋代的 袁粲为刘僧敬所害,其子以身卫父,粲以“我不失为忠臣,汝不失为孝子”赞之,称谓“ 忠臣孝子”。
《后汉书•袁安传》李贤注引晋周斐《汝南先贤传》载,有一年冬天, 纷纷扬扬的大雪一连下了十 余天,地上积雪有一丈多厚,封路堵门。洛阳令到州里巡视灾情, 访贫问苦, 雪中送炭。见家家户户都 扫雪开路,出门谋食。来到袁安家门口,大雪封门,无路可通,洛阳令以为袁安已经冻馁而死,便命人凿冰除雪, 破门而入,但见袁安偃卧在床,奄奄一息。洛阳令扶起袁安,问他为什么不出门乞食,袁安答道:“大雪天人人皆又饿又冻,我不应该再去干扰别人!”洛阳令嘉许他的品德,举他为孝廉。并又在 汉章帝的建初年间出任河南尹,在职十年,政尚慈爱,被朝廷誉为"孙宝行 秋霜之诛,袁安留冬日之爱",并且自此 扶摇直上,成为了汉室的社稷之臣。 谢安以一扇赠行, 袁宏曰:“辄当 奉扬仁风,慰彼 黎庶”,古有“卧雪情操,扬风惠政”之赞。宋代的 袁粲为刘僧敬所害,其子以身卫父,粲以“我不失为忠臣,汝不失为孝子”赞之,称谓“ 忠臣孝子”。
指 高士生活清贫但有操守。晋 陶潜《咏贫士七首》之五:“袁安困积雪,貌然不可干。
绘典名画
袁安卧雪的故事,在古代极有影响,成为传统文学和绘画广为引用的典故和题材。
历史上许多著名画家如 王维、 董源、 李升、 黄筌、 范宽、 李公麟、 李唐、 周昉、 马和之、 郑思肖、 颜辉、 赵孟頫、 王恽、 沈梦麟、 倪瓒、 沈周、 盛懋、 陶宗仪、 祝允明、 文徵明、 文嘉、谢时辰、等都画过 《袁安卧雪图》,而且尚有一 些不知作者姓名的《袁安卧雪图》,与 沈括差不多同时期的 郭若虚在《 图画见闻志》卷六就记载一帧佚名《袁安卧雪图》:“丁晋公典金陵,陛辞之日,真宗出八幅《袁安卧雪图》一面。其所画人物、 车马、林石、 庐舍,靡不臻极,作从者苦寒之态,意思如生。旁题云:“臣 黄居寀等定到 神品上”但不 书画人姓名,亦莫识其谁笔也。上宣谕晋公曰:“卿到金陵日,可选一 绝景处张此图。”晋公至金陵,乃于城之西北隅构亭,曰“赏心”,危耸清旷,势出尘表。遂施图于巨屏,到者莫不以为 佳观。岁月既久,缣素不无败裂,由是往往为人刲窃。后 王君玉 密学 出典是邦,素闻此图甚奇,下车之后,首欲纵观,乃见窃以殆尽。 嗟惋久之,乃诗于壁,其警句云:“昔人已化嘹天鹤,往事难寻 《卧雪图》。”
些不知作者姓名的《袁安卧雪图》,与 沈括差不多同时期的 郭若虚在《 图画见闻志》卷六就记载一帧佚名《袁安卧雪图》:“丁晋公典金陵,陛辞之日,真宗出八幅《袁安卧雪图》一面。其所画人物、 车马、林石、 庐舍,靡不臻极,作从者苦寒之态,意思如生。旁题云:“臣 黄居寀等定到 神品上”但不 书画人姓名,亦莫识其谁笔也。上宣谕晋公曰:“卿到金陵日,可选一 绝景处张此图。”晋公至金陵,乃于城之西北隅构亭,曰“赏心”,危耸清旷,势出尘表。遂施图于巨屏,到者莫不以为 佳观。岁月既久,缣素不无败裂,由是往往为人刲窃。后 王君玉 密学 出典是邦,素闻此图甚奇,下车之后,首欲纵观,乃见窃以殆尽。 嗟惋久之,乃诗于壁,其警句云:“昔人已化嘹天鹤,往事难寻 《卧雪图》。”
现代,以此典故为题材的名画也比比皆是: 傅抱石、 刘峨士、 胡世华、 冯超然,等等。
诗佛雪蕉
王维曾有一帧极负盛名的画叫作 《袁安卧雪图》,北宋沈括《 梦溪笔谈》卷十七曰:“ 书画之妙,当以 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观画者,多能 指摘其间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如彦远《画评》言:“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余家所藏 摩诘《袁安卧雪图》有 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 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论也。
王摩诘画了一幅《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给后人留下了多少 谈资和 蠡测,实在也是物有所值了,虽然这幅超乎想像的画似乎没有谁见到过,就是挑起此事的沈括也没有把那幅画拿给别人看过,只说是“予家所藏”。后人再论此画,也只有把沈括的话原封搬来,以验明此身,非是 子虚乌有。 “雪中芭蕉”成了绘画、艺术史上的千古绝唱。没有人能超越它的境界,也少有人敢于蔑视它的境界。 
“没有那一种艺术比绘画这门艺术引起更多的理想和自然的争论。”(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千百年来,由于该画的“雪蕉”问题,使其成为我国绘画史上最大的一桩艺术公案,人们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再加上“诗画本一律”的传统,以致传统 文学批评对此也成了热门话题。历来大体形成如下几种观点:
一、神理说:沈括即此观点。宋释 惠洪《 冷斋夜话》卷四曰:“王维作画 《雪中芭蕉》, 法眼观之,知其神情寄寓于物,俗论则讥以为不知寒暑。”宋 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宋陈善(《 扪虱新话》下集卷四)、宋 楼钥( 《攻愧集》卷二)、明 沈周(《 石田诗选》卷九)、明 王骥德( 《曲律》卷三)、清 毛先舒(《诗辩坻》卷三)、清 王士祯( 《池北偶谈》卷十八)、 潘天寿(《 中国绘画史》第三编第一章)、葛兆先(《禅宗与 中国文化》第190页)等均同此观点。
二、写实说:宋 朱翌《 猗觉寮杂记》卷上曰:“《 笔谈》云:‘王维画入神,不拘四时,如《雪中芭蕉》。’故惠洪云:‘雪里 芭蕉失寒暑’皆以芭蕉非雪中物。岭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如, 红蕉方开花。知前辈虽画史亦不苟。洪作诗时,未到岭外,存中亦未知也。”同此观点的有宋 晁冲之( 朱弁《 风月堂诗话》卷下)、明 王肯堂(《郁冈斋笔尘》卷二)、明 俞弁(《逸老堂 诗话》卷上)、清 尤侗《艮斋杂说》、清 俞正燮( 《癸巳存稿》)、清 邵梅臣( 《画耕偶录》)、 刘启林(《梦溪笔谈艺文部校注》)等。
三、事谬说:宋朱熹《 朱子语类》卷一三八曰:“雪里芭蕉,他是会画雪,只是雪中无芭蕉,他自不合画了芭蕉。人却道他会画芭蕉,不知他是误画了芭蕉。”明 谢肇淛《 文海披沙》卷三亦认为:“作画如作诗文,少不检点,便有 纰缪。如王维《雪中芭蕉》,虽闽广有之,然 右丞关中极寒之地,岂容有此耶……皆为识者所指摘,终为 白璧之瑕。” 钱钟书则称谢论“最为 持平之论”(《 谈艺录•附说二十四》), 康有为(《 万木草堂论画》)、 童书业(《唐宋绘画谈丛》第35页)、 俞剑华(《 中国画论类编》第44页)等对《雪中芭蕉》略有 微辞。
四、佛理说:清 金农《杂画题记》曰:“王右丞《雪中芭蕉》为画苑奇构。芭蕉乃 商飙速朽之物,岂能 凌冬不凋乎?右丞深于禅理,故有是画,以喻沙门不坏之身,四时保其坚固也。”钱钟书认为:“假如雪里芭蕉含蕴什么‘禅理’,那无非象海底尘、腊月或 火中莲等等,暗示‘稀有’或‘不可思议’。”(《中国诗与中国画》, 《七缀集》)。 葛晓音认为是“表现一种佛教的寓意……赞美他( 袁安) 安贫乐道的志趣”(《汉唐文学的嬗变》第290页至291页)。 张育英认为:随意“不问四季”正是禅宗 心性论的表现(《禅与艺术》第四章)。 陈允吉认为:“雪中芭蕉”是“寄托着‘人身空虚’的佛教神学思想”(《王维“雪中芭蕉”寓意蠡测》)。 黄河涛认为:“雪中芭蕉”是寓意着对禅宗的热情,表现了对 适意人生追求的执着,甚至还认为“王维以袁安舍己的典故”是对此寓意的“进一步烘托”( 《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第98页)。
五、象征说:刘大杰《 中国文学发展史》第十四章认为:“〔王维〕有《雪中芭蕉》一帧,极负盛名,这证明他的艺术是着重于意境的象征,而不着重于饰绘。” 朱自清《论逼真与如画》( 《论雅俗共赏》)一文也认为是象征。不过都未明确指出具体象征何事何物。后 程千帆(《俭腹抄》第220页)、郁沅(《古今文论探索》第119页)等都认为是象征袁安的 高洁。
中国文学发展史》第十四章认为:“〔王维〕有《雪中芭蕉》一帧,极负盛名,这证明他的艺术是着重于意境的象征,而不着重于饰绘。” 朱自清《论逼真与如画》( 《论雅俗共赏》)一文也认为是象征。不过都未明确指出具体象征何事何物。后 程千帆(《俭腹抄》第220页)、郁沅(《古今文论探索》第119页)等都认为是象征袁安的 高洁。
另外因“雪蕉”的冷热不调之故,历来人们亦喜拿此话题戏以为谑,诸如:“雪里芭蕉 摩诘画,炎天梅蕊简斋诗。”( 陈与义《题赵少尹青白堂三首》其三)、“客来问讯名堂意,雪里芭蕉笑杀侬。”( 杨万里《寄题张商弼葵堂,堂下元不种葵花,但取面势向阳二首》其一)、“檐牙窗额两三株,只欠王维画雪图。”(杨万里 《芭蕉》之三)、“清过炎天梅蕊,淡欺雪里芭蕉。”( 张炎《 风入松•溪山堂竹》词)、“ 杜门我自无干请, 闲写芭蕉入画中。”( 倪瓒《题孙氏雪林小隐》)、“雪中蕉正绿,火中莲亦长。”( 李流芳《和朱修能雪蕉诗》)等等。
遗憾的是,此画早已失传,除沈括外,历史上再未有任何人提及见过此画。历史留给此画仅有“雪中芭蕉”四字而已。



 求购
求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