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弥留之际

我弥留之际
内容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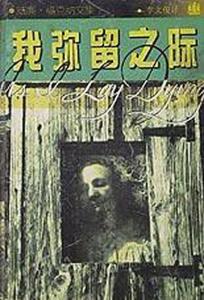 其他版本的《我弥留之际》(5)
其他版本的《我弥留之际》(5)
小说以一个女人—艾迪·本德伦为轴心。艾迪是小学教员出身的农妇,经过几十年生活的煎熬,终将撒手归西,小说便以此开篇。艾迪是本德伦家5个孩子的母亲,她要求丈夫安斯在她死后将她的尸体运到杰弗生与娘家人葬在一起。但是,仿佛老天有意捉弄,艾迪死时恰逢大雨倾盆,次子达尔与另一个儿子朱维尔(艾迪与一牧师的私生子)驾驶着全家唯一的运输工具——一辆破旧的马车离家挣钱在外。3天后,被大雨耽搁后终于归来的马车载着艾迪的尸体踏上了通往40英里外的杰弗生。但是,能去杰弗生的所有桥梁都己经被大水冲走,本德伦一家只好冒着危险涉水而过。结果,长子卡什为保护母亲的遗体而被压断了一条大腿,家里唯有的两头骡子溺死在水中。为使旅途继续进行,只好抵押了全家的耕作机、播种机,搭上卡什攒下用于买电唱机的8美元,并换掉了朱维尔利用夜间辛苦做工换来的视若生命一般宝贵的马,买了一对新的拉车骡子。炎热的夏天,在路上奔波了几天的尸体的臭味不仅招来一群群的秃鹜,而且,所经之处,行人侧目,乡邻咒骂,连警察也不得不出面干预。达尔,这个渴望母爱却一直被拒之门外的儿子,企图放火烧掉棺材,以结束这次荒诞的旅程,但目的没有达到,却烧掉了停放尸体的别人的仓房。历尽千辛万苦,经过“水”与“火”的灾难,本德伦一家终于埋葬了艾迪。之后,在朱维尔和杜威·德尔(本德伦家的女儿)的协助下,两个带枪的人将达尔抓了起来,送入了精神病院。而安斯则迅速地配上了假牙,找到了新欢—一个“鸭子模样”的女人。
作品目录
| 达尔 | 皮保迪 | 达尔 | 塔尔 | 惠特菲尔德 | 瓦达曼 |
| 科拉 | 达尔 | 卡什 | 达尔 | 达尔 | 达尔 |
| 达尔 | 瓦达曼 | 达尔 | 塔尔 | 阿姆斯蒂 | 卡什 |
| 朱厄乐 | 杜威·德乐 | 瓦达曼 | 达尔 | 瓦达曼 | 皮迪保 |
| 达尔 | 瓦达曼 | 达尔 | 瓦达曼 | 莫斯利 | 麦高恩 |
| 科拉 | 塔尔 | 安斯 | 塔尔 | 达尔 | 瓦达曼 |
| 杜威·德乐 | 达尔 | 达尔 | 达尔 | 瓦达曼 | 达尔 |
| 塔尔 | 卡什 | 安斯 | 卡什 | 达尔 | 杜威·德乐 |
| 安斯 | 瓦达曼 | 萨姆森 | 科拉 | 瓦达曼 | 卡什 |
| 达尔 | 塔尔 | 杜威·德乐 | 艾迪 | 达尔 |
创作背景
| 达尔 | 皮保迪 | 达尔 | 塔尔 | 惠特菲尔德 | 瓦达曼 |
| 科拉 | 达尔 | 卡什 | 达尔 | 达尔 | 达尔 |
| 达尔 | 瓦达曼 | 达尔 | 塔尔 | 阿姆斯蒂 | 卡什 |
| 朱厄乐 | 杜威·德乐 | 瓦达曼 | 达尔 | 瓦达曼 | 皮迪保 |
| 达尔 | 瓦达曼 | 达尔 | 瓦达曼 | 莫斯利 | 麦高恩 |
| 科拉 | 塔尔 | 安斯 | 塔尔 | 达尔 | 瓦达曼 |
| 杜威·德乐 | 达尔 | 达尔 | 达尔 | 瓦达曼 | 达尔 |
| 塔尔 | 卡什 | 安斯 | 卡什 | 达尔 | 杜威·德乐 |
| 安斯 | 瓦达曼 | 萨姆森 | 科拉 | 瓦达曼 | 卡什 |
| 达尔 | 塔尔 | 杜威·德乐 | 艾迪 | 达尔 |
人物介绍
福克纳是在1929年10月25日(星期五)开始写《我弥留之际》的,当时他正在密西西比大学发电厂里监督那些上夜班的工人。当时,福克纳正处于经济危机和艺术枯竭的时候,而美国的灾难(1929年的大萧条)使他的处境更为恶化。有关“繁荣的20年代”的故事开始从报纸中消失,接下来的“30年代”或“大萧条时期”已经开始。然而,他周围的许多人都不相信他能成为一个职业作家,因为他以前作品的销售情况很让人失望。在福克纳从老一辈作家比如约瑟夫·康拉德等那里借鉴了一些写作风格。另一个有影响力的作家是舍伍德·安德森,其小说《小镇畸人》中的故事为描写《我弥留之际》中本德伦一家(the Bundrens)的环境提供了额外的灵感:福克纳赋予这个家庭以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色彩。同样,詹姆斯·乔伊斯在他史诗般的《尤利西斯》中的内心独白也被福克纳用在他的小说中。影响稍少的要数T·S·艾略特的那些描写孤立之人的诗歌,尤其是《空心人》和《荒原》了。
从字面上说,《我弥留之际》讲的是小说中本德伦一家的女主人艾迪临死以及死后发生在这一家人身上的故事;但从比喻意义上说,《我弥留之际》之中的“我”可以暗指刚刚过去的“繁荣的20年代”,它虽已成过去,但是其影响还深深地留在美国人们的脑海里,20年代还在“弥留”着。毋庸置疑,福克纳在小说中触及到了存在于当时美国社会中的许多社会现实问题。鉴于该小说的重要性以及它创作和发表的时间来说,可以说,《我弥留之际》是20年代创作的最后一本重要的美国小说,也是在30年代发表的第一本重要的美国小说。
在20年代,美国南方地区仍然在努力从1860年代的内战以及战后北方对南方的经济殖民中恢复过来。南方的农民已经处于长期的萧条时期了。在30年代,各种各样的合作行为几乎在整个美国都得到了鼓励。全国范围内,“集体主义”成了一种口号。在南方,平民党党员(Populist)和各种激进运动人士都在为提高弱势群体,尤其是贫穷白人农民们的经济和政治条件而斗争,即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去反对富有的种植园主和银行联盟者。虽然当时平民党主义(populism)的影响在不断扩大,但对南方而言,“集体主义”的故事却有着特别保守的涵义。从传统意义上说,南方的集体主义理想意味着一种对长期存在的集体关系和风俗的尊重。它意味着要讲究礼节形式。福克纳把南方这种集体主义理想写进了小说中。
1930年1月12日,福克纳打完了《我弥留之际》,之后他便筹划投稿给一些有知名度的杂志,这些筹划中的小说有30篇于将来的3年中发表。这时他的短篇小说稿酬已超过过去写四部长篇的酬劳。4月30日,短篇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发表于《论坛》杂志,同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还有《荣誉》、《节俭》和《殉葬》。10月6日,《我弥留之际》在纽约由凯普与史密斯公司出版。12月,同一公司出版了修订版的《圣殿》。同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克莱·刘易斯在其演说中提到了福克纳,称他“把南方从多愁善感的女人的眼泪中解放了出来”。
安斯
卡什
安斯可以说是整个南方穷苦农民的代表,他身上体现了农民的典型品质。尽管众多评论家认为“他集懒惰、自私、虚伪、甚至冷酷于一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但从实际上看,这种评价过于主观,忽略了生存环境对他的影响和他身上的其他特质。作为一家之主,他曾辛苦劳作,以至于“脚八字的厉害,”“脚趾痉挛、扭歪、变形,两只小脚趾根本长不出指甲来”;他俭朴持家,为了一家人不挨饿而事事节省,甚至十五年来不舍得装一副假牙;他为家庭琐事烦心,卡什的瘸腿、达尔和朱厄尔的叛逆、艾迪的病,全都使他焦头烂额、心力憔悴。尽管科拉认为他自私自利到无药可救,完全不值得信任;尽管他在卡什摔断腿时,首先痛心的是“他(卡什)整整六个月干不了活” ,在艾迪将死之际仍不舍得请医生,仅仅是因为心疼诊费。但客观上说,这些言行举止是生活贫苦的他的本能反应,对一个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生存都有困难的农民来说,他不得不从现状出发考虑问题,而他的现状就是缺钱、缺劳动力。他的自私、冷酷很大程度上是被生活所迫,对他来说,生存才是最重要的。但在运送艾迪的尸体回杰弗生这件事上,他充分展示了一个农民的固执、忍耐和对自己道德信念的坚守。在整个过程中,他只有一个信念,“我亲口答应过她,我和孩子们一起用骡子能跑得最快的速度送她去那儿,好让她静静安息”。为了实现这个诺言,他带着一家人开始了这段艰难旅程。即使在途中遭遇洪水冲桥,人伤马亡,但他从未退缩。他甚至不惜拿出自己攒了许久的买假牙的钱、典当农具,就为了能将艾迪送到杰弗生安葬。他自始至终坚守着自己的道德观念,坚定不移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由此可见,他并非人们印象中那样自私、冷酷。
艾迪
卡什无疑是全书中最为正常的人物,他身上具备很多优秀品质。作为兄长,他包容、疼爱弟妹,知道朱厄尔彻夜打工买马,他就默默的替朱厄尔完成家里的活;作为儿子,他孝敬父母,母亲一句无关紧要的话他都会放在心上。当听到艾迪说如果有肥料的话她就试着种花时,他马上“就拿了只烤面包的平底锅到马棚去装了满满一锅马粪回来”,让母亲种花;在艾迪弥留之际,他一丝不苟、不分昼夜的赶制棺材以给母亲“带来自信,带来安逸”。在众多儿女中,他是最关心父亲的一个,在大雨中,他自己淋雨却让父亲穿上雨衣到一旁休息。卡什的身上体现了福克纳一直宣扬的勇敢、忍耐、同情等精神。在整部小说中,卡什话语不多,但他却用行动证明自己对家人的爱。在送葬这件事上,他像往常一样没有过多的发表意见。但从小说中可以看出,卡什虽木讷却并不愚蠢,他不可能不知道这趟旅程的艰辛,但是他义无反顾的踏上这条送葬路。哪怕半路为救棺材摔断腿,他也要坚持下去,忍着剧痛将母亲安葬到杰弗生。卡什正是鲁迅先生说的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他明确的认识到了现实的不幸,但勇于面对并反抗这种不幸,从而获得新生。
达尔
艾迪可以说是全书的轴心,一家人的苦难历程都是为了实现她的遗愿而展开的。作为“人”,她没有直接参与这段历程。可她的整个人生却是一段更为坎坷的“苦难历程”。艾迪是一个悲观的人,在她看来,“活着就是为长久的安眠做准备”,所以生活对她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她也是一个一直生活在幻想中的人。她嫁给安斯,期望婚姻可以改变她厌恶的教师生活,却适得其反,因为她无法使自己真正融入到琐碎婚姻生活中,以至于科拉反复告诉她“她不是一个真正的母亲”,“她对孩子们、对安斯、对上帝欠了债”;她与牧师惠特菲尔德偷情,幻想从他身上获得慰藉,但却碰上了一个敢做不敢当的懦夫,使她的愿望再一次落空。一次次的失败使她的内心世界与生活现状越来越格格不入——她的内心渴望爱却不相信爱的存在,她期盼为人理解却从未真正的敞开心扉。在她悲剧的一生中,她从未用正确的生活态度去正视现实。在她看来,活着就是为了等待死亡,所以她从未努力争取过,甚至从未真正的融入到现实的生活中去感受丈夫、儿女的爱。她的人生中只有失去,没有未来、没有希望,所以她只有在孤独、绝望中耗尽一生。
杜威·德尔
达尔也是本书的焦点人物之一。许多评论家认为他是一个“先知”,“敏感、孤独、偏执,具有神经不正常的人才特有的那种超人的想象力和洞察力,能看到不在场的事情和看透别人心里的想法”。的确,作为小说最主要的叙述者,许多不为人所知的秘密,如:杜威·德尔的怀孕,朱厄尔是私生子的事实等,都是通过他的话语显现出来的。但他更“是一个固执的丧失理智的男孩子”,他会一遍又一遍地问朱厄尔:“你是谁的儿子?”“你爹是谁,朱厄尔?”很显然,他知道答案却不敢向众人揭穿这个秘密,只能通过伤害别人来掩饰自己的懦弱。他对送葬一事的态度正是他性格的最好体现。他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现实的残酷性和这件事情本身的荒诞性,但他没有像卡什那样坦然面对,却试图用更加荒诞的行为阻止这件事。为达到目的,他不惜放火烧马棚,以期将母亲的棺材葬于火海。然而,他的过激行为是毫无意义的,并改变不了什么,那只是对现实的逃避。这种逃避现实的行为注定他最终会被现实击败,不能与其他人一起享受生活。因为“这个世界不是他的,这种生活也不是他该过的”。
作品鉴赏
一直以来评论家们对杜威·德尔的评价都以否定为主。他们认为她有“原始人的气质,既懦弱却又凶残”。事实上讲,杜威·德尔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在母亲艾迪生病期间,是她寸步不离的照顾母亲,大热天里站在母亲的身边“用一把扇子给她扇风”。母亲死后,她“俯下身去,把被子从艾迪手中轻轻的抽出来,拉直盖到下巴底下,又把它抚平、抻挺”。从这些细微的动作可以看出她对母亲是充满关爱的。与母亲一样,她也与人偷情,但被情人抛弃后,她没有像母亲那样自怨自艾,为死做准备,而是接受了现实,到城里打胎。即使打胎失败,即使明明知道了那些药“不会起作用的”,她还是选择了接受命运的安排,勇敢的活下去。可能以后的生活会更加艰难,但毕竟,活着就有希望。在反抗不幸的过程中她输了,但虽败犹荣。
主题
手法
这部小说有着一切伟大小说的基本元素:如何面对生存和死亡、大自然和人的关系、人性的善和恶、人如何面对上帝、人的家庭内部和外部的关系等等。[2]
在总体上,福克纳还是把这次出殡作为一个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行为来歌颂的。尽管有种种愚蠢、自私、野蛮的表现,这一家人还是为了信守诺言,尊重亲人感情,克服了巨大的困难与阻碍,完成了他们的一项使命。福克纳自己说:“《我弥留之际》一书中的本德仑一家,也是和自己的命运极力搏斗的”。可以认为,《我弥留之际》是写一群人的一次“奥德赛”,一群有着各种精神创伤的普通人的一次充满痛苦与磨难的“奥德赛”。从人类总的状况来看,人类仍然是在盲目、无知的状态之中摸索着走向进步与光明。每走一步,他们都要犯下一些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就这个意义说,本德仑一家不失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缩影。他们在一定意义上,是全人类的象征,他们的弱点和缺点是普通人身上所存在的弱点和缺点,他们的状态也是全人类的普遍状态。加缪对福克纳作品的主题所作的概括也许是绝对化了一些,但是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说:“福克纳给予我们一个古老然而也永远是现代的主题。这也许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悲剧:盲人在他的命运与他的责任之间摸索着前进”。福克纳有他自己的概括方式。他说:“到处都同样是一场不知道通往何处的越野赛跑”。在三十年代福克纳所在的世界里,这样的描述不失为准确与真实。福克纳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了这样的现象,应该说是忠实地反映了他周围的现实。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福克纳是一位关注人类的苦难命运,竭诚希望与热情鼓励人类战胜苦难,走向美好未来、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尽管他总是将受苦的人写得那么丑陋,在写成《我弥留之际》前的另一本小说《圣殿》里,福克纳写出了社会的冷漠、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以及人心的丑恶,道出了恶的普遍存在,而《我弥留之际》写出了一群活生生的“丑陋的美国人”。而在《我弥留之际》,福克纳依然写出了人类的勇敢、自我牺牲与理性的一面,譬如朱厄尔、卡什与达尔的那些表现。而且在总体上,福克纳是把这次出殡作为一个吉坷德式的理想主义来歌颂的,尽管有愚蠢、自私、野蛮的表现,这一家人还是为了信守诺言,尊重亲人感情,克服了巨大困难与阻碍,完成了他们的一项使命。自我净化是人类走向幸福的必由之路,正是基于这个目的福克纳才在他的作品中突出了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南方人性格中丑陋的一面。
在福克纳那里,因为他发现了人里面那种恒久忍耐、正义、为承担诺言而忍耐、责任感以及人的不可摧毁等崇高品质,人与现实的关系趋于缓解,福克纳坚信:人类通过与自身命运的极力搏斗,可以获得终极幸福,譬如本德仑太太在弥留之际达到的澄明境界,福克纳用自己终身的行动捍卫了自己所监守的信念是真实的、可信的。而《我弥留之际》写的正是一群人的一次“奥德赛”,一群有着各种精神创伤的普通人的一次充满痛苦与苦难的“奥德赛”。从人类的总体状况来看,人类仍然是在盲目无知的状态中摸索着走向光明与进步。每走一步,他们都要犯下一些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使我们认识到——人类虽然渺小,却有着无坚不摧的勇气,通过自身坚苦卓绝的努力,一定会战胜所有苦难。
作品影响
对福克纳而言,写作《我弥留之际》是一次冒险的“技术壮举”。他使出了所有的招数,譬如内心独白、多角度叙述和意识流手法等等,正是这些创作方法奠定了福克纳作为一个现代派小说家的地位。
荒诞剧
国外的批评家说这是一出悲喜剧。其实最确切的说法应该是荒诞剧,因为它具有五十年代荒诞剧的一切特色,虽然在它出版的1930年,世界文坛上还没有荒诞剧这个名称。《我弥留之际》如果与福克纳同时期创作的另一本小说《圣殿》并读,主旨就显得更清楚了。(《圣殿》的出版在《我弥留之际》之后,其实写成却在《我弥留之际》之前。)在《圣殿》里,福克纳写出了社会的冷漠、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以及人心的丑恶,写出了“恶”的普遍存在。而在《我弥留之际》里,福克纳写出了一群活生生的“丑陋的美国人”。
神话模式
《我弥留之际》中叙述的历险,与《奥德赛》和《出埃及记》就有着内在的联系。安斯的妻子与人通奸,与阿伽门农类似;它的神话原型是《奥德赛》,但是它完全没有《奥得赛》的英雄色彩。在框架上又有点像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和《旧约·出埃及记》中摩西率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也曾经历长途跋涉。只不过,在《我弥留之际》中,已没有了那种英雄气概。
意识流
福克纳抛弃了传统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而是借鉴了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1922)的意识流技巧,以及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精华,以意识流蒙太奇的表现手法追求人物的心理真实。因此这是一部比较难读的小说,如同乔伊斯那本被称为“天书”的《尤利西斯》一样,它打破了读者长期以来被惯坏了的阅读习惯。对那些只希望在作品中读到伟大人物和波澜壮阔的社会画面的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颠覆。然而《我弥留之际》的意义无法抹杀,他在难度和有趣上仍然无愧于世界名著的称谓。正是从乔伊斯,马塞尔·普鲁斯特,以及福克纳等同时代作家的努力,小说才恢复了微小事物、日常事物,甚至是无意义的生活细节在写作中的地位。通过他们的努力,写作才成功地从集体记忆力解放出来,真正进入个人内心生活的真实。
非现实主义
三十年代时,美国的一些批评家曾把《我弥留之际》作为一本现实主义小说来分析,把它看成是关于美国南方穷苦白人农民的一部风俗志,一篇社会调查。用那样的眼光来看《我弥留之际》更是没有对准焦距。这非但无助于领会作品的主旨,反而会导致得出“歪曲贫农形象”这样的结论。
因此不应那么实、那么死把本德仑一家当成美国南方穷苦农民的“现实主义形象”,他们在一定意义上是全人类的象征,他们的弱点是普通人身上存在的弱点,他们的状态也是人类的普遍状态。在福克纳大部分作品中都在表达着同样的主题,“他们在苦熬。”(They endured)。在故事的开头,艾迪·本德仑太太躺在卧榻上,她曾得到丈夫的口头保证,在她死后,遗体一定要运往她娘家人的墓地去安葬。本德仑太太死后,家人遵照她的遗愿将尸体送去40英里外的墓地埋葬而经历的一次长达十天的苦难历程。尽管每个人怀着各自的目的踏上送葬之路,尽管一路上有许多自私、愚昧、荒诞的行为发生,但这次出殡仍然具有理想主义的光辉,在与水灾、火灾的斗争中,显示了人的力量。
作者简介
《我弥留之际》自出版以来,评论家们一直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这部作品被许多评论家认为是代表福克纳最高创作成就的作品之一,也是福克纳高超意识流技巧的体现。也是威廉·福克纳一部实验性的作品,也是一部为他带来国际性声誉的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杰作。作品剔除让读者眼花缭乱的技术外,它的真正价值在于:重估人对苦难的承受力。福克纳借助他独特的叙事方法,将那些看起来完全是记忆碎片重新整和、结构,恰恰在他将整个世界折开的同时重新建筑了起来。
《我弥留之际》在当时是一部具有实验性的小说,是对西方流行的探求文学模式的讽刺性模拟。是了解福克纳其他更具有挑战性小说的入口。这本小说已经为作者以后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系列作品做好了铺垫,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本小说中,福克纳描写的不仅仅是南方人,评论家们集中关注其中人类忍受苦难的能力以及最终取胜的人道主义思想。并且他还触及到了整个现代世界和人类的生存状况,而这正是福克纳整个“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作品系列的主题所在。
词条图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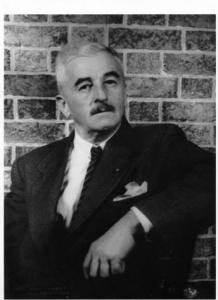 威廉·福克纳(3)威廉·福克纳(Willian Faulkner 1897~1962),美国小说家。他被西方文学界视作“现代的经典作家”。共写了19部长篇小说和7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绝大多数故事发生在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被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这部世系主要写该县及杰弗生镇不同社会阶层的若干家庭几代人的故事。时间从独立战争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场人物有600多人,其中主要人物在他的不同作品中交替出现,实为一部多卷体的美国南方社会变迁的历史。其最著名的作品有描写杰弗生镇望族康普生家庭的没落及成员的精神状态和生活遭遇的《喧哗与骚动》;写安斯·本德仑偕儿子运送妻子灵柩回杰弗生安葬途中经历种种磨难的《我弥留之际》;写一个有罪孽的庄园主塞德潘及其子女和庄园的毁灭性结局的《押沙龙,押沙龙!》;福克纳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3]
威廉·福克纳(3)威廉·福克纳(Willian Faulkner 1897~1962),美国小说家。他被西方文学界视作“现代的经典作家”。共写了19部长篇小说和7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绝大多数故事发生在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被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这部世系主要写该县及杰弗生镇不同社会阶层的若干家庭几代人的故事。时间从独立战争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场人物有600多人,其中主要人物在他的不同作品中交替出现,实为一部多卷体的美国南方社会变迁的历史。其最著名的作品有描写杰弗生镇望族康普生家庭的没落及成员的精神状态和生活遭遇的《喧哗与骚动》;写安斯·本德仑偕儿子运送妻子灵柩回杰弗生安葬途中经历种种磨难的《我弥留之际》;写一个有罪孽的庄园主塞德潘及其子女和庄园的毁灭性结局的《押沙龙,押沙龙!》;福克纳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3]

-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2025-09-20 05:02:52 查看详情


 求购
求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