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俗文学

通俗文学
众说纷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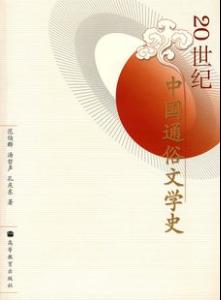 正如对赵树理作品的评价在历史上众说纷纭一样,对“通俗文学”这一概念的厘定现在看来也是充满了内在的矛盾。因为首先,如果说“通俗文学”和市场——如果大家同意,可以包括经济的市场和观念的市场——是有巨大关系的,那么,我们在谈论市场的时候,必须注意到市场的多样性,在现代都市的市民阶层之中存在市场,那么在中国更广袤的农村社会难道不存在市场吗?我想当然是有的,赵树理的存在本身就已经很有力的印证了这个农村文化市场的存在。其次,如果说“通俗文学”是接续了某种中国传统的,或者承继了某种传统的文化趣味的,那么我想,和程小青等人相比,赵树理反而是更传统,更乡土,更有中国趣味的——他本来就是在毛泽东“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理论指导下写作的嘛。因此,我理解范先生何以在上述引文中使用“通俗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还冠以“市民”二字。在“通俗文学”和“市民文学”的概念之间容忍某种混淆,把“市民文学”的趣味和标准潜在的化入对“通俗文学”的考察和描述,是我们今天更加难以进入历史语境了解通俗作品和时代之间关系的一种障碍。相比而言,“市民文学”或者“市民的文学”是更清晰的表明了文学和特定时代特定社会阶层的联系的。
正如对赵树理作品的评价在历史上众说纷纭一样,对“通俗文学”这一概念的厘定现在看来也是充满了内在的矛盾。因为首先,如果说“通俗文学”和市场——如果大家同意,可以包括经济的市场和观念的市场——是有巨大关系的,那么,我们在谈论市场的时候,必须注意到市场的多样性,在现代都市的市民阶层之中存在市场,那么在中国更广袤的农村社会难道不存在市场吗?我想当然是有的,赵树理的存在本身就已经很有力的印证了这个农村文化市场的存在。其次,如果说“通俗文学”是接续了某种中国传统的,或者承继了某种传统的文化趣味的,那么我想,和程小青等人相比,赵树理反而是更传统,更乡土,更有中国趣味的——他本来就是在毛泽东“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理论指导下写作的嘛。因此,我理解范先生何以在上述引文中使用“通俗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还冠以“市民”二字。在“通俗文学”和“市民文学”的概念之间容忍某种混淆,把“市民文学”的趣味和标准潜在的化入对“通俗文学”的考察和描述,是我们今天更加难以进入历史语境了解通俗作品和时代之间关系的一种障碍。相比而言,“市民文学”或者“市民的文学”是更清晰的表明了文学和特定时代特定社会阶层的联系的。
存在矛盾
 然而,就是从这样的矛盾的概念出发,中国的“通俗文学”在今天是获得了巨大的合法性和确定性。上接唐传奇、宋话本、明清的章回小说,中承晚清之谴责与黑幕,到张恨水、程小青、李寿民等等,再到是金庸、古龙和琼瑶,如果算到如今这个“网络时代”,可能就有安妮宝贝之类的作者吧。“通俗文学”成了一个一脉相传的伟大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形成了自己的古典,自己的过渡和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个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当中,赵树理,包括后来的山药蛋派,包括后来的黄子平意义上的“革命历史小说”,我想还应该包括今天像张平这样的很大众化的作家,当然就是些异类,更不要说文革时候的东西。对于“八大样板戏”,范伯群先生的看法是:“总算是用行政手段推行而达到了极致,可以说达到了全民‘大普及’,但这些作品的创作既不符合创作的内在规律,也无法进入民众的心灵”。
然而,就是从这样的矛盾的概念出发,中国的“通俗文学”在今天是获得了巨大的合法性和确定性。上接唐传奇、宋话本、明清的章回小说,中承晚清之谴责与黑幕,到张恨水、程小青、李寿民等等,再到是金庸、古龙和琼瑶,如果算到如今这个“网络时代”,可能就有安妮宝贝之类的作者吧。“通俗文学”成了一个一脉相传的伟大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形成了自己的古典,自己的过渡和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个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当中,赵树理,包括后来的山药蛋派,包括后来的黄子平意义上的“革命历史小说”,我想还应该包括今天像张平这样的很大众化的作家,当然就是些异类,更不要说文革时候的东西。对于“八大样板戏”,范伯群先生的看法是:“总算是用行政手段推行而达到了极致,可以说达到了全民‘大普及’,但这些作品的创作既不符合创作的内在规律,也无法进入民众的心灵”。
贴近百姓
 通俗文学就在我们的周围,最贴近我们的生活,最能迎合大众的口味,最能反映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最能展现人民的审美观,也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虽然所有的通俗文学,不一定都能成为名著,但绝大多数的名著,在其诞生之初,都是通俗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名著是通俗文学这座金字塔的塔尖,高高在上,令读者敬畏多于亲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毕竟是少数,能读懂文学名著的人也是少数。文学名著有其特定的阅读群体和专家群体,而通俗文学就没有,它适合各个阶层。有的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读过一本文学名著,却可能看了不少通俗文学的作品。我们常常看到有人在闲暇时沏一杯茶,捧一卷书,悠闲惬意的阅读。读的什么书呢?武侠、言情、侦探、科幻,甚至是连环画。这就是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的阅读。还有一种现象非常有趣。文学名著的影响力往往不是来自作品本身,而是得益于其他艺术形式对名著的通俗化演绎。譬如,正是评书、曲艺、戏剧等通俗化的艺术形式让《三国》、《水浒》、《红楼梦》、《西游记》这样的古典文学名著走入千家万户,贴近寻常百姓。而大部分评书、曲艺、戏剧也是通俗文学的一部分。通俗是文学的生命力,是文学必然的发展方向。通俗文学比文学名著影响大,这不仅是二者定位不同的必然,更为历史和现实所证明,是不争的事实。
通俗文学就在我们的周围,最贴近我们的生活,最能迎合大众的口味,最能反映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最能展现人民的审美观,也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虽然所有的通俗文学,不一定都能成为名著,但绝大多数的名著,在其诞生之初,都是通俗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名著是通俗文学这座金字塔的塔尖,高高在上,令读者敬畏多于亲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毕竟是少数,能读懂文学名著的人也是少数。文学名著有其特定的阅读群体和专家群体,而通俗文学就没有,它适合各个阶层。有的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读过一本文学名著,却可能看了不少通俗文学的作品。我们常常看到有人在闲暇时沏一杯茶,捧一卷书,悠闲惬意的阅读。读的什么书呢?武侠、言情、侦探、科幻,甚至是连环画。这就是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的阅读。还有一种现象非常有趣。文学名著的影响力往往不是来自作品本身,而是得益于其他艺术形式对名著的通俗化演绎。譬如,正是评书、曲艺、戏剧等通俗化的艺术形式让《三国》、《水浒》、《红楼梦》、《西游记》这样的古典文学名著走入千家万户,贴近寻常百姓。而大部分评书、曲艺、戏剧也是通俗文学的一部分。通俗是文学的生命力,是文学必然的发展方向。通俗文学比文学名著影响大,这不仅是二者定位不同的必然,更为历史和现实所证明,是不争的事实。

-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2025-11-02 01:06:08 查看详情


 求购
求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