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
- 首页
-
- 百科
-
- 发动机系统
-
-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
人物生平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1905年5月24日生于维申斯克省的顿斯科伊军屯的克鲁日林村(今罗斯托夫州维申斯克区)的农民家庭,母亲出嫁前一直给地主家当女仆;父亲是个哥萨克下级军官;继父是平民知识分子“外乡人”,年轻时当雇工,后来做过商店店员和磨坊经理,十月革命后担任苏维埃政权下粮食部门的职员。他的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在那里度过,青少年时期广泛的社会经历,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1905年5月24日生于维申斯克省的顿斯科伊军屯的克鲁日林村(今罗斯托夫州维申斯克区)的农民家庭,母亲出嫁前一直给地主家当女仆;父亲是个哥萨克下级军官;继父是平民知识分子“外乡人”,年轻时当雇工,后来做过商店店员和磨坊经理,十月革命后担任苏维埃政权下粮食部门的职员。他的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在那里度过,青少年时期广泛的社会经历,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4年肖洛霍夫先是被送往莫斯科,后来又回到哥萨克村里上学。十三岁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对乌克兰的入侵中断了他的学业。1919年至1922年这段时间里,年轻的肖洛霍夫为红军做过各种工作,其中一项是在顿河地区征集军粮,大部分哥萨克人却竭力抵制布尔什维克的“横征暴敛”。1922年,肖洛霍夫去莫斯科,加入了“青年近卫军”,成为年轻的无产阶级作家组织的一员。同年,肖洛霍夫来到莫斯科,开始从事文学活动,并参加了文学团体“青年近卫军”。1923年,肖洛霍夫与一位哥萨克的女教师玛丽姬·格罗斯拉夫斯卡娅结婚。1923—1924年间在《青年真理报》上登载了他的三篇杂文《考验》、《三》、《钦差》和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胎记》。1924年加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拉普),成为职业作家。
1926年作品集《顿河故事》和《浅蓝的原野》出版。1925年他们回到了顿河地区定居。《静静的顿河》第一部的巨大成功使肖洛霍夫声名鹊起,经过14年的时间终于全部闻名于世1926年,他出版小说集《顿河故事》和《浅蓝的原野》(后合为一集),受到文坛的关注。在集子的2”多篇小说中,作家把严峻而复杂的社会斗争浓缩到家庭中间和个人关系之间展开,在哥萨克内部尖锐的阶级冲突的背景中展示了触目惊心的悲剧情景和众多的悲剧人物。早期作品特色鲜明,但艺术上还欠成熟。
1930年肖洛霍夫见到了斯大林,在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写出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1932);(第二部一些篇章从1955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于1960年最后完成全书,获得1960年度列宁奖金。)1932年肖洛霍夫成为一名正式的苏共党员。
根据后来发表的文件,肖洛霍夫曾两次在斯大林的亲自过问下,于30年代救助过遭受饥荒和政治清洗的顿河人民。
1938年10月罗斯托夫州安全部门罗织肖洛霍夫组织哥萨克暴动的罪名,并派人到肖洛霍夫那里卧底,要将他逮捕,置之死地。肖洛霍夫得到消息后,逃到莫斯科,求见斯大林才幸免罹难。在30年代,肖洛霍夫的国际声誉逐渐上升,他在文学界为党所做的政治工作使他得以崛起。
卫国战争时期,肖洛霍夫上过前线,写了许多通讯、特写和短篇小说,揭露德国法西斯的野蛮侵略罪行,歌颂苏联军民的爱国热枕和英雄功绩,如《学会仇恨》等。1943年开始发表反映卫国战争的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未完成,1943—1944年,以连载形式发表,这部小说早就构思好了,但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推迟脱稿)。
195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 (又译《人的命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称为当代苏联军事文学新浪潮的开篇之作。
斯大林死后,肖洛霍夫逐渐成为苏联文学界的元老,他接受过各种奖励,给文学社团和学校团体作过报告,向年轻人提出种种建议,但与此后涌现出的作家的接触却越来越少。肖洛霍夫为战后文学史上日丹诺夫的高压政策辩护,并对在国外发表作品的苏联作家进行攻击,结果招致了许多苏联严肃作家的憎恶。他还成为反美宣传的代言人。然而,他在群众中的威望仍然很高,他的描写顿河哥萨克人的小说也一直被列为学校的教科书。
1956年到1960年,肖洛霍夫的八卷本全集在苏联出版,此后的各卷也陆续发行。1984年肖洛霍夫全集的英译新版本问世。
1965年,肖洛霍夫因其“在描写俄国人民生活各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力量和正直品格”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获其他多种荣誉。
1984年肖洛霍夫在他的出生地克鲁齐林诺村去世。
1999年,“顿河”手稿被发现存于其密友库达绍夫的远亲家中。后总统普京下令财政部筹款,以50万美元购得,目前珍藏于“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2005年命名为“肖洛霍夫年”。
主要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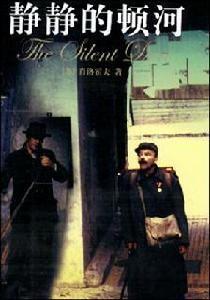 《静静的顿河》《静静的顿河》[3]
《静静的顿河》《静静的顿河》[3]
《新垦地》(旧译《被开垦的处女地》)
《一个人的遭遇》
《考验》
《三》
《钦差》
《顿河故事》
《浅蓝的原野》
《他们为祖国而战》
主要成就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作品(3)肖洛霍夫为意识形态对立的东西方两个世界共同认可。他也是惟一既获斯大林文学奖,又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这在苏俄文学史上绝无仅有。肖洛霍夫的小说对顿河流域的史诗般的描写,揉进了东西方文化的特质,对人性的张扬与文学艺术的创新。肖洛霍夫从孩提时代就十分谙熟俄罗斯顿河哥萨克人的生活,并在自己的作品中真实记述了哥萨克人在苏联政权发生急剧性转变初期的生活状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作品(3)肖洛霍夫为意识形态对立的东西方两个世界共同认可。他也是惟一既获斯大林文学奖,又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这在苏俄文学史上绝无仅有。肖洛霍夫的小说对顿河流域的史诗般的描写,揉进了东西方文化的特质,对人性的张扬与文学艺术的创新。肖洛霍夫从孩提时代就十分谙熟俄罗斯顿河哥萨克人的生活,并在自己的作品中真实记述了哥萨克人在苏联政权发生急剧性转变初期的生活状态。
肖洛霍夫以他非凡的智慧,创作了不朽的著作。肖洛霍夫是苏联的一位文学巨人,其作品影响之大,读者之多, 在苏联作家中罕有其匹。截至1980年1月,他的作品用苏联各民族的54种语言和30种外国语言出版了974次,总印数达790万册。他享有最高的文学荣誉:获得斯大林奖金、列宁奖金和诺贝尔文学奖金,曾获五枚列宁勋章、两枚镰刀与锤子金质奖章及国内外其它各种奖章和勋章。他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曾是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苏联科学院院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和苏共中央委员。
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维奇·肖洛霍夫是二十世纪苏联文学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读者十分熟悉且至今仍给予特殊关注的作家。这不仅仅因为他给世界人民留下了《静静的顿河》、《新垦地》(旧译《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等珍贵的文学遗产,还因为他一生的创作和文学活动与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始终存在着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并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十年代末,中国新文学奠基人鲁迅首先注意到肖洛霍夫的作品。1928年《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在《十月》杂志上发表,第二年鲁迅先生便约请贺非翻译,并亲自校订,还撰写了后记。1931年《静静的顿河》中译本作为鲁迅编辑的“现代文艺丛书”之一,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从此,肖洛霍夫的作品几乎每发表一部,都很快介绍到中国来。尤其是《一个人的遭遇》在《真理报》上刚一刊出,当月就译成了中文,而且有两个不同的译本,先后在《解放军文艺》和《译文》上发表。这在中国翻译史上是难寻之事。
肖洛霍夫对中国作家影响颇深。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客观真实的创作原则、关注普通人命运的创作立场、魅力无穷的人性刻画以及魂牵梦萦的乡土情结。中国作家在吸收和借鉴肖洛霍夫创作经验的基础上,还继承了本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而形成他们自己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
肖洛霍夫是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苏联作家,其作品在中国产生过巨大影响,尤其对中国许多现当代作家的创作泽被深远。当《静静的顿河》第一部中译本在中国即将面世时,鲁迅就准确地预见了此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将来倘有全部译本,则其启发这里的新作家之处,一定更为不少。但能否实现,却要看这古国的读书界的魄力而定了。”此后的历史验证了这一预言的正确性。在周立波、丁玲、柳青、刘绍棠、陈忠实等现当代作家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见到“肖洛霍夫的影响因子”,它宛如一条生生不息的长河,静静地流淌在中国作家的创作血液中。
创作特点
语言特点
肖洛霍夫的叙述语言充满了各种方言词汇。无论是他的主要人物的语言,还是他自己的叙述语言,都常常恰当地引用哥萨克人流行的有代表性的词汇或俗语:“迈开飞毛腿窜了”,“七扭八弯的战壕”“稀松的乌焦墨黑的土地”,“在路对过里”——这类用语时时在小说里出现。肖洛霍夫还按照这种方式创造自己的比拟和隐喻。例如:“ 一刀下去,被砍断的枝条往一旁落下,然而枝千却纹丝不动。哥萨克军刀锋利的刀尖戳进麦桔旁的沙袋,然后又被拔出来。长得有点像加尔梅克人的美男子西米格拉左夫正是挨了这样的一刀,他双手捂着被砍开的胸口,从鞭子上掉下,落到竖起的马身下面。”
他在小说里引进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对事件作了军事性和历史性的评论,这构成了作品华语言的新特点。由于主要人物的语言各不相同,作者的叙述语言也很生动,他的作品的语言变得丰富多彩有时作者的语言和主要人物的语言交织成五光十色的图画。有时,又来一段精彩的抒情;有时,大胆使用文献语言,这一切完整地构成了叙述语言的复杂多样。这是与小说中所提供的材料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它深刻的思想性相适应的。
肖洛霍夫创作的本质特色,是“严酷的真实”。作家全部的创作活动,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是“正直地同读者谈话,向人们讲述有时是严峻的,但永远是勇敢的真实”。肖洛霍夫与其他作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直书全部的真实”,正如费定所论述的:“肖洛霍夫的巨大功勋表现在他的作品所具有的那种胆识之中。无论他反映任何一个时代,他都不回避生活所固有的种种矛盾。他的书全面地描写过去和规在的斗争。这就使我不由地记起列夫·托尔斯泰在年轻的时候给自己立下的约言:不仅不要直接撒谎,并且也不要消极地通过避而不谈来撒谎。肖洛霍夫从不避而不谈,他直书全部的真实,他决不把悲剧变成为正剧,也不把正剧写成使人入迷的消遣读物。他不把悲剧的场景掩藏在宽慰人心的一束束野花之中,但是真实的力量是那样强大,无论生活的苦痛多么可怕,都会被向往幸福的强烈意志、获得幸福的愿望和赢得幸福之后的欢畅所压倒、所征服”。
人物形象
顿河哥萨克农民的生活是肖洛霍夫创作的源泉。选取农村题材,描写农民生活是肖洛霍夫创作的一大特色。作家立足子顿河草原,以哥萨克农民为描写对象,展示出他们粗野外表掩盖下的火一般的激情,塑造了一批‘强有力的个性”。他第一次真正地把农民推上历史舞台的中心,他笔下的哥萨克农民既是历史的积极创造者,同时也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改造着自身。肖洛霍夫并不是第一个将农民引进文学的作家,在他之前就已形成了农民题材方面的传统。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农民题材在俄国文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屠格涅夫以真诚的、诗一般的笔触表现了俄罗斯农民的智慧和精神美。托尔斯泰对农民题材和农民生活有着特殊的兴趣,他把自己的宗法制社会生活的理想寄托在对农民的描写之中。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一批民粹派作家对俄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种贡献突出地表现在对农民生活的描写之中。他们深入农村,但由于思想的局限,他们不可能全面公正地描写农民。他们把农民当成一种特殊类型的人。农民被描写成既是“十足的醉鬼”、“顽命徒”,又是负有拯救世界使命的“圣徒” 。
他善于深刻而又多方面地刻画人物,维妙维肖地描写人物对话,精细地描写顿河流域壮美的自然风光。这些特点在长篇巨著《静静的顿河》里也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现。
肖洛霍夫写人物从来不遵循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的公式,从来不用单一的色彩描绘人物。他在表现某些新社会优秀分子的成就和高贵品质时,并不一笔抹杀他们的缺点和错误以及作为人的许多弱点。比如他描写了彭楚克在阶级斗争残酷性面前表现出的软弱;珂晒沃依在生死关头表现出的胆怯;彼得捷尔珂夫在虐杀战俘时表现出的残忍;达维多夫在爱情迷误中表现出的庸俗;拉兹米推洛夫在感情上摆脱不了的缠绵。他从来不把共产党人、革命者塑造成一贯正确、无所不能的完人,而是把他们作为真人的活的灵魂呈现在读者面前。在描写阶级敌人时,肖洛霍夫同样没有忽略真实性。他不仅表现反动势力在道德上的堕落及其被消灭的过程,而且还表现他们开展破坏活动中的某些暂时得逞,如鲁基奇、奥斯特洛夫诺夫、罗夫采夫等人在挑拨党和哥萨克的关系上、在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得手。肖洛霍夫在表现敌人时,反对用漫画式的手法来描写他们,他不排除他们也有人的自然行为,也有感情和眷恋,但他让读者在自然人性之外更看到了敌人的畸形的残忍感情以及道德上的堕落。肖洛霍夫谈起苏联文学应该如何表现敌人的问题时说:“文学必须毫不隐瞒、毫无掩饰地讲述我们的朋友和敌人”,他认为:“我们总是标语口号式地、简单化地描写敌人,这只能使读者解除武装。”所以在肖洛霍夫的笔下,敌对营垒中的人物在反对革命、反对人民的共同特点中,都有独特的、符合他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教养的个性特点。
悲剧形式
肖洛霍夫对悲剧题材有特殊的偏爱。他以无比的胆识和勇气写社会主义时代的悲剧,他的整个创作都着眼于发掘和传达时代与社会的悲剧性内容,他笔下的人物很少不是悲剧性结局。可以说,他追求的是悲剧形式的真实。现实主义要求作家真实地摹写生活,真实性是现实主义作家共有的特点,但即使在真实地反映现实这一点上不同的作家又有不同的特点。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肖洛霍夫,他“写真实”有自己的个性,即把真实性寄寓于悲剧,以悲剧的形式来概括真实。在《静静的顿河》里,作家把生活的严酷与人物的悲剧结合起来,通过葛利高里的悲剧性命运来揭示‘ 强有力的个性” 的力量。葛利高里的悲剧,不是性格悲剧,亦非命运悲剧,而是寄寓于社会巨变与个性的激烈冲突之中。葛利高里作为作家喜爱的主人公,被赋予了勤劳正直等美好的品性,他的魅力就在于:不管肇活如何残酷,道路怎样曲折,命运多么坎坷,他自始至终保持着完整的个性,他在社会斗争的漩涡中左玲右突,积极寻求自己的理想。探求哥萨克的真理,是他性格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他所追求的是正直的生活以及是生存的权利。
肖洛霍夫通过情节生动的故事,出色地描绘了国内战争,就象犁痕一样把敌我双方的人区分得清清楚楚。孩子杀死父亲( 《种瓜人》和《粮食委员》) 父亲杀戮爱子( 《胎记》和《成了家的人》) ,在流血和残忍的战斗中诞生了新生活。在严峻的斗争中,肖洛霍夫看到了人们身上美好的品德,表现那些在人们身上唤起这种美好品德的共产党员,他的小说充满了对人的信心,显示了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表现出的崇高精神。这些作品显示出作者的洞察力和择取典型特征的本领,但也带有一些自然主义色彩和滥用方言土语的弊病。
肖洛霍夫是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从生活出发,尊重生活真实,反对违背生活真实。他作品所表现的历史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展开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氛围都有严格的依据。创作《静静的顿河》时,他曾奔走于顿河各村镇,收集民歌和传说,到各大图书馆查阅资料,他曾实地考察过当年的战场. 他尊重历史的真实,勇敢地揭示历史事件的真相。他从艺术的角度,诊释了1919年顿河暴动的起因,指出是由于苏维埃政权的“左”倾过头行为和红军某些人违法乱纪导致的。小说第三部因此发表受阻,某些“拉普”的领袖们指责作家为暴动辩护,甚至说他是反革命分子。但作家没有屈服,而是坚持自己的立场,这显示了他尊重历史真实的严肃态度。肖洛霍夫所追求的,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这也体现在人物塑造上. 例如葛利高里的返回故土,就是作家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的神来之笔,这已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了。再如丽亚的自杀,并不意味着这个人物性格发展的中断,恰恰相反是性格发展的顶点。她的忏悔是人性的复苏,在她的忏悔里我们看到了这个放荡不羁毒如蛇蝎的女人身上的人情味,沉河前的忏悔也显示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
人物评价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围绕着肖洛霍夫的作品,在俄罗斯乃至在世界许多国家,一直颇多争议。尽管他曾因《静静的顿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事前事后这些争议始终没有平息。关于肖洛霍夫本人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也评价不一,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分歧更大:有人指责说,他实际上在各重要历史阶段,曾经为许多错误政策张目:有人则维护说,他先知先觉,大智大勇,从二、三十年代起就是反对错误路线的英雄。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围绕着肖洛霍夫的作品,在俄罗斯乃至在世界许多国家,一直颇多争议。尽管他曾因《静静的顿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事前事后这些争议始终没有平息。关于肖洛霍夫本人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也评价不一,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分歧更大:有人指责说,他实际上在各重要历史阶段,曾经为许多错误政策张目:有人则维护说,他先知先觉,大智大勇,从二、三十年代起就是反对错误路线的英雄。
从艺术成就来看,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学者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苏联著名的文学家高尔基在1931年看完了《静静的顿河》第三部手稿后,认为:“肖洛霍夫非常有才能,他可以造就成为一个优秀的苏联作家。”法捷耶夫这样说过:“肖洛霍夫有着怎样巨大神奇的吸引人的力量啊。可以直率坦白地说,当你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会体验到一种真正的创作上的忌妒心情,真想偷走许多东西。”康·米·西蒙诺夫则认为: “有这样一些作家,如果不读他们的作品,就不可能对某一国家的当代文学得出明确的概念。我们就有几位这样作家。肖洛霍夫便是其中之一。”
法国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说过,苏联作家新的优秀作品,例如肖洛霍夫的作品,是同上一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相联系的,这个传统体现了俄国艺术的实质,而以肖洛霍夫为代表的苏维埃文学使这个伟大传统的特点为之一新。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我非常喜欢俄国文学。当代作家中,我喜欢肖洛霍夫。”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说,肖洛霍夫的书“一旦读起来,就会爱不释手”。鲁迅也盛赞肖洛霍夫的作品: “风物既殊,人情复异,写法又明朗简洁,绝无旧文人描头画角、婉转抑扬的恶习,华斯珂普所说的,充满着原动力的新文学的大概,已灼然可以窥见。
苏联批评家尤·鲁金说:“肖洛霍夫永远充满着对人的爱⋯⋯他的心灵是向人的一切痛苦和所有能够把人变成大写字母的‘人’的美好东西敞开着的。”所以求善是肖洛霍夫艺术活动的目的和理想,他的美学思想就是用美的方式、艺术的方式去表现真和善,实现真善美的统一。”
肖洛霍夫是苏维埃文学史上极其独特的现象——他作为极具争议的作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世纪末,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动荡不已,波及文坛,殃及肖洛霍夫。在文学圈内一部分人出现了将肖洛霍夫妖魔化的苗头,更多的人则误解或曲解肖洛霍夫、曲解他的作品。有人将肖洛霍夫称为“斯大林分子”,有人要追究肖洛霍夫在道德和艺术上堕落的原因。有人认定,在创作《被开垦的处女地》的过程中肖洛霍夫落入了“跟真理作对,跟良心作对”的痛苦境地。更广泛流传(在世界范围内)的,则是《静静的顿河》不是肖洛霍夫所作,他是剽窃者之类的传言。
社会影响
肖洛霍夫为意识形态对立的东西方两个世界共同认可。他也是惟一既获斯大林文学奖,又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这在苏俄文学史上绝无仅有[5]。肖洛霍夫的小说对顿河流域的史诗般的描写,揉进了东西方文化的特质,对人性的张扬与文学艺术的创新。肖洛霍夫从孩提时代就十分谙熟俄罗斯顿河哥萨克人的生活,并在自己的作品中真实记述了哥萨克人在苏联政权发生急剧性转变初期的生活状态。
肖洛霍夫以他非凡的智慧,创作了不朽的著作。肖洛霍夫是苏联的一位文学巨人,其作品影响之大,读者之多,在苏联作家中罕有其匹。截至1980年1月,他的作品用苏联各民族的54种语言和30种外国语言出版了974次,总印数达790万册。他享有最高的文学荣誉:获得斯大林奖金、列宁奖金和诺贝尔文学奖金,曾获五枚列宁勋章、两枚镰刀与锤子金质奖章及国内外其它各种奖章和勋章。他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曾是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苏联科学院院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和苏共中央委员[6]。
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维奇·肖洛霍夫
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维奇·肖洛霍夫是二十世纪苏联文学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读者十分熟悉且至今仍给予特殊关注的作家。这不仅仅因为他给世界人民留下了《静静的顿河》《新垦地》(旧译《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等珍贵的文学遗产,还因为他一生的创作和文学活动与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始终存在着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并产生了一定影响[7]。
中国新文学奠基人鲁迅首先注意到肖洛霍夫的作品。1928年《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在《十月》杂志上发表,第二年鲁迅先生便约请贺非翻译,并亲自校订,还撰写了后记。1931年《静静的顿河》中译本作为鲁迅编辑的“现代文艺丛书”之一,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从此,肖洛霍夫的作品几乎每发表一部,都很快介绍到中国来。尤其是《一个人的遭遇》在《真理报》上刚一刊出,当月就译成了中文,而且有两个不同的译本,先后在《解放军文艺》和《译文》上发表。这在中国翻译史上是难寻之事[7]。
肖洛霍夫对中国作家影响颇深。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客观真实的创作原则、关注普通人命运的创作立场、魅力无穷的人性刻画以及魂牵梦萦的乡土情结。中国作家在吸收和借鉴肖洛霍夫创作经验的基础上,还继承了本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而形成他们自己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8]。
肖洛霍夫是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苏联作家,其作品在中国产生过巨大影响,尤其对中国许多现当代作家的创作泽被深远。当《静静的顿河》第一部中译本在中国即将面世时,鲁迅就准确地预见了此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将来倘有全部译本,则其启发这里的新作家之处,一定更为不少。但能否实现,却要看这古国的读书界的魄力而定了。”此后的历史验证了这一预言的正确性。在周立波、丁玲、柳青、刘绍棠、陈忠实等现当代作家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见到“肖洛霍夫的影响因子”,它宛如一条生生不息的长河,静静地流淌在中国作家的创作血液中[8]。
人物思想
政治思想
现实生活中的肖洛霍夫无疑是一个主流意识形态的拥护者,是一个“共产主义信徒”、“无产阶级作家”。肖洛霍夫在每一个重要时期都站在主流意识形态一边。
在农业集体化时期,作为作家,他不仅仅限于为创作而去体验生活,而是直接投身到火热的生活中,去亲身感受时代脉搏的跳动。不是集体化运动的旁观者,而是积极投身于这场运动,成为运动坚定的支持者与参加者。他的足迹遍及哥萨克村、镇,到处发表热情的演说,号召人们加入集体农庄。这一过程中,他宏观上积极支持斯大林的农业政策,微观上细致地落实农业集体化的措施。当发现集体化实施过程中出现弊端与不足时,他不仅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指导、纠正,而且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反映,甚至直接给斯大林写信。当时,农庄庄员在播种时偷拿种子充饥,这事关乎着粮食产量的增减。他就向斯大林写信反映,揭露播种人盗窃种子的方法,并建议,“为了防止播种人擅自改变播种量,应责成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往播种机上安装下列这样一个既简单而又无须花什么钱的附件:在播种量监测器手柄的底部钻一个孔;在种子箱后壁的左侧牢牢拧一个套环扣的螺钉,要求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委员在确定播种量时简单处理一下,就可以使播种人无法减少播种量了: 用一节细绳儿或金属丝将手柄上的小孔与螺钉上的环扣连接起来,系上死扣,再打上铅封。我相信,采取这样一个措施会少流失很多粮食。”这表现出他对待集体化的态度。为了歌颂集体化,他创作了《被开垦的处女地》。有时,他不仅仅是一个斯大林政策的拥护者,甚至有点极“左”的倾向。肃反运动使苏联党政军各部门的领导干部都受到了极大的重创,作家、学者也受到迫害,肖洛霍夫自己亦受到很大冲击。到1939年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时,连日丹诺夫也承认,在过去的大清洗中有过火行为,使不少无辜者蒙受不白之冤。可是肖洛霍夫却在同一次会上发表了一通热情洋溢的演说,认为苏联文学的队伍由于清除了“敌人”,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健康了。当然,这可能是他在当时肃反运动冲击波残存的环境下的一种生存本能使然。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
在赫鲁晓夫时期,这明显表现在“《日瓦戈医生》事件”上。1957年,帕斯捷尔纳克发表了《日瓦戈医生》。1958 年,作者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部小说所描绘的主人公,最初是个“憧憬革命”的“高尚青年”,但十月革命后他哀叹“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遭到了破坏和毁灭”,他备尝艰辛,最后倒毙街头。该书在苏联国内未能发表,而在意大利首先出版发行,继而在西方广为传播。它被西方利用来攻击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对此反应强烈,作家协会将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只是在他作了检讨并拒往受奖之后才恢复其会籍。对此,肖洛霍夫曾发表谈话,说“《日瓦戈医生》无疑是反苏的,把一个人开除出作家协会并不是在经济上使他为难,而是要激发他的天良。”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在文艺政策上力求平息争论,加强领导和控制,提出了“反对两个极端”和“写正面人物”的方针。即既反对粉饰现实,又反对给现实抹黑,并要求表现生活中的美,塑造“当代英雄”形象。对于“坚持反苏立场”和“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则给予严惩。在1967年5月召开的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不同倾向的作家展开争论。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在给大会的一封信中提到出版自由的问题。肖洛霍夫对一些青年作家的政治态度,特别是对“出版自由”之类的呼声感到恼火,他说,“最近西方发出了不少呼声,赞成给我们苏联作家以创作的-自由. 。这是一批不请自来的啦啦队长,他们当中有中央情报局,,某些美国议员,狂热的白卫分子,叛徒阿利卢耶娃,还有臭名昭著的,早已成为政治僵尸的克伦斯基。我们那些热衷于出版自由的人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是与这样一些乌七八糟的人为伍的。”可见,肖洛霍夫的观念与主流意识形态十分吻合。西方许多评论者也都认为,肖洛霍夫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党。正如1965年肖洛霍夫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皇家学院院士安德斯·奥斯特林在授奖词中对他的评价一样:“肖洛霍夫无疑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美学思想
肖洛霍夫认为小说是能使艺术家“描绘出现实世界最广阔的图景,并能以此反映自己对现实世界及其重大问题的看法的文学形式”。然而这样一来,现实主义就融进了现代特征,于是肖洛霍夫称其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传播革新生活,并为了人类利益去重建生活理想的现实主义”。
肖洛霍夫的美学思想有两个要点,一是求真。他敢于面对严酷无情的现实,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他曾明确表示他的创作是为了“正直地同读者谈话,向人们说出真理——有时是严峻的,但永远是勇敢的真理,在人类心灵中坚定对于未来的信念和对于自己能够建成这一未来的力量的信念”。也就是说,肖洛霍夫认为艺术家要敢于面对现实,勇敢地揭露矛盾,尊重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而不是粉饰现实或歪曲现实。
他认为,艺术真实要遵循生活真实的原则,即使微小的细节也不能疏忽。他说:“一个作家哪怕是在一些细枝末节上违背了真实,他也要引起读者的不信任,读者会想:‘这一点可以说明,他在大事上也可能撒谎’。”肖洛霍夫这样严格要求自己,说明他是从保证作品的价值和作家的声誉乃至文学的声望的高度来看待真实性的。他作品中所表现的历史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展开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氛围都有严格的依据。创作《静静的顿河》时,他曾到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搜集国内战争资料;曾奔走于顿河各村镇,收集民歌和传说;曾深入到哥萨克中,走访了大量暴动亲历者。他像托尔斯泰那样考察过昔日战场,也像历史学家一样辨析过事件的真相。
肖洛霍夫美学思想的第二个要点是求善,尊重人的价值,关心人的命运。他说:“人的命运,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命运,未来的人的命运,永远使我不安。”他认为,作为“人民的儿子”的艺术家不能像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灵”那样,“凌驾于各种敌对势力的搏斗之上,对人间的疾苦漠不关心”,而是要用自己的艺术作品去“帮助人们变得更好些,心灵更纯洁,唤起积极为人道主义和人类进步的理想而斗争的意向”,从而改变这个不完善的世界。
肖洛霍夫对处在动荡时代的人民的命运十分关注。在《静静的顿河》这部描述十月革命和苏联国内战争的长篇史诗中,肖洛霍夫没有把领导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作为小说的中心,而是把葛利高里的一生命运放在小说结构的中心。这除了要充分利用他熟悉哥萨克生活这一有利条件外,更主要的是肖洛霍夫想从总结历史经验的高度,提出工人阶级在革命运动中应该如何对待农民,特别是对待中农的问题。因为他在欢呼革命胜利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象葛利高里这样的本不应该被历史淘汰、却成为历史前进的牺牲品的人的命运。
作为一个杰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肖洛霍夫没有回避过人道主义这个重要的伦理道德问题。如在《静静的顿河》中作者着重描写了国内战争时敌对双方不人道的残暴行为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顿河地区第一次内战浪潮是1981年春天,小说着重描写了两个场面。一个场面写顿河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彼得捷尔珂夫在盛怒之下,下令砍死了被俘在押的40名白军军官。另一个重点场面是以彼得捷尔珂夫和克雷沃希科夫为首的80多名被俘的革命哥萨克和红军战士,遭到叛乱哥萨克的毒打后被集体屠杀。这两个场面形成强烈的对照和映衬,突出地提出了战争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同样是残忍的不人道行为,其后果同样导致了加深双方的敌对情绪。但他们的性质是不同的,彼得捷尔珂夫属于不执行红军政策的意气用事,白军则是出于阶级仇恨的报复行为。葛利高里混淆了二者的性质,对彼得捷尔珂夫下令枪杀白军俘虏耿耿于怀,作者明显地把两者区别开来了,但认为红军的残忍行为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肖洛霍夫肯定和赞美在残酷的环境中仍然保持美好人性的人们。如《静静的顿河》的主人公葛利高里,他善良正直、刚毅顽强、热爱自然、热爱土地。但是“1814-1921年事变的强大旋涡”卷走了他生活中宝贵的一切。他也曾一度陷入酗酒、纵欲、砍杀的疯狂状态,但他没有就此沉沦,而是一边痛苦地诅咒“生活是最大的罪犯”,一边顽强地、甚至是凶狠地保护着自己心中善与美的因素,他仍有“一颗在粗俗野蛮的哥萨克胸中跳动着的美好的心”。比如,在战争中抢劫对于哥萨克来说已经相沿成习,但葛利高里仍“心情激动地很害怕去动别人的东西,而且很憎恶抢劫的行为”。哥萨克叛军残杀俘虏已成习惯,他却因“没有下令抢杀和剥光俘虏”而被革职。他当叛军师长时,擅自作主释放了叛军关押的百余名红军家属。在严酷的社会斗争中,葛利高里没有异化成野兽,仍然保持了坚贞美好的人性。

-
埃蒂安-雅克-约瑟夫-亚历山大·麦克唐纳
2025-11-01 00:32:56 查看详情 -
亚历山大·达尼洛维奇·缅什科夫
2025-11-01 00:32:56 查看详情 -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
2025-11-01 00:32:56 查看详情 -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
2025-11-01 00:32:56 查看详情 -
鲍利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
2025-11-01 00:32:56 查看详情


 求购
求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