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良嗣

赵良嗣
人物简介
赵良嗣(?—1126年)[1],即马植,辽燕(今河北北部)人。仕辽至光禄卿。 徽宗政和初,童贯使辽,因献结好女真伐辽取燕之策,随贯归,易姓名李良嗣,被荐于朝,徽宗召见,进联金灭辽之议,赐姓赵,任秘书丞。宣和二年(1120)多次使金(女真),与完颜阿骨打谈判联兵攻辽事,颇尽心力。进龙图阁直学士。宋攻克辽燕山府后,官至光禄大夫。后因力谏勿纳张觉,夺职。累贬郴州(今湖南永兴南)。靖康初,以结边患,于贬所处死。后金人败盟,于钦宗靖康元年戮死于郴州。有《燕云奉使录》,已佚。事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四、一一,《宋史》卷四七二有传。今录诗二首。
历史事件
宋政和元年(1111年),童贯作为宋朝使节出访辽国。童贯当时是西北宣抚使,被称为西陲将军,深得宋徽宗信赖,宋徽宗认为他是北部边患专家,其实他只是个不懂军事、不会打仗的“常败将军”。
童贯在辽国官员的陪同下在卢沟桥附近的驿馆里下榻。这期间,因买马结识了一个叫马植的人。马植曾任辽国的光禄卿(三品),就是专管祭祀、朝会和皇帝生活用品的官儿,后来辞官做起了马贩子。此人是燕京人,做事干练,虽然身在辽国,却希望自己的家乡能归宋朝,可谓身在辽国心在宋。马植说自己身为汉人,祖居燕山,想到契丹人占着燕山心感愧疚。现辽帝天祚荒于女色,大权旁落于大舅哥萧奉先手中,辽国已是外强中干,人心涣散,灭亡是迟早的。他向童贯献计说:现在在辽国东北面有一支女真人,他们对辽国通鹰路、打女真的做法非常不满,正在酝酿一场大的反抗。宋朝应当以买马为名,暗中遣使渡海,与女真人联合图辽,南北夹击,燕云十六州何愁收不回呢?童贯是个聪明人,连呼好计。
1115年,听说大金国成立,马植向宋朝的雄州投了蜡丸书密信,在雄州刺史的协助下回到宋朝,隐藏在童贯家中。早在童贯与马植初次见面时,童贯就想到马植早晚要回到宋朝,为隐瞒身份,就赐马植改名为李良嗣。此时,童贯也向宋徽宗献上了联金灭辽之策,并向宋徽宗推荐了马植。宋徽宗听后连连点头,念李良嗣一片忠心,赐予皇姓,即称赵良嗣。宋徽宗说:“辽国不灭,燕云不收,北部边陲久不安宁。今所献良策,或可解除朕心头之病。”
关于是否应该与女真人结盟夹击攻辽,宋朝的大臣们在廷议时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但经过童贯的运作,还是没能阻止宋徽宗做出与女真联合攻辽的决定。《三朝北盟会编》对“海上之盟”的评价是:“国家祸变自是而始”。
作战的金军
谈判经过--几经波折多次使金
联合女真攻辽之策虽然定下来了,但是由于宋朝跟西夏打了一次败仗,随后西北又发生了一次地震,所以结盟之事暂时搁置。
政和七年(1117年),童贯调到枢密院主管北方防务,这时金已经建国并且占领了辽东,打过了辽河,童贯便准备实施马植之策。八月,宋朝非正式地派了一个辽降宋、懂金文的药师去探女真虚实,结果此人因为没带正式的文书,到了金州被女真兵抓住,直到政和八年才回到山东,无功而返。
宋朝总结了第一次派人的教训,决定正式派使节使金。于是挑选了有胆识、文武双全且有勇有谋的登州防御史马政做正使,平海军卒呼延庆为副使。经过一番准备,政和八年八月,使团从蓬莱出发渡海,九月到了辽东金州,又走了20多天到了金上京。阿骨打在皇帝寨接见了马政一行,听闻宋金联合攻辽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动议,十分意外。阿骨打与吴乞买、撒改、斜也、斡鲁、粘罕、完颜希尹等商议了两天,决定同意这个策略,并派渤海人李善庆等人与马政同回宋朝商量具体事宜。
李善庆一行十月起程,十二月抵达了汴京。宋徽宗并没有接见李善庆等金国使节,只是派了蔡京、童贯与金使谈判。童贯首先提出攻辽成功后燕云十六州自然归宋,李善庆以临行时太祖未授分配燕云权力为由,含糊其辞。
政和九年三月底,宋朝派赵有开为使,呼延庆为副再次使金,李善庆等金使跟随回到金国。不料走到登州,没等上船渡海,赵有开就死了。这时宋朝听到辽国册封阿骨打为东怀国王、辽和女真讲和的消息,就取消了再派使节的打算,让呼延庆只带登州的文书与李善庆回金国,六月初到了金上京,呼延庆被扣留。金国粘罕问呼延庆,宋朝为何中止谈判,并对宋朝此前再三的傲慢无礼表示不满。呼延庆回答:我朝听说贵国已受辽封为东怀国,与辽修好,故未遣使。粘罕说:与金修好是辽单方面的意思,辽册封金为东怀国,是对大金的侮辱,并没有接受。如果宋朝想继续联金攻辽,请拿国书来。因宋徽宗没见金使,这次阿骨打也没见呼延庆。宋朝滞留了李善庆8个多月,金国又扣留了呼延庆几个月,才放回大宋。
宋金结盟--金变被动为主动
宋政和十年三月,赵良嗣带着宋徽宗的亲笔信再次使金。此时恰巧阿骨打带兵在外攻打辽上京,二国政吴乞买接待了赵良嗣。吴乞买建议与宋朝的结盟叫金宋联盟。赵良嗣一听金在前,觉得很不舒服,但把宋放前边,金朝又不会同意。于是脑筋一转,就说:此盟是从渡海开始的,不如就叫海上之盟。吴乞买表示同意。
赵良嗣未等阿骨打回来,昼夜兼程,在辽上京附近追上了阿骨打,进行了金宋结盟的谈判。赵良嗣首先拿出了宋徽宗的亲笔信,这信除了礼节性的话之外,主要就是双方联合攻辽成功后,请许宋燕京一带旧汉地。这个条约定的本来就很不明确。实际当时契丹占的长城以南的地方共分成燕、云、平三部分:燕是北京周边(包括北京)的9个州县;云是大同周边(包括大同)的7个州县,加起来十六州。但是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平州,就是秦皇岛周边的滦、昌、乐等州县。宋对是否要西京大同说的含糊其辞,对(平州)秦皇岛地区根本就没有提及。这么糊涂的朝廷,谈判中怎么能占到便宜呢?经过辩论,双方达成如下条款:
一、宋金南北出兵夹攻契丹。两国军队均不许越过长城。这期间双方不许单方与辽讲和。
二、宋朝作为代价,将每年贡给辽国的岁币,按旧数转贡金国。金国出兵,宋朝给予一定的粮饷军费补贴。
三、战后(如果胜利),金原则上同意将燕云十六州交给宋朝。
四、双方不许招降纳叛。
五、双方共同遵守盟约,若不如约,则难依已许之约。
六、平州不属燕京旧汉地,也不属辽太宗受贿之地,与燕京为两路,不在归还之列。此外,金军为捉拿天祚帝暂住西京(云中)。
赵良嗣回到汴京后,由于出色地完成了“海上之盟”的签订,宋徽宗和童贯都非常高兴,赵良嗣也变成了朝野中无人不知的名人。宋金之间经过两年时间派使节“五来二去”的周折,终于签署了“海上之盟”。
大宋:惨不忍睹的“胜利”
盟约签订后,阿骨打率领金军很快攻下了辽中京,同时派粘罕出兵占领了西京大同。这时,阿骨打在关外把军队安顿下来,等待宋朝出兵攻燕京的消息。宋朝却迟迟没有出兵。原来宋朝“后院起火”,方腊在南方的起义让宋徽宗焦头烂额,宋朝只好先派兵镇压方腊起义。方腊平了之后,童贯才率大军挥师北上攻打燕京,虽然晚了很长时间(三年零八个月,如果从金建国算已经晚8年了),可毕竟是出兵了。然而童贯所率大军连连溃败,始终攻不下燕京,只好求助阿骨打。阿骨打非常气愤,同时也对宋军产生了一种蔑视。于是挥师南下直指居庸关,守关的辽兵听说阿骨打率领金军要攻关,放下武器打开关门让金军通过。就这样,金军一路顺利进入燕京城。燕京城的文武百官都集合在鞠球场上受降,连炮衣都没有掀开,说明面对金军辽军根本就没想反抗。金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燕京城。
最后大宋不得不与金国达成如下协议:金同意将太行山以东燕、蓟、檀、景、顺、涿、易七州交还于宋;宋每年向金纳岁币(进贡)银绢各20万两匹,另输代税钱100万缗;平滦营不是五代时契丹的受贿之地,不在归还之列。西京暂不还,另议;宋同意金带走燕地人口。
对宋来说,这是个相当苛刻的协议。但是宋徽宋急于庆祝所谓的“胜利”,并没有计较,就急着答应了。金军满载金银财宝、图书典籍,押解着几万燕京的各类工匠、年轻女子、青壮劳力浩浩荡荡一路向东去了,给宋朝留下了一座空的燕京城和周边几座几乎空了的县城。尽管如此,宋徽宗仍然非常兴奋,他认为自己完成了历代老祖宗都没有完成的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伟业,值得庆祝。于是先是把收复燕地有功人员晋官封爵,封童贯为豫国公,封赵良嗣为近康殿学士(二品)等,又宣诏全国大赦,同庆三天。最可笑的是,他觉得这些还不够,最后在万岁山刻了一块石碑,让自己的功绩永垂青史[4]。
历史背景
“辽国必亡,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万一女真得志,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事不侔矣。”
赵良嗣思辩不俗,还有一副好口舌,仅凭三言两语,就哄得宋徽宗龙颜大悦。其实早在仁宗和神宗时期,朝廷就制订过联合高丽对抗辽国的战略规划,并得以部分实现。作为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徽宗马上想到的就是效仿皇父的做法,眼下除了高丽这层老关系外,还多了女真反辽的天赐良机,若是把握住机会,没准能彻底除掉辽国这个横亘在北方的心头大患。赵良嗣的情报,勾起了徽宗的念想,每一句话都说到了艺术家皇帝的心缝里。于是,在大内朝堂上,徽宗授予无尺寸之功、且不知根不知底的赵良嗣“朝请大夫、秘书丞、为秘阁待诏、备皇帝顾问”这么一大串头衔,让他由一个大辽的叛逃者,骤然变身为大宋的宠贵。
但是,赵良嗣给北宋带去的,只不过是某种宽泛的构想,并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步骤。他此前甚至连女真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如何联金?选择哪种形式和途径?这些涉及具体落实的问题,只能统统交给北宋方面去想办法。而北宋对辽、金双方的战争形势缺乏及时可靠的情报渠道,辽东半岛又属于辽国的东京道,辽人不可能允许大宋的海船靠岸,不加阻拦地放任宋使北上联络金国。正基于此,北宋在第一时间想到了友好邻邦——高丽。
于是就有了开篇的那一幕。在赵良嗣到宋国一年零三个月之后,徽宗高调地超规格款待了李资谅,他希望能通过高丽的协助,与金国取得联络。政治嗅觉敏锐的李资谅听到宋徽宗的密谕,马上就明白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了。然而,对于十年前刚刚被女真人放了一次血的高丽而言,这分明是逼着他们去摸高压线[5]。
靖康之难
靖康之难,一个极其富强的宋王朝,突然崩盘,绝大多数人尚未来得及反应,就已经迅速跌落至谷底。这其中既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更多的是人为因素造成,靖康之难到底是谁造成的祸害,这个话题在南宋以后一直都很热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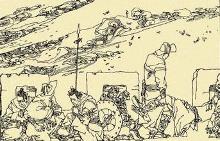 靖康之耻(5)汉式帝国结构发展到宋代日趋完善,组织能力更加强大,所以宋朝创造出汉唐都远远不能望其项背的文明高峰,但仍有其缺陷,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抗大风险能力。封建领主制民族将主权分散到许多个层叠的领主单元,所以组织能力很差,但其中一个甚至几个领主的损毁都不会造成全盘崩溃。而庞大的汉式帝国虽然组织能力奇强,但是高度统一的主权形式也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了一个篮子里,一旦被敌军攻克国都,整个国家都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
靖康之耻(5)汉式帝国结构发展到宋代日趋完善,组织能力更加强大,所以宋朝创造出汉唐都远远不能望其项背的文明高峰,但仍有其缺陷,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抗大风险能力。封建领主制民族将主权分散到许多个层叠的领主单元,所以组织能力很差,但其中一个甚至几个领主的损毁都不会造成全盘崩溃。而庞大的汉式帝国虽然组织能力奇强,但是高度统一的主权形式也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了一个篮子里,一旦被敌军攻克国都,整个国家都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
前代的汉唐面临的敌人很弱,做不出来这样的事,但时代发展到宋代,辽、金甚至西夏、蒙古的出现就有了将这种危险转化为现实的可能。而由于缺乏长城的稳定防御以及蒙古草原的现代化,宋帝国的国土安全远逊于前代甚至后代的明朝。虽然宋初通过强大的河北军,用无数儿郎的血肉组成新的长城,以步制骑,将强大的辽军挡在国门之外,但随着与辽帝国的百年和平以及西夏的崛起,宋军的精锐已经转移到陕西军,河北军的实战能力已经很差。
当失去辽帝国这个活长城又错信郭药师时,河北军再也无法像百余年前的潘美、李继隆那样抗击彪悍的女真铁骑了。而本来更加强大的陕西军,被牵制在广袤的西夏边境上,又突然失去了童贯这个主心骨,虽然也派出了一些部队救援中原,但始终没有对金军形成有效攻势,甚至被濒死的西夏人咸鱼翻身,战线东移了不少。
顺便说一句,有些人说宋朝“守内虚外”,为了维护封建独裁统治,不信任边将,把兵力都集中在都城,所以边防军战斗力差。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宋初的精兵集中在河北,后来在陕西,东京只有一些内卫、仪仗部队,靖康之难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正是都城守御虚弱,边防精锐来不及救援造成的。“守内虚外”的说法有,但恰恰是错误的。
当然,除了这些客观原因外,更多的是人为因素。类似情况发生在罗马、波斯、大明身上的时候,都是这些帝国自身走入弱势,实难支撑的时刻。而宋帝国却是在经济、军事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主动崩盘,则不得不认为人为因素更多于客观因素。
靖康祸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童贯,这位宦官王确实在陕西战场立下大功,但他为了立更大的功,挑唆艺术家皇帝违背祖宗家训,挑开宋辽战端,自己创造了无数令人瞠目的纪录,也将文明葬送在了巅峰。而他的同伙蔡京、王黼、赵良嗣包括宋徽宗也都是主要责任人。
当然,这些人是直接责任人,但这一群思维方式奇特的人是怎么掌握国家大权的?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现在有些人把祸首认定为宋太祖、宋太宗,认为是他们阉割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造成了靖康之祸。甚至有人把责任扣在孔夫子头上,认为是儒学造成了汉民族的“文弱”。我还遇到过有人说是朱熹的理学造成的(注:朱熹在靖康之难三年后才出生)。为什么靖康之难这么重大的一个历史教训,到我们的时代突然变得这么混乱,会有这么多人对这么严肃的一个问题信口雌黄?事实上,南宋以后人们对靖康之难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并且基本认定其祸首就是——王安石。
对,您没有看错,靖康之难的祸首正是“中国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
很清楚,靖康之难的原因既不是什么“文弱”,也不是什么“守内虚外”,而是灭辽这个近乎弱智的决策。世界上有弱智存在很正常,但是弱智们掌握朝政就很可怕了,宋徽宗、蔡京、童贯、王黼这些人为何能够身居高位并且沆瀣一气,破坏宋帝国长久以来稳定的决策机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党。
熙宁变法我们前面一直没有说清,因为现在才是说清的时候。熙宁变法的具体内容完全正确,大多进入宏观经济学的经典教材,也是现代国家具体采用的经济政策,王安石的奇才堪与沈括、牛顿比肩。但是他试验这些工具的时候方式太过于激进,对经济的一时伤害尚在其次,而这场变法造成的“新旧党争”才是靖康之难的主源头。王安石除了千年不遇的卓越才华外,还拥有极高的人格,但非常遗憾的是他提拔的人却没有一个好东西。曾布、吕惠卿这些人不是真正的改革家,而是企图打着改革的名义攉取政治利益的投机分子。《宋史奸臣列传》中共有21人,其中14人在北宋,这其中又有12人都是新党人士。大家注意,“新党”、“旧党”这样的词汇并非所谓旧党人士发明,而是新党人士在朝廷内部人为划分出的阵营,政治投机商们便通过这样的阵营打击异己,提拔自身。宋神宗年轻时信任王安石,是新党的支持者,后期非常后悔,转而支持旧党。而其后执政的皇帝、太后在新党和旧党之间反复切换,将党争的风气推向了高潮,而最令人遗憾的是,最后的胜利者仍然是新党:宋徽宗。
虽然最后的新党不再像王安石那样不理智的强推新法,但他们的政治风气却已经形成。众所周知,权力的制约和内部平衡是一个权力主体生存的保障。按照宋朝的权力制约设计,皇帝、台谏、文官形成三足鼎立的制约态势,相当稳固。但是新党人士为了自身利益,无原则的和皇帝合作,压倒了反对势力,形成了制约很小的权力阵营。这种风气在曾布、吕惠卿身上已有体现,在蔡京、童贯身上更是发挥到了极致。按照宋廷的决策机制,做出一项战略决策需要通过很多环节,接受很多监督,并非某些人头脑一热就能通过。伐辽这种智力不正常的战略明显是某些人的好大喜功,在正常的朝政下是不可能通过的,也只有皇帝、首相、总司令沆瀣一气的时候才能通过。
中打转的宋夏战争更加激烈震撼[6]!

-
运良版牧马人战马上市 4月15日正式上市
2025-10-03 09:34:52 查看详情 -
运良版牧马人战马上市 15.99万元
2025-10-03 09:34:52 查看详情 -
运良版牧马人战马上市 补贴后售18.18万元
2025-10-03 09:34:52 查看详情 -
杜兴氏肌肉营养不良症
2025-10-03 09:34:52 查看详情 -
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
2025-10-03 09:34:52 查看详情


 求购
求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