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角色扮演理论

角色扮演理论
角色简介
角色扮演需要的是一种能够洞悉他人态度和行为意向的能力。在米德的理论体系中,这种角色扮演能力也被称为“心灵”,它包括:
(1)理解常规姿态的能力;
(2)运用这一姿态去扮演他人角色的能力;
(3)想象演习各种行动方案的能力。这种被称为“心灵”的东西并不是人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社会过程之中、在社会互动的经验母体之中产生和发展的”,其作用在于帮助人们获得运用和解释有意义的姿态的能力,即意味着一个人可以通过环境中其他人发出的姿态来解读这些人的意向,具备这种能力是心智成熟的先决条件,也是人实现社会化的第一步。
举例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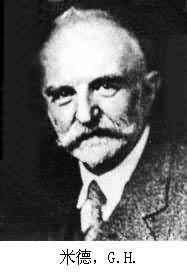 米德 在我们刚出生的时候,作为婴儿的我们并不具备自我意识,我们的所作所为完全就如同“低等生物”那样是根据他人的姿态做出的条件反射,我们会哭泣,但这样的哭泣并不能准确的指明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是食物、水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同时,由于不能准确解读其他人在特定环境中发出的声音或姿态,我们经常会产生适应上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一直要持续到我们开始本能地尝试扮演他人的角色才有所改善,例如一个初步获得解读符号意义能力的婴儿能通过母亲的语调、表情和话语来想象她的感觉和可能的下一步行动,也就是扮演母亲的角色。角色扮演对于个人心智的产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除非他人的姿态以及这些姿态所显示的行为的倾向能够作为有用的信息被你加以利用,来暗中预演可供选择的行动路线,否则公开的行为将经常会导致对环境的不适应。如果一个人不具备对必须接触的人的观点进行设想的能力,那么要想适应这些人并与之和谐共存,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米德 在我们刚出生的时候,作为婴儿的我们并不具备自我意识,我们的所作所为完全就如同“低等生物”那样是根据他人的姿态做出的条件反射,我们会哭泣,但这样的哭泣并不能准确的指明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是食物、水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同时,由于不能准确解读其他人在特定环境中发出的声音或姿态,我们经常会产生适应上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一直要持续到我们开始本能地尝试扮演他人的角色才有所改善,例如一个初步获得解读符号意义能力的婴儿能通过母亲的语调、表情和话语来想象她的感觉和可能的下一步行动,也就是扮演母亲的角色。角色扮演对于个人心智的产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除非他人的姿态以及这些姿态所显示的行为的倾向能够作为有用的信息被你加以利用,来暗中预演可供选择的行动路线,否则公开的行为将经常会导致对环境的不适应。如果一个人不具备对必须接触的人的观点进行设想的能力,那么要想适应这些人并与之和谐共存,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角色理论
认为,在孩子出生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并未意识到自己与他人是有所区分的。随着语言的发展和对符号的理解,自我概念开始发展。当在思维中把自己当作客体并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加以想象和思考的时候,自我就形成了。他们可以与自己的自我“交谈”,可以对自我作出反应。他们本身成为了自我的客体。 n自我分为两部分,即“主我(I)”与“客我(me)”。“主我”包括每个人自我的、独一无二的、“自然”特征,如在每个正常婴儿和儿童那里都有的无约束的冲动和动力。“客我”是自我的社会部分,是内化的社会要求和期待,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主我”首先发展起来。“客我”要经过很长时间才得以出现。自我的发展包含“主我”与“客我”之间的一系列连续交流,在这种交流过程中,“主我”不断地对变化着的“客我”作出反应。 n米德认为,社会化的实质是“角色扮演”,即学会理解他人对于角色的期待,并按照这种期待从事角色行为的能力。米德认为,社会化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模仿阶段(imitation stage)、嬉戏阶段(play stage)、群体游戏阶段(game stage )。每个阶段的“角色扮演”能力是不同的,“客我”涵盖的内容和范围play stage也是不同的。
各个阶段
模仿阶段
人一生最初的两年,儿童仅仅与父母进行“手势交流”,模仿父母的动作。真正的“客我”尚未形成。
嬉戏阶段
从两岁开始,大约持续几年的时间,开始从事“角色扮演”(role taking)。他们把自己想象为处于他人的角色或地位,从而发展起从他人的角度看待自我与世界的能力。起初,儿童开始扮演重要他人的角色,在这阶段,当儿童模仿他人角色的时候,他们实践着重要他人所期待的态度和行为。虽然“客我”在这阶段开始得到发展,儿童还是不能理解角色扮演的意义,他们只是在玩耍生活中的社会角色。
群体阶段
三四岁以后,开始走出家庭,与更多的人和群体发生联系,同时他们也把家庭看作是他们所隶属于的群体。开始关心在非家庭群,包括作为整体的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发展起了一般意义上人们对他们的要求和期望的观念,即米德所说的一般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s)。当他们开始扮演“一般化他人”角色时,标志着他们已将“社会”内化了,“客我”的形成过程已经完成。
可见,社会化过程就是一个从只能扮演有限的、特定的角色到能扮演普遍的“一般化他人”的角色的演进过程。
角色阐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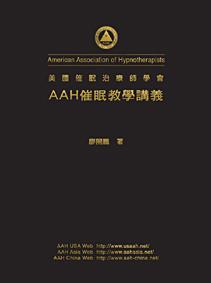 角色催眠 角色扮演学说(RoleEnactment)是由萨宾提出并详细阐述的,不过,其最好的解说则见于萨宾是以一个社会心理学家的观点研究催眠的。他认为,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扮演一定的角色,以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催眠也不过是一种社会环境。正如人们能够扮演雇员、恋人或其它任何成千上万的角色一样,人们也可以扮演“被催眠者”或“催眠师”这样的角色。
角色催眠 角色扮演学说(RoleEnactment)是由萨宾提出并详细阐述的,不过,其最好的解说则见于萨宾是以一个社会心理学家的观点研究催眠的。他认为,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扮演一定的角色,以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催眠也不过是一种社会环境。正如人们能够扮演雇员、恋人或其它任何成千上万的角色一样,人们也可以扮演“被催眠者”或“催眠师”这样的角色。
(1977)和瓦格斯塔夫(1981)二人都公正地指出,这并不是说受术者在故意作假。如同能够真实地进入其它生活中的角色一样,他们也可真实地进入催眠中的角色。萨宾称之为“机体进入角色”。正是由于进入了角色,受术者才真正相信他们的确经历着所受暗示的催眠行为。当受术者报告体验着幻觉时,萨宾则认为这些幻觉是“信任的想象(believedinimagings)。受术者非常好地扮演了“被催眠者”的角色,以至于他们自己也真正相信确实产生了幻觉。
虽然人们常常认为萨宾反对把催眠状态视为一种意识的变换状态,但事实并非如此。他认为,有关催眠状态的大量争论是沿着这样一条主线来回往复的:这些行为是受术者在催眠状态下表现出的特征性行为;该受术者作出了这样的行为,故他肯定处于催眠状态之中。看来萨宾之所以不反对把被催眠者看成是处于一种意识变换状态的观点,是因为他愿意接受另一种观点,即被催眠者的主观反应可以作为他们处于一种意识变换状态的证明。然而,正如席汉和佩里(1976)所指出的那样,萨宾对意识变换状态的观点看来并不满意。他认为,如果把催眠现象看作是信念的想象,而不是看成催眠状态的外在表现,那么对于同一现象的表述就更加清楚,而且对于这种信念的想象所能发生的环境也可能提供更好断解释。

-
柯明斯基理论 第三季
2025-09-14 23:58:31 查看详情


 求购
求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