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天济

李天济
人物简介
李天济,1947年在吴祖光等人的鼓励下,李天济写出了电影剧本《小城之春》,由费穆导演。之后又写了喜剧《逢凶化吉》。解放后,他继续探索喜剧电影的创作道路,写了《今天我休息》,成功地塑造了人民警察马天民这一艺术形象。他因长相特别,还被邀拍过多部影片如《魔术师的奇遇》、《乌鸦与麻雀》、《阿Q正传》等。此外他还执导了《不夜的村庄》和《抓壮丁》。
根据文学家钱钟书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围城》剧中精彩片段:“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的那位老学究的扮演者为著名表演艺术家李天济,他还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小城之春》的编剧!
个人经历
建国前
李天济(1921—1995)曾用笔名高鲁、于刚、光沛,中国著名编剧、演员,1921年5月生于江苏镇江。李天济自幼爱好文学,读了大量小说,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功底。
1938年9月李天济来到成都,考进了四川戏剧音乐学校;在校期间,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徐州突围》,在报上连载几近一年。1941年起,先后在重庆中央青年剧社、民众剧社、中华剧艺社当演员、剧务、剧务科长、演出部主任。这对他以后的创作生涯,打下了比较扎实的生活基础。
1947年,李天济回到上海,曾一度担任上海剧人福利会秘书;同年他发奋创作电影剧本《小城之春》,以其独到的视角和富有表现力的结构,通过剧中人物在规定情景中的感情纠葛,折射社会,透析人生,以初生之犊的锐气,对电影特性进行探索,在影坛引起较大反响,后由费穆导演拍成影片。
建国后
建国后,李天济相继在中央电影局电影剧本创作所、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上海电影制片厂任编剧。他能比较自觉地深入生活实际,善于从普通的日常生活中摄取群众所关注的热点,经过概括提炼而形成创作题材,热情讴歌新社会新生活中的凡人凡事,如他精心创作的《今天我休息》,剧中主角民警马天民的形象,血肉饱满,熠熠生辉,至今仍广为传诵。而后,他又陆续写出了《爱情啊,你姓什么》、《姑娘今年二十八》、《逢凶化吉》等电影剧本,以比较生动的情节,注意电影艺术的视觉造型,并赋之以喜剧性的矛盾冲突,从而产生风趣、幽默的喜剧效果。
长期以来,李天济老师还潜心与表演艺术。1949年在影片《乌鸦与麻雀》中饰演国民党军官侯义伯,并于1959年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评奖中获个人一等奖。以后,又曾在《魔术师的奇遇》、《阿Q正传》、《八仙的传说》、《绝境逢生》等影片中扮演角色,以其夸张的表演和固有的脸型特征,擅演各类反面人物,在观众中颇有影响。
剧作
《好夫妻》
《小城之春》
《闯关》
《落水记》
《见面礼》
《逢凶化吉》
《这是我应该做的》
参与影片
绝境逢生 (1994)
天朝国库之谜 (1990)
逢凶化吉 TURN ILL LUCK INTO GOOD(1989)
八仙的传说 THE LEGEND OF EIGHT IMMORTALS(1985)
夜半歌声 SONG AT MIDNIGHT(1985)
姑娘今年二十八 GIRL AT 28(1984)
爱情啊,你姓什么? WHAT IS LOVE?(1980)
见面礼 THE FIRST GIFT(1980)
魔术师的奇遇 (1962)
太极拳 (1959年10月)
今天我休息 (1959)
落水记 (1956)
乌鸦与麻雀 (1949)
好夫妻 (1948)
小城之春 (1948)
还乡日记 (1947)
获奖
1959年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评奖个人一等奖
谈喜剧
谈到喜剧电影的人物塑造,我觉得里边的人物之所以好笑,是因为他的行为本身往往带有“不可思议”这样一种特点。这种例子也是很多的。比如《寅次郎的故事》,我觉得山田洋次在人物塑造上玩来玩去就四个字:自作多情。他写寅次郎跟人家谈恋爱,谈着谈着,到最后女的反而跟人家结了婚----人家根本不爱他,他以为人家爱他,这不叫自作多情吗?自作多情,才会构成笑。同样,写某个人吃苦,这并不好笑,可是如果这个苦是他自找的,那就显得很好笑了。比方说,你李天济上学时因为老师不让你考试及格,你想捉弄一下老师,就在教室门上放了一个痰盂罐,结果外面一声“老师来了”,李天济一紧张,自己去拉门,痰盂罐砸了自己脑袋——自己安排一个圈套,结果倒霉的却是自己,这叫自食其果,是可笑的。还有一种可笑的行为,是自以为是、自作聪明。比如,你李天济明明长得这个样子,可你老觉得自己长得即使不象梁山伯也应当象潘安,结果你拿了镜子一看,其实一点也不漂亮,你就赖镜子歪曲了自己的形象。又比如,“四人帮”倒台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政治笑话:某个国外的卫生代表团来访问,当人家向部长先生提到贵国李时珍如何如何了得的时候,这个部长说:“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他的政策落实吗?快给李时珍落实政策。”——在这里,他的可笑就可笑在自以为是上。也就是说你的愿望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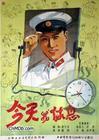 你的实际是背叛的,是自己背叛了自己。以上这些例子,是从人之常情来讲的;要是从故事来讲,那范围就更宽。我记得有一个苏联的短片,其中写一群年轻人带着一条狗去外面玩——这条狗训练有素,你扔什么它都能给你叼回来还给你。来到湖边后,这群年轻人想做鱼汤喝,可是又不愿意麻烦,就往湖里扔了颗炸弹,结果没扔远,炸弹落在湖边。于是,那条狗就把炸弹叼了回来。主人一看不得了,撒腿就跑。可是主人越跑,那狗就追得越欢,非要把这个炸弹还给他。象这样的情景安排出来,你还怕观众不笑吗?!
你的实际是背叛的,是自己背叛了自己。以上这些例子,是从人之常情来讲的;要是从故事来讲,那范围就更宽。我记得有一个苏联的短片,其中写一群年轻人带着一条狗去外面玩——这条狗训练有素,你扔什么它都能给你叼回来还给你。来到湖边后,这群年轻人想做鱼汤喝,可是又不愿意麻烦,就往湖里扔了颗炸弹,结果没扔远,炸弹落在湖边。于是,那条狗就把炸弹叼了回来。主人一看不得了,撒腿就跑。可是主人越跑,那狗就追得越欢,非要把这个炸弹还给他。象这样的情景安排出来,你还怕观众不笑吗?!
在喜剧的构思中,我们还要正确看待误会的运用。喜剧创作是经常要用误会和巧合的。本人曾经做过16个小时的讲课,16个小时里我就只讲了两个字——误会。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为误会翻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以前只要有人一用误会,大家都瞧不起,理由是“没有接触到社会的真正矛盾”。哎呀我的娘啊,误会首先是从生活里来的。而且实际上,所有的剧本、所有的片子,不用误会的几乎很少很少。我们诸位都看过万家宝先生的《雷雨》,如果没有误会,这个剧本站得起来吗?假定周萍晓得四凤是自己的同母异父的妹妹,他跟四凤搞恋爱,他有毛病呀?这就是误会——不过它这个误会,不是为引发笑的,区别仅仅在这儿。很多时候,悲剧也是用误会的。堂堂莎士比亚的那个《奥赛罗》,不就是个误会吗?苔丝德蒙娜是很忠实地爱你奥赛罗的,是你奥赛罗自己误会了,整出一台悲剧来。在《罗密欧与朱莉叶》中,朱莉叶吃这个药下去,那是死不了的,可是罗密欧误会了,又是一出悲剧。象《钦差大臣》这样的戏,也同样是用了误会的。我最佩服它一点:它的主人公明明没有说自己是钦差大臣,怎么会被别人搞成个钦差大臣了呢?这个误会这么来的呢?戏一开场,说是钦差大臣要来,那个市长就吓掉了魂。正是从市长这个人的心态出发,他把假钦差当成了真钦差,这个误会就有了依据。所以,问题是不在于你用不用误会,而在于你运用误会的本事的大小。误会运用得好与不好,是被创作者的修养和能力所决定的。在喜剧创作里,判定运用误会的高低,是看你这个误会用得能不能令人信服——我不想用“真实”或“不真实”这几个字,因为一说“真实”,就有“是生活表象的真实还是生活本质的真实”之类的诘问,我这几十年尝到的味道不少,怪麻烦的,因此我宁肯用另外几个字:可信性。你这个误会搞得观众不相信,那就完了。实际生活中间发生的真实的事件,不一定可信,而可信的东西不一定是生活里面真实存在的。这是两回事。报上曾经登过:两口子结婚,放“天地响”鞭炮,“砰”,第一响上天了,但第二响却落在新娘的脑袋上,把新娘给炸死了。这是生活中的真实事件,真实极了。但你要把它写在剧本里边,不行的,因为观众觉得不可信,他会说你是硬编的。
总之,在喜剧创作上,误会、讽刺、巧合、机智、诙谐、滑稽,都是应该允许的。

-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
2025-10-09 03:26:45 查看详情


 求购
求购










